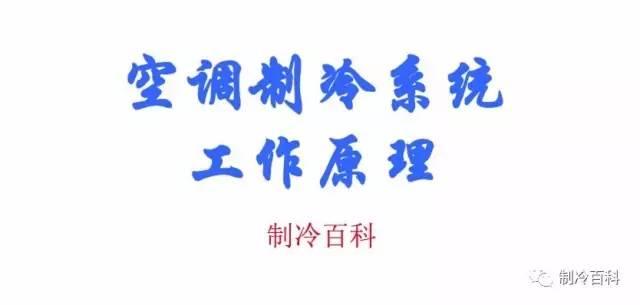67岁老农自夸是毛泽东的领导(67岁老农自夸是毛泽东的领导)
1951年3月31日,毛主席收到了一封特别的信件。说它特别,是因为寄信人来自于湖南乡间的一位67岁的老农,更特别的是,这位老农居然在信中开口求毛主席给他安排工作。
按说,这样的一封信件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嘛!新中国刚刚成立,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亟待收拾,国内匪患猖獗、敌特横行,国际上敌视国无不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毛主席日理万机的时间都不够,哪里还会有闲心思去理会这样一封呢?
可出人意料的是,当毛主席收到了这封信后,内心禁不住颤抖了起来。他仔细读完信件后,又认真地给老农写去了回信,在笔走龙蛇中,他的思绪不禁飞回到了14年前。
1937年,美国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先生在与毛主席的一次谈话时,毛主席就对他谈到了自己在新军的经历便说:“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中,“湖南矿工”就是彭友胜,而彭友胜就是给毛主席写信的67岁老农。
毛主席与彭友胜之间的革命友谊非常深厚,个人私交感情甚笃,俩人的关系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以至于多年后,已经高居中央领导人职位的毛泽东同志,在接受斯诺的采访时,不无动情地提到了这位学生时代的好“大哥”后依旧是念念不忘,这次,彭友胜的书信不期而至,再次从内心深处,唤醒了毛主席思绪中的那段峥嵘岁月。
静坐在案几前,提笔的毛主席思绪再次不自觉地飞回到了40年前。

1911年,中华大地风起云涌,革命的浪潮一波又一波冲击着即将崩溃的满清王朝。当年,黄花岗72烈士的鲜血飘洒在广州城,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也愈演愈烈,敢为天下先的武昌革命党人也不甘落后,率先于全国发起了震惊世界的“武昌起义”。
随即,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纷纷宣布“独立”,脱离了清王朝的统治,创立了革命军政府,一时之间,革命的星火燃遍了整个华夏大地,湖南的革命党人也率先响应了全国的革命形势。
此时,年仅18岁的毛泽东正在湘乡中学读书,武昌首义传遍全国后,湖南革命党人的活动更加频繁和紧张起来,尤其是革命党人到毛泽东所在的学校发表演说后,毛泽东更是心潮澎湃。
对此,毛泽东回忆道:
“黎元洪领导的武昌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我们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需要穿雨鞋,于是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他们正拥到街上去”
没过多久,湖南的革命党人推翻了满清的衙门,建立了革命军政府。但此时满清皇帝没有退位,革命还要经历一个时期的斗争。武昌去不成,毛泽东便决心在湖南当地参加革命军。
参加革命军是要有可靠的人作担保的,可放眼长沙,举目无亲的毛泽东,又有谁能给他担保呢?
为此,他在兵营门口与征兵的人发生了争吵。恰在此时,有一名叫朱其升的上士被毛泽东慷慨激昂的雄辩吸引住了,他将毛主席带进兵营,找到衡东人彭友胜说:“彭副目(副班长),这位兄弟愿意参加革命军,无人担保,我们为他担保行吗?”
彭友胜晚年在向儿孙们回忆起毛主席当兵时的情况,其外孙夏建良这样描述:
1911年10月底,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外祖父彭友胜正与班里的弟兄们在营房外的大樟树下聊天。上司领来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对外祖父彭友胜说:“这个伢子想当兵,就交给你们了。”
借着月光,彭友胜抬头一望,身旁站着一位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高个子,大号军装穿在身上还显得有些短,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正温和地看着大家,下巴上那颗大黑痣特别显眼。

“我叫毛润芝,又名毛泽东,小名叫石三伢子,家住湘潭韶山冲。今日来当兵,请各位弟兄多多关照。”没等大家“欢迎”,年轻人就自报家门。
彭友胜站起身来,简单询问了毛主席的一些情况后,就答应和朱其升一起做他的入伍担保人。然后,彭友胜拉着毛泽东的手说:“走,进营房看看,正好我的上铺空着,以后你睡上铺,我睡下铺。”
就这样,18岁的毛泽东在登记本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毛润之。开始了近半年的辛亥革命军生涯。
毛主席成功加入了革命新军后,在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师标第一营左队,当上了一名列兵。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参加革命军时,其所在队伍的司令是程潜将军,当然了,当时毛主席与程潜地位悬殊,两人也不可能有什么来往。后来,解放战争中,程潜将军率部起义,程潜不一定记得毛主席曾是他的兵。但毛主席却记得那段历历在目的往事,在北京与他相见时,以部下对“老上司”之礼待之。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话又说回来了,当时战局未定,物资装备匮乏,军棉衣、军毯等御寒装备都没有到位,又恰逢是个寒冷的大冬天,孑然一身的毛泽东身无长物,刚入伍的他随时都有挨冻的风险。
可在彭友胜的关照下,毛泽东被安排在了他的上铺,朱其升也慷慨地把自己的一半衣物都分给了这位年轻人。
彭友胜之所以如此关照毛泽东,是因为他觉得毛泽东恐非池中之物。跟毛泽东不一样,彭友胜参军是因为有一大家子人等着要养活,他参军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毛泽东却是心怀天下,为了革命而革命,绝不仅仅只是混口饭吃,
而且毛泽东博古通今,文化水平高,能言善辩,口才特别好,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都能讲出一套一套的道理来。
尤其是,自毛泽东入伍以后,在军事训练上严格要求自己,勤学苦练,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掌握了军事基础知识和战斗基本技能,教官时常让他给其他士兵做示范。整个班容班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彭友胜也就对毛泽东刮目相看了。
因此,毛泽东后来回忆新军生活时说:“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为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凭借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惊人的才华,很快,毛泽东便与全班战友打成一片,大家伙儿都对毛泽东敬重有加,彭友胜为此得意洋洋,经常跟别的班长炫耀:我们班有个大秀才!
值得玩味的是,毛泽东参加革命军后,他领到的是一支“汉阳造”旧式步枪,该枪的编号为8341。

时光荏苒,到了解放初,在建立中央警卫团取番号的时候,主席又想起了自己当年的那杆枪的编号,于是给中央警卫团钦定了取了“8341”这个编号。而这个数字刚好和他活了83岁、主政41年这两个时间高度吻合。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毛泽东刚入伍不久便成为了部队里的“宠儿”,可部队里也并非一汪清水。旧式军队里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很多心怀叵测、动机不纯者趁着改朝换代的当口,浑水摸鱼钻进了革命的队伍里。
他们顶着大兵的头衔敲诈勒索、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一天,一个兵痞拿了卖烟老人家的两包烟,不给钱就要走。毛泽东看见后,硬是抓住他不放,逼着他给钱。当时人多,对方也知道自己不占理,只好给钱。从此,他就和毛泽东结下了梁子,只要逮到机会就想报复。不过,毛泽东一点儿也不怕。因为彭班长等兄弟们,自然会帮他摆平。
毛泽东在革命军的队伍里不仅善于搞好人际关系也拥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据他的战友朱其升晚年回忆:
当时很多兵痞四处寻衅滋事,毛主席经常与之斗争。兵痞们就想伺机报复,但看到毛主席很讲斗争策略,团结一般弟兄,又受到副目(副班长)爱护,也就不敢造次了。
毛主席是一个求知欲望极强的人,当时,毛主席的军饷是每月7元。他除留下必要伙食费外,余下的4元多,全都用在订报纸上。毛主席在班中的威信很高。由于他能写字,有知识,在士兵中他是一位受人敬佩的“大学问家”,经常帮助文化低的士兵写家信,或讲解报刊上的新闻。
我之所以后来会记账、写字、做生意,这多亏了当时毛润之的帮助。毛主席的知识力量使他不知不觉已成为班内的精神头领———大凡正、副目(正、副班长)布置的事情,只要毛泽东认为言之有理的,其他列兵也便一呼百应;反之,若毛泽东加以反对,执行起来就大打折扣。
在毛泽东与副班长彭友胜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逐渐也认识到彭友胜也不是一位简单的人物。
彭友胜从孩提时代起就上山砍柴放牛,下河捕鱼荡舟,年纪幼小的他便竭尽所能地为家庭分担重负。1899年,15岁的彭友胜便背井离乡,外出闯荡江湖,寻找生活出路,打过短工,当过矿工。1907年,时年23岁的彭友胜参加了湖南新军。

在光复长沙的武装起义中,彭友胜是攻打北门的主要指挥者。他率领部队,从北门入城后,又沿现在的蔡锷路往南向前,与革命党人的手枪队打下了荷花池军械局,让新军“枪多弹足”。然后,挥师西进,又攻下省谘议局,再折向又一村巡抚衙门的西辕门,将衙门围了起来,一直到这里挂上白底“汉”字旗。
彭友胜以卓越的功勋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此时的他27岁还是个副班长。长沙反正成功后,正副目们起码应该晋升为“兵头将尾”的排长、队官,而彭友胜这样的有大功者怎么还是继续做副目?
原来,这是因为彭友胜为人忠厚本分,不懂得邀功请功,也不屑于给上级拉关系送礼,再加上部队里也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因此,战功突出的彭友胜始终在副班长的位置上“坐冷板凳”。
尽管彭友胜老实木讷的性格,没有给他的军旅生涯,交出一份仕途高升的满意答卷,可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份质朴和纯真,在部队中,他有着非常好的人缘,包括毛泽东在内,大伙儿都愿意听他的差遣。他更是与少年毛泽东建立起了纯真无邪的深厚友谊。
正当毛泽东打算在部队里大展宏图之际,“南北议和”的消息突然传来,毛泽东以为革命至此已经取得了胜利,是时候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共享天下太平了。
于是,1912年3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把彭友胜拉到一旁,说了一阵悄悄话:“副目,我想离开新军,继续回校读书。”
彭友胜两眼噙着泪水,看着毛泽东久久呜咽不语,半晌,只见他声音沙哑难过地说道:“润芝,我晓得你胸怀大志,不能长久埋没在这里。你就远走高飞吧,我不会为难你……”
这是何等伟大的友谊?
要知道,当时的当兵可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事情。要退出部队,要么,你背负恶名去当可耻的逃兵偷偷离开部队,要么,就光明正大地得到上级长官的许可,否则,纪律森严的部队里,岂会任何人员随意进出?
得到了副班长彭友胜的首肯后,毛泽东即将顺利地离开军营了,不过,在离开之前,全班战友们凑钱办了桌酒菜给毛泽东饯行,其中有一碗是毛泽东最爱吃的红烧肉。
彭友胜很了解毛泽东,知道他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也吃不起红烧肉。
毛泽东当时的军饷是7块,除掉吃饭等开销外,还剩下4块左右。这些钱毛泽东一分都没留,基本上都花在了买报纸上了,他渴望从报纸上看到武昌、北平等地革命军的消息。所以那时候的毛泽东,精神生活是无比丰富的,但物质生活却极度贫乏,要吃一碗红烧肉更是一种奢望。
毛泽东也非常感动,多年以后,每每吃起红烧肉总会想念起当年的老战友彭友胜。

毛泽东与战友们一一碰杯答谢,吃完红烧肉,喝完践行酒,战友们依依话别。彭友胜又把毛泽东叫到了一旁,偷偷地往他手里塞了两块银洋,当作给毛泽东的路费,并说:“多多珍重!”。
毛泽东了解彭班长家里的情况,他之所以15岁就会出来谋生,就是因为家里兄弟多、父母身体又不好。所以平日里一发了军饷,他基本都往家里寄了,这两块钱是他从牙缝里省下来的。两块钱说多不多,却是彭友胜的一番心意。毛泽东推托不过,只能含泪收下了彭副班长的深情厚谊。
告别了军营,毛泽东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大舞台上,演绎着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角色。而彭友胜则继续留了下来当兵吃饷。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这是三国曹魏时代曹植所赋的一首《赠白马王彪》,用这首诗来形容毛泽东实在毫不为过。
经此一别,毛泽东与彭友胜有15年不曾相见。在这15年里,毛泽东在湖南一师上过学、和同学们办过新民学会、在北大图书馆当过小管理员。一番努力后,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
而彭友胜所在的部队,也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他也慢慢由一个班长爬到少尉排长的位置。这个位置对于别的军官来说比“蜗牛还慢”,但对老实巴交完全靠军功,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彭友胜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一天,彭友胜在一张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毛君润之来穗讲学。
“毛润芝?他也到广州来了?10多年没有会面了,见见他去!”,此时的彭友胜才知道,润之老弟要来广州了。
15年不见,兜兜转转,他们还是都在革命队伍里了。只不过昔日的副班长,现在的职位却远低于曾经的列兵了。不过彭友胜相信,不管身份怎么变,战友情是变不了的,他决定上门去找毛泽东。
出发前,他特意理了个发,洗了澡,换上一套新军装,兴冲冲地直奔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正全神贯注伏案备课,听门卫通报,当年的“顶头上司”求见,连忙起身迎接。
“盖三兄!”毛泽东亲热地用别名称呼彭友胜,“别来无恙。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真想死你了。”
彭友胜非常激动,这么多年都没见了,没想到毛泽东竟然还记得他这个笔墨不通的“大老粗”。
于是,兴奋之余,他将这些年来南征北战、卷入军阀混战,后来信奉三民主义的事,一五一十讲给毛泽东听。此时的毛泽东已是中共中央委员,还担任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高屋建瓴,向彭友胜宣传革命道理。毛泽东还恳切地向彭友胜提出,“我们一块干,今后再也不分开了。”
彭友胜沉思片刻,面带愧色地说:“我是个大老粗……干不了舞文弄墨、治国安邦的大事。留在你身边帮不了什么忙,不如继续当兵扛枪好。”
本分憨厚的彭友胜说的是真心话,他不是不相信润之老弟能干成大事,而是那时候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是中国人,不管是在哪里打仗都一样是为了老百姓,所以也就不用折腾了。毛泽东自然不会强人所难。随后,他俩把话题转到军事训练、士兵情绪、工人生活、农民问题上,谈得十分投机,直至夜深人静。

彭友胜告别毛泽东后,不久便参加北伐,投身到炮火连天的战场。他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又一次立了大功,并被提拔为副连长,一家老小的生活终于有了保障。
在很多人看来,他也算是熬出来了。可这官没当多久,彭友胜就做了一个让同僚们无法理解的决定:离开部队,当个普通人。
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原因是:他对国民党部队里的种种不堪行径心灰意冷。他不明白什么叫“攘外必先安内”,他更不明白为何明明都是中国人,他们却非得放着日本人不打,要用枪口对准自己的兄弟?想不通这个问题,不如索性不干了。
这个决定很“任性”,却令人钦佩。为了这个“任性”的决定,彭友胜没少吃苦头。为了养家糊口,这个曾经的副连长在县里看过仓库、打过各种零工。再难的时候,他都没想过再回去。
1940年,他回到老家衡东县三浦乡种起了地。读到这里,不知朋友们是否和笔者一样,会对彭友胜有这样一个认知:
这个老兵还真就不是一个给国民党当兵的料。溜须拍马他学不会、做人又太有原则、就连放弃底线服从命令,他都做不到。
但事实上,他又比那时的大多数人都活得通透。对战友,他够仁义;对像毛泽东这样的有志少年,他懂得欣赏。面对毛泽东的邀请,他确实没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分得清对与错。而这些,正是毛泽东几十年都没有忘记他的原因所在。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伟大人物。长期以来几乎与世隔绝的彭友胜,在看到毛泽东的画像后,才得知当年他手下的那个士兵已经当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兴奋之下,更是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逢人便指着画像就说:“我和毛主席共过事,那一年,他在我手下当过小兵呢。”
当有人提出质疑:“既然毛主席与你共过事,你为什么不跟他走到底呢?”,他只好摇头摆手,长叹一声:“唉,怨只怨我脑后没长眼睛。要是有先见之明,一直跟定毛泽东,如今我也到北京干大事去了。”
自从毛主席在彭友胜手下当过兵的消息传开后,邻里乡亲始终对这位67岁老人的话持怀疑态度,很多人都只是一笑了之,当做看笑话。彭友胜心里很清楚:乡亲们都认为一个落魄的贫农,是无论如何都攀不上万人景仰的伟大领袖的。
而每每向家人提及他与毛主席点点滴滴的过往时,家人们虽然都相信他说的话,但却总给彭友胜“泼冷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人家是不是还记得你,都不一定呢!
如今,彭友胜都已经是个67岁的老农民了,人家可是万民爱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广州一别25年后,别说主席这么日理万机的人了,就是普通人也不一定能记得住你。

可是倔强的彭友胜内心深处却偏不相信,当年的少年毛泽东会不记得他这个“老班长”。
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1951年春,他几次对老伴和女儿唠叨,等到秋收以后,要背上一袋新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最终,彭友胜与老伴商量后决定:暂时不去北京,先给毛泽东写一封信,投石问路,看看当年的那个士兵到底记不记得他这号老农。
当年3月14日,彭友胜特意买回了上好的纸笔和信封,请来了本地“学历”最高的夏金声老先生代笔,由自己口述,给毛泽东修书一封。
信的大意一是问毛主席还记不记得他这个“老班长”?二是拐弯抹角求毛主席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写好信函后,儿女们都抢着要替老父去湘潭寄这封信。但彭友胜不干,非得亲自过湘江、亲手把信送到了邮局。
投递完信件之后的20多天,对彭友胜来说是无比“难熬”的,他害怕毛主席会忘记他,他担心自己会成为众人耻笑的对象,白天吃饭不甜,晚上睡觉不香。望着他那垂头丧气的样子,老伴数落他:“毛主席要管全国那么多的大事,哪有空闲搭理你一个泥脚杆子。六七十岁的人了,还异想天开‘吃皇粮’,这不是为难毛主席吗?”
老伴的话说得彭友胜更加六神无主了。 大约清明节后第3天,乡邮递员风尘仆仆来到彭友胜家——毛主席果然回信了!大牛皮纸信封上“湘潭县王十万对河柴山冲转彭友胜先生收”18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字,是彭友胜熟悉的“毛体”。他捧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双手微微地颤抖,两眼闪烁着泪花。
彭友胜小心翼翼、如获至宝地打开书信,托人念给他听,只见奔放纵横的“毛体”跃然于纸上,信上写着:
友胜先生:
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
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去试一试。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
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三月三十一日
当旁人读完了毛主席的亲笔书信后,彭友胜的脸庞早已是热泪滚滚:毛主席还记得我,他没有忘记我这个“老班长”,没有拒绝给我安排工作。彭友胜全家像过节一样,沉浸在无比喜悦和幸福之中。

透过这封信,足见毛主席心思之巧妙。因为在信中,毛泽东既没有答应给对方工作,也没有完全拒绝。信的第二段一开始毛泽东就讲明了,希望他能“待在乡下为好”,而且也表示自己不便向湖南方面直接推荐。这是原则性问题,他不能随便徇私。
但同时,毛泽东也替对方想好了出路:如果确实困难,可以自己去找程星龄,自己去省里争取。毛泽东甚至给对方出了主意,该怎么争取才有可能成功。
在这封加上标点共300余字的信里,笔者看到了两个字:尊重!这种“尊重”,不只是开头的“不要客气”、也不只是结尾的“顺致敬意”等字眼,而是体现在字里行间的一个细节上:在信中,毛泽东特意用了一个括号,刻意注释了他与彭友胜共事时的关系。
“你当副目,我当列兵”,这8个字他本可以不写的。这是一个最高领导人,明确向一个老农民表示“我以前是你的一个兵”,这份气度,几人能有?所以,这封信是充满人情味而又暖心的。对于彭友胜来说,它是无比珍贵的。
彭友胜很快就将全信300多个字背得滚瓜烂熟。遇上有人打听此信的内容,他便一字不漏地背给人家听。至于信的原件,他已用红绸布包得好好的,放进衣柜夹屉里,用一把“铁将军”把住,轻易不让别人看。搞好了大田的犁耙工夫后,彭友胜坐火车直奔省会长沙。
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彭友胜找到了副主席程星龄,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在长沙一住半个月。
彭友胜之所以半个多月都没有等到程星龄的答复,一则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彭友胜的个人经历在乱世中变得非常复杂了,二则是因为他的年纪都67岁了,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确实也没法给他安排到合适的工作。
对此,毛主席也早已想到了程星龄的难处。于是,在彭友胜去省城找程星龄时,程星龄也接到了毛主席写给他的信函。
星龄兄:
此人叫彭友胜,据我过去的印象是个老实人,四十年的历史不清楚,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湖南军队充副目(即副班长)我在他那一班当列兵,后来在广州见过一面。现来信叫苦,我已复信叫他待在乡下,不要出外;如果十分困难,又出于自愿,不怕无结果,则可持我的复信到长沙找你,向你请示:是否可以对他有帮助。
我在复信上已说明,不一定有结果,因为程先生不清楚彭的历史,连我也不清楚,不便提出确定的意见。
他来见时,请你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酌予帮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员例年给若干米,或一次给他一笔钱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办法,则为介绍一个工作而不用上二次办法。请酌定。
毛泽东
三月三十一日
从这封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毛主席谨慎的处事风格:老朋友归老朋友,即使曾经是老相识,毕竟很多年不见,必须要加以考察,看其是否历史清白,然后才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帮助,这才给出了具体的办法,解决了程星龄犯难的问题。

当然,对于这些事情,彭友胜是完全不知情的,在省城好吃好喝地被人伺候着,种惯了地的彭友胜哪里还能闲得住啊!
于是,彭友胜找到程星龄说:“你们把我当上宾,天天让我吃鱼吃肉,又没事可干,实在不好意思。我这次来长沙,主要是请您安排个工作,家里人还在等我的喜讯呢!”
程星龄安慰了老人一番,提笔给省委统战部写了一封公函,大意是:
彭友胜先生1911年曾和毛主席在湖南新军共过事,属于辛亥革命老人,如今年龄偏大,又没文化,不宜安排工作,请你们按照一般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待遇,每月发给一定标准的生活补助。
没有得到工作安排,彭友胜能理解,因为他此时已经67岁了,早过了退休年龄。他返回家乡后继续务农,但享受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从1951年6月起,省委统战部按月寄来30元生活费,一直到1967年5月文革把一切正常的秩序都打乱后为止。
对于毛主席的特殊关怀和省城领导的安排,彭友胜很是心存感激。据彭友胜的外孙夏建良回忆:
外公晚年生活还是无忧的,因为他每月有30元的生活补贴。这笔补贴还是源自毛泽东那封回信。
30块钱,在当年对于一个贫农来说,已经算是不少了,基本上都是参照国家工作人员的标准来享受待遇了。
衣食无忧,吃上“皇粮”的彭友胜心情激动无比,逢人就炫耀他与毛主席的往事,他想给毛主席做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彭友胜与老伴及女儿商议:毛主席待我们这样好,我们却没有什么礼物回报,他有喝茶的嗜好,我们不如就地取材,每年精制点上等茶叶送给他,表达我们的心意。
全家人纷纷表示同意,全员出动,在自家的一片坡地上开始侍弄起了茶林。彭友胜一家人每年会将自制的优质谷雨前茶包好缝牢,用挂号邮往北京,这一送就是整整18年。
毛主席每次喝到新茶,都不忘提醒办公厅的同志们:记得回信。所以,每一次送完茶叶后不久,彭友胜都会收到办公厅的回信:“友胜先生,你寄来的茶叶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某年某月某日。”
1960年,湖南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纷纷深入群众体验生活。著名作家叶蔚林到衡山一带采风时,听到彭友胜精制茶叶献给毛泽东的故事,顿时来了激情和灵感,赶写了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的歌词:
桑木扁担轻又轻呃,我挑担茶叶出山村, 船家问我是哪来的客,我湘江边上种茶人……
叶蔚林将歌词交给作曲家白诚仁。白诚仁读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只用了一个小时,曲谱就写出来了。

《挑担茶叶上北京》创作出来不久,总政歌舞团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和中央首长演出,歌唱家方应暄演唱了这首歌,毛主席听了特别高兴。后来,这首歌经何纪光演唱,在神州大地传遍了,至今还在这片天空回旋。
1969年11月23日,彭友胜再也不能为毛泽东制茶、寄茶了,85岁的他不慎落水,告别了人间,留下的是两个革命军战友的故事。
彭友胜不幸离世后,永远安息在了湘江边畔。1984年,中共衡东县委统战部修葺了他的坟冢,并为他立碑,他的坟冢位于普通百姓家的坟冢中,显示着他的平凡与不凡。
墓有石栏相围,水泥盖面。东面那块石碑上除刻有一般百姓人家“显考某公”之类文字外,还刻有一副对联:“拔剑掀戈除弊政,徒伤风水讨群奸”。墓前另一块碑上刻有“辛亥革命新军四十九标二营代表彭友胜永垂不朽”、“1984年立”的字样。立碑者为“中共衡东县委统战部”。
结语
毛主席是一个特别念旧情、念亲情、念友情的人,但他坚守亲友交往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
可我想说的是,毛主席的力量感并不神秘,来自于他的人民情怀,对人民朴素的情感深深感染了亿万人民,这看起来简单,但一生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的只有毛主席,而毛主席与彭友胜感人至深的点滴交往完全阐释了“我是你的一个兵”的伟大含义。
毛主席离开我们至今已经45年了,45年的沧海桑田、风云变幻,令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变的永远都是毛主席散发出来的伟大人格魅力,以及他与“老班长”质朴的友谊传奇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代人永远以毛主席为榜样,不断为国家、为民族砥砺前行,燃烧自己、照亮明天的美好希望。
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人民的好领袖毛主席!人民永远爱戴您!
注:本文绝大多数史料来源于彭友胜的外孙夏建良的回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同斯诺的四次谈话》等,内容翔实可靠,有据可查,以飨读者。
我是历史侦查处,下期精彩内容,我们再见,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订阅公众号历史侦查处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