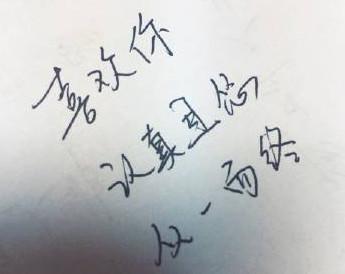农村的老汉们(村里的老汉们)
一心无着落,坐卧不宁,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农村的老汉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农村的老汉们
一
心无着落,坐卧不宁。
随着年轮的一圈圈递增,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幻觉。想象自己置身于某个原始村落里,阳光下,几个老人在推石碾,我走过去帮他们推,和他们唠家常。我扒着碾杆转了一圈又一圈,总也转不到头,随着石滚的转动,红红的高粱被碾成了白色的粉末。想着想着,我陶醉了,陶醉在温馨的场面和清香的气息里,陶醉在这片淳朴之中。
此时的我,就像进入了一种禅境,迫不及待地想躲进群山环抱、人烟稀少的大山深处,放下浮躁的心,来到村里的老人们中间,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
听着听着,我朦朦胧胧地走进了童年的某个时段,小时候熟悉的情景,有灵有性地在我的脑海里再现出来,我闭上眼睛,静静地去寻找那些残留在梦中的记忆。
由于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家人在外地,回到家里感觉空荡荡的,好在单位安排我离开总部到分部上班。分部设在距离总部四十多公里外的小城,那里也是我的老家,我的父母亲人、同学还有儿时的伙伴都生活在那里。距离的拉近,使我和他们有了更多交往的机会,也因此冲淡了我独处时的孤独,所以,对我来说到分部工作也是一件好事。
在这个让我们哭让我们笑的人世间,我们读到过各种各样的心灵鸡汤,每种鸡汤喝起来都有滋有味,只恨自己知道得太晚。当我们天真地按照鸡汤去处理事务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会变得一团糟糕,那些鸡汤虽然好听,却一点都不实用。
实际上,是鸡汤把我们灌醉了,以至于我们糊里糊涂地错把忽悠当成了翡翠。当我们清醒过来以后才意识到,岁月静好只是片刻,一地鸡毛才是常态。
其实,人的一生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到了什么年龄,就要办这个年龄该办的事,只有做好当下的事,才算完成了当下的积累,当然这个积累光靠努力是不行的。曾仕强教授说过,如果努力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会成功,努力只是一个人的本分,要想真正拥有必须用心而不是努力。
曾经拥有过,你才能淡然谈放下。亲身经历过,你才有资格谈看破。
我们穷尽一生追求温度,渴求做有温度的人,遇有温度的事。当遇上真正有温度的朋友,虽然不经常见面,但每次想起他,内心总是温暖的,由于他的存在,自己的生活会变得有声有色。
自从来到分部工作,一到休息日,那几个有温度的狐朋狗友就会打电话过来,约上我一起来到田野乡间,去体会那真诚、朴实的气息。去的次数多了,我们也因此走遍了周边的村村寨寨和山山水水。
留在村里的大部分是老年人,年轻人很少。那些比较大一些的村子,还能看到几个年轻媳妇带着她们的孩子在走动,偏远一些的山村几乎就只剩下几个老人了。这些留守老人,是山野里一道靓丽的风景,也是最后的守望者。当你融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会让你看到孩童时代的自己。这个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地从心底发出由衷的感慨:
风景依旧在,我已非少年。
二
这里是太行山上一个比较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山区农村一样,留在村里的大部分是老年人,年轻人大都离开了。
村子距离城里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距离大路边三公里左右,大路边上就有很多通往城里的乡下公交,水泥路一直通到村里的街街巷巷,交通十分便利。村里的老人们都营务着几亩农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自在地享受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崔江明是生产队的小队长,由于他在家排行老三,所以大家都叫他崔三。崔三是一个地地道道劳作了一辈子的老农民。改革开放以来,他除了种地以外,还在家门口开了一个小代销店,虽然生意一般,但也能见几个活钱。
勤快的崔三在代销店门口摆放了几根砂石条,他把砂石条和门口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里阳光充足,又是背风的堂屋,村里的老汉们几乎每天都会来到这里,天南海北、唾沫四溅地胡吹上一通。然后,再听别人胡吹,自己就半闭上眼睛,悠闲而贪婪地享受着冬日清新而温暖的太阳光。
几年前,村上有个不错的煤矿,开采手续都很齐全,虽然是外面的大老板承包着。但是,逢年过节,煤矿上也能给村里的老百姓发一些大米白面和食用油。秋末冬初,天气转冷的时候,按人头每人分上一吨细煤和一吨炭块,过年的时候还给每个人两千块钱。因此,这里的老百姓不像别的村民那样过分清贫。
后来,政府为了优化煤炭资源配置,实行有序开采,进行资源整合。他们村的煤矿被关闭了,但是资源还在他们村的地下。虽然坑口开在了外村,但是开采的还是他们村的资源。经过和煤矿所在企业的讨价还价,最后,企业答应给他们村一小部分股份,村里每年都能从煤矿分到点红利。当然,现在煤矿上给的这点红利,远远不如当年坑口在他们村里时多,老百姓分不上钱了,但逢年过节也能分到点米面油,冬天还能给点煤炭。
尽管不多,但是所有这些“福利”已经足以让几个临村的老百姓们羡慕的不得了。周围村子的老百姓们都在挖空心思,纷纷动用各种亲戚关系,想方设法地在这个村子给自己的闺女找个婆家呢——就是能嫁给个离过婚的男人也行。
尽管这样,如果家里多个上学的孩子,日子照样是紧巴巴的过着,没有一点多余的,有时候还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很多人家宁可受些冻,也舍不得烧完那些分配下来的煤炭。他们只留很少的一部分让自己过冬取暖用,把其余的全都在煤矿上直接兑换成了现钱。
由于老汉们每天集聚在这里晒太阳聊天,渐渐地,崔三家门口就自发地形成了村里的“文化中心”和“新闻中心”
村里大部分的新闻都是通过这里发布的,就和设在凤城电视台旁边的那个新闻发布厅差不多。不一样的是,这里不收一分钱的费,凤城那个还要收费。
这里也是全村的正大门,进入村里的行人和车辆大部分要经过这里。所以,这里发布的消息,不仅及时,而且会很迅速地传递到家家户户的老老少少耳朵里。人们在这里晒太阳闲聊的同时,就能知道村里和外面的很多大事小情。
老汉们中的部分人,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工作了几十年,现在叶落归根,告老还乡,又和孩提时代席屁股长大的伙伴儿耍到了一起——真是世事轮回啊!
不管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干部,只要是退休回来的人,村里的老百姓们都统称他们是“老干部”
从穿戴上就能分辨出他们的身份来,那几个穿戴比较整齐,白净的脸,背梳着花白头发而精神饱满的老人,就是告老还乡的“老干部”。而崔三和老黑这些明显是穿着儿孙们退下来的旧衣服,古铜色的脸,就像是荒草一样卑微,手上布满老茧的人,一看就是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庄稼老汉”
孙有胜老汉虽然也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但是,由于有个出息的儿子,多年来,他不愁吃不愁穿,零花钱也十分充足。所以,他也相当幸福,生活水平不亚于那几个领着退休金的“老干部”
老汉们平时都是闲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有时候,他们也根据自己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星半点儿新闻,有一茬没一茬地谈论一些美国新冠病毒的泛滥和北京冬奥会准备情况等国际国内的大事。虽然,知道内情的人听上去有点离谱。但是,他们谈论的气氛却是那么的热烈,没有半点的虚假。
当然,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他们目前面临的最现实的事情——儿孙们对自己的孝顺问题。
那几个“老干部”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退休金,不管儿孙有无在外工作,他们不用花儿子们的钱,孩子们对老人一般都比较孝顺。有几个领着高工资的退休教师,还倒贴给自己的儿子钱呢,在半上午的时候,常常看到他们的儿媳妇,端着一碗放了白砂糖、冒着白雾的冲鸡蛋,满大街地寻找自己的公公呢。给老人增加些营养,多活几年就能多挣几年工资,一年六七万呢,比自己的男人出去打工挣得还要多。
而那些庄稼老汉们就不一等了,有的,儿子在外打工或做些生意赚了钱,经济状况比较好,不在乎自己老人多花的那几个钱,吃的喝的花的都能让老人得到满足,也显得子女比较孝顺。
而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只是靠营务那点庄稼养家糊口,再没有别的额外收入。自己小日子的生活都十分困难,如果再娶上个厉害的老婆,也就很难考虑对老人的孝顺问题了,只要自己不再给老人添麻烦就算不错了。
大家最羡慕的是孙有胜老汉,有胜的儿子小飞从小就出去工作,现在已经是单位的头了。经常小车来小车去的给有胜老汉送些钱和生活用品,听说小飞也快退休了。
当年,集体经济时,土地还没有下户。有胜是大队干部,和公社的领导们很熟悉,他通过关系,把自己的儿子小飞安排到公社农机站当了个通讯员。通讯员的工作,其实就是给农机站的领导们打扫打扫办公室卫生,收发收发报纸和信件,闲的时候再到食堂伙房帮帮大师傅的忙。
小飞继承了有胜的优点:聪明勤快、脑子灵活。因此,很受农机站领导和那些拖拉机驾驶员们的喜欢。勤快的小飞还经常帮助拖拉机手擦洗擦洗机器,借机会就坐到驾驶楼里握住方向盘试一试,还十分谦虚地向驾驶员请教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
工作两年后,小飞不仅学会了做饭,还学会了开拖拉机,当然,只是会开并没有驾驶执照。
几十年来,聪明的小飞辗转在很多单位工作过。而且,都是一些不错的单位。慢慢的,他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由一般工人转为国家干部,再由一般干部成长为中层领导,在他48岁那年就成了单位的一把手。
他成了单位的一把手以后,除过自己的父亲,村里人见面,再也没有人直呼小飞了,而是改叫其大名孙鹏飞了,庄稼人还不习惯称呼他孙主任。
经过几十年的打拼,孙鹏飞不仅仅坐上了单位的第一把交椅。听孙有胜老汉说,自己的儿子光商品房就有好几处呢,还把他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了大学生,毕业后去了大城市工作。唉,想想自己那不争气的儿子啊,你们小两口住的房子还是我这把老骨头给你们盖的,比比看看人家小飞——哼!你们也不嫌脸红。
孙主任对父亲很孝顺,他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要从城里回到老家来,和父亲一起住上一两个晚上,他妈早年前就不在了。所以,他把孝心都给了父亲。平时口碑就不错的他,现在在这些大伯大叔面前更加谦虚了,除过穿戴很讲究以外,村里人看不出孙主任有半点官架子。
他操着地道的家乡土话给老汉们一人发一支“软中华”,老黑正抽着自己的旱烟腾不出手,小飞就把一支软中华夹到他的右耳朵上。孙主任的这些家乡土话和农民举动,让老汉们感到十分亲切和随和。
再比照一下秦家圪洞秦全顿家那个能不够的二小子,在西北当了三天兵,回家探亲时就说上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了。和别人说到全顿时,不说“我爸爸”而是改说“我父亲”了,真是给秦家老祖宗败透兴了——村里人都在背后嘲笑他。
秦全顿自己也感到脸红,气得全顿回到家,全然不理会他老婆的劝阻。狠很地臭骂了自己的二儿子一通:你个败家子的,以后不准你在众人面前丢人显眼了,你不知道,人家都在背后笑话你祖宗呢!
他儿子还不服气:
“部队首长要求说普通话的,这是纪律”
“纪律个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那么高级别的首长还是说的家乡话呢”全顿说。
他儿子干脆不和他争吵了,每天依然在村里说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
上个礼拜天,孙主任回家来看望自己的父亲时,还拿着长镜头的高级照相机给老汉们照相呢,听说光那个长镜头就八千多块呢。
能免费照相,老汉们一个个纷纷回家换上体面一些的衣服,刮了刮已经很长的胡子,高兴的合不住嘴。
照上一张标准的“人头像”再装上个木头框,等自己死了以后往棺材前面摆放,省得以后孩子们给自己花那个冤枉钱。
好几个礼拜了,村里的老汉们一直没有看到孙主任那辆黑色小卧车路过村口的“文化中心”开进村里来。
就是这件很普通的事,让习惯了每个星期五的下午都能看到孙主任的小车开进村里来的老汉们多少有点纳闷——孙主任可能到新马泰考察去了?
崔三打扫完小卖铺前面的卫生,往墙上挂扫帚的时候问有胜老汉:
“这几天怎不见你儿子回来呢”
“小飞说身体不舒服出去休养去了,他走时说需要休养好长时间呢”有胜回答。
又过了几天,还不见孝顺的孙主任回来看望自己的父亲,就连81岁高龄的孙有胜老汉本人也感到不可思议,儿子休养也应该打个电话回来呀。
实在耐不住性子的有胜老汉,第一次主动拿起家里的座机给儿子打电话。平时老汉舍不得浪费自己家里的电话费,也怕影响儿子的工作,一般都是儿子打过来,小飞用的是公家的电话。
可是,拨了好几次号码,电话里说话的一直是那个声音很好听的女人“对不起,你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候再拨”
老汉心想:可能是小飞的秘书在说话,小飞现在有事让他等一会儿再拨。
“臭小子,你的儿子都三十多岁了,还找个女秘书,也不怕你老婆吃醋”下次回来我得好好说说他。
几天来,有胜老汉不停地拨打儿子的手机,可里面一直是那个声音很好听的女秘书在说话,儿子就是不接他的电话。
着急的有胜老汉就去问出嫁到本村的女儿他哥哥的情况,女儿当场也拨了一遍他哥哥的手机号码,还是那个声音。
就对她爸说:“估计是向我哥请示汇报工作的电话太多,为了安静休养,我哥肯定是专门关着机呢。那不是女秘书说话,是移动公司的语音提示”
老汉这才放下心来,原来小飞没有那个花花肠子——差点错怪了儿子。
后来才听说,小飞那段时间是去参加一个由各单位一把手才能参加的保密培训会议,因为涉及到一些政策调整方面的大事,怕走露了风声,所以就把他们的手机都屏蔽了。
有胜老汉那颗悬着的心这才平静下来。
孙有亮是孙有胜老汉的本家兄弟,在凤城塑料厂当了一辈子工人。前几年就退休了,去年才回到了老家居住,一双儿女早已结婚成家,都在凤城市里参加工作,另起炉灶,过上了自己的小日子。
本来,退休后的孙有亮老汉和儿子孙鹏宇一家,生活在当年塑料厂分给自己的家属楼里,房子早已经买下归个人了。可是,自从前年老伴去世后,老汉什么家务也不会做,还得儿媳妇给他做饭。儿媳妇就有意无意地故意找茬和自己的女婿生气,其实是专门让老汉看的。
受不了这份窝囊气,有亮老汉就雇上本家的亲戚们,把自己多年不住的老房子收拾了一下。又买了一车煤球,搬回村里居住了,他回村居住后人家小两口再也不生气了。
尽管儿子不忍心看着老父亲一个人住在农村的旧房子里,可是又纠缠不过自己的媳妇。没办法,在有亮老汉的主动要求下,孙鹏宇很不情愿地同意了他父亲回老家居住。不过,儿子鹏宇也很孝顺,他轮流倒着上班,休息时间不固定,每到休息的时候,他就会买上一些生活用品给父亲送来。
孙鹏宇当年是接替父亲的班,在凤城塑料厂当了工人的,他和父亲孙有亮一样,也是个普通工人。鹏宇每次回老家时,都是坐上从城里开往东山后的乡下公交车,在村南边半山腰的公路边上下车,再沿着沟里的小路步行回村里。
他进村时不走村里的“正大门”,而是由村南边的“偏门”进入村里,以躲避“文化中心”那些老汉们拿自己和孙主任作比较。
老实人孙鹏宇有时候也自我安慰:我比不过他孙鹏飞有本事,难道还比不过你们这些臭老汉,起码比你们年轻——哼,年轻就是资本!
孙鹏宇和本家哥哥孙鹏飞同在凤城市工作,由于两个人地位的悬殊。孙主任交往的圈子大部分是当官的和那些有钱的老板们。孙鹏宇来往的除了和自己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外,其余大部分朋友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普通工人阶级。所以,鹏宇和鹏飞虽然同是一个孙姓老祖宗,平时来往并不多。
不过,孙鹏宇如果遇到什么不好办的事,需要本家哥哥孙鹏飞帮忙的话,只要他找上门来,孙主任都会尽力帮助。这一点,让没本事的老实人鹏宇非常感动。
那年鹏宇的女儿中考时分数考得不理想,能到市里最好的凤城一中读书就是孙主任找人办妥的。在不知内情的外人面前,老实人孙鹏宇也知道不失时机地吹嘘——孙主任是我哥哥。
除过孙有亮老汉心理清楚自己是因为什么原因要回家养老外,其他老人们都还想着他是感觉老家清净才回来住的。
就这样,老汉们每天依然来到“文化中心”,他们悠闲自在地一边抽着旱烟,一边晒太阳,一边海阔天空、唾沫四溅地胡吹着。有时候,他们也起起哄,将那几个领着退休金的老干部一军,要求老干部在崔三的小卖铺买上一盒五块钱的“红旗渠”烟给大家一人发一支。
日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过去,老汉们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多么富裕,但除了自己种的庄家,村里每年还给发给些大米白面,倒也十分自在——知足常乐嘛!
像老黑和崔三这些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他们劳动的本性刻在了骨子里,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们,宁肯舍去自己的老命,也不愿意荒芜掉一小块田地。他们像守护自己心爱的女人那般,憨厚、虔诚地守护着他的庄稼。直到有了沉甸甸的收获,他们从不贪婪,每一分收获都是那样的实实在在、清清白白、坦坦荡荡。他们总是佝偻着身躯,肩扛着锄头,屁股后的裤腰带上插着旱烟袋,高贵地活着。
到底怎样的生活是幸福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说,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看法:
我饿得饥肠辘辘,看到别人吃着大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
我冻得瑟瑟发抖,看到别人穿着羊皮棉袄,那他就比我幸福。
“大雪纷纷落,我住柴火垛,看你们穷人怎么过”这是一个找到了栖居之地的乞丐对幸福的理解。
村里的老汉们认为,像孙主任那样,穿着名牌衣服,小车接小车送就是幸福。可是,当了多年官的孙主任却有些厌烦,官场上套路太深,很多事情弄得他不开心,有些事情还让他烦不胜烦。他十分地羡慕他们村里那些自由自在,穿着儿孙们退下来的旧衣服,坐在崔三家门口的石头上,抽着五块钱的“红旗渠”香烟,晒着太阳,胡乱吹嘘的庄稼老汉们——你们多幸福呀!
由于种种的不甘心,人们都在尝试着通过各种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其结果大都是两败俱伤。因为,在自己无法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总是无休止地扩大着实现这个目标的好处。有时,甚至在内心深处把这个目标神话了。而当你真正得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你依然会觉得这个目标不是你期待的那样好,人性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
三
冬天过去,春天来临。在冰雪融化的差不多,天气逐渐转暖的时候,村里突然来了一帮操着普通话的外地人。
这些人说的普通话听起来那么顺耳,比秦全顿家那个能不够的二小子说的普通话好听多了——那小子是个冒牌货!
好几天了,那些外地人每天早饭后就坐着小车,由凤城市委宣传部的领导陪着来到村里,他们在村里各个角落转悠,指手画脚的。还时不时地到老黑家里坐坐看看,问长问短的唠上一会儿家常,说上几句客气话,就像是上面的领导来农民家里调查研究。
老黑和他那个虽然不识字,但平时在街坊邻居面前很爱说的老婆,面对这些外地人,却什么话也不会说了,只是竖着耳朵听人家说。就像机关的干部们听他们的领导作报告一样,并不理会讲的什么,只是做出认真听的样子,她时不时地张开大嘴,露出黄牙陪着人家笑笑。
老黑家住在村的最东头,那里是村里修建的第一批排房。七十年代的建筑,统一的五间平房,灰蓝色的砖和瓦。街道的东西两边都是两家紧挨着的那种房子,两家走一个大门。
两个院中间用低矮的花墙隔开,这样看起来各是各的院。再往东就是土墙,土墙上面就是农田了。当年,这些房子很让村里人眼红了几年,现在有点落后了。
老黑家就住在东边的院子里,他不是那种十分贫穷的家庭,但也不富裕。
那些外地人还专门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来到他家,看看老黑老婆做高粱面黑圪条。还争着一人吃上一碗,弄得饭不够自己家人吃了,老黑他老婆还得重新给家里人做。
不过,这些人也真够意思,每次吃完,走的时候还给她放到那张已经掉了红油漆的方桌子上一百块钱。尽管她不好意思收人家的钱,可他们还是硬要放下。
那个年轻漂亮的外地女人还俏皮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不能白吃群众的黑圪条。
多么好的同志啊,八路军又回来了!
那些外地人在村里转悠了好几天,把村里的角角落落都转了个遍。他们走了以后,老黑在“文化中心”传播了一个令人欣喜若狂的消息:要在咱们村拍电视剧了!
啊呀!咱们村居然要上电视了,人们像炸开了锅一样惊讶。
果然,在老黑传播消息的第二天,那些人扛着三角架、摄像机、聚光灯等各种设备浩浩荡荡地进村了。
没有谁刻意安排,村里的大人小孩都争先恐后地帮助他们扛设备、搬家具。没有多少力气的老汉们也帮助拿一些比较轻的道具和演员服装之类的东西,寂静的山村顿时沸腾起来了。
拍摄地点主要选在村最东头老黑家那条街,听老黑说他家里也是主要的拍摄现场。
原来,是黄河影视文化传播中心、省电视台和凤城市委宣传部。要联合拍一部反映黄河儿女在党的富民政策鼓舞下,发展农村经济,告别贫穷和落后,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历程,充分展现党的惠农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的电视连续剧。
因为老黑家居住的那条街和老黑的家里面布局很像七十年代的情景,符合剧情需求。通过市委宣传部和村委沟通,决定就在这里拍摄。听说还要给老黑家付钱呢!真是天上的大馅饼掉到这个老家伙头上了。
老汉们纷纷起哄,要求老黑请客,心里正偷偷高兴着的老黑,很大方地在崔三的小卖铺买了一包“红旗渠”给大家一人发了一支。
在开机之前,剧组的那些人先把原来用石灰喷成白墙的街道两边重新用涂料涂成了灰蓝色。又把老黑家和邻家之间的矮花墙拆除,两个院变成了一个大院,大院里面也涂成了灰蓝的颜色。
正式开机那天,大人们忘记了下田干活。村里的小学也给孩子们放了一天假,让学生们感受一下先进文化的诞生过程。
村里的人们都怀着激动和稀罕的心情来看拍电视,“文化中心”也由二蛋家门口临时转移到了老黑家这里。
这几天,崔三家小卖铺的生意萧条了许多,销售额直线下降。气得他老婆不停地嘟囔:一个破山村有什么好拍的,要拍也应该来我们家门口拍呀!难道这里还比不上他老黑家红火——她哪里知道光红火是不够的。
拍摄现场,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老黑和临家的两个院落挤得严严实实。看看那些演员,穿戴的都是很过时的衣服,光他们这些演员人手远远不够,还需要村里一部分人当群众演员。
啊呀!我们也有机会上电视了。
人们高兴得争先恐后地来到导演面前,要求当群众演员,那几个女人还专门回家换上了漂亮时髦的新衣服让导演挑选自己。
可是导演说:衣服穿得不合适,要穿旧一些的服装,七十年代时候的穿着打扮才行。老黑、崔三、孙有亮这几个穿着旧衣服的老汉们反而一眼就被导演选中。
能上电视,老汉们一个个高兴得像孩子。真是赶上好时候了,以前天天在电视上看别人,现在居然要在电视上看到自己了。
开拍的时候,那些职业演员穿插着“混”在老黑、崔三和孙有亮这些群众演员里面。如果不说话,单从穿戴上根本看不出谁是专业演员谁是群众演员。
导演交待崔三老黑他们这些人,你们可以有鼓掌、大笑、咳嗽、抽烟等动作。但不要说话,真正说话的是那些专业演员。对了,抽烟要用烟袋锅抽旱烟,不要抽现在带过滤嘴的香烟,也不要用打火机点,要用火柴点烟。
噢,原来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电视剧都是这样拍的啊,怪不得电视剧里老是那几个人说话呢,其他人就像哑巴。
不让说就不说吧,反正能上一回电视就已经很满足了。
剧情里还有一段需要拍摄在老黑家吃黑圪条,还要拍老黑老婆擀面的镜头。哎呀!老黑那个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太婆竟然也要上电视了——真是让人笑掉了大牙。
现在想起来了,前几天那些人来老黑家专门吃黑圪条,原来是为了拍戏体验生活呀!
就像正式上班一样,那些老汉们和村里的其他年轻人每天按照剧组要求。准时来到老黑家,和那些专业演员一起演戏。
多美的差事啊,不仅能上电视,听说完了剧组还要按天发钱,一个人一天二十块呢!
这几天,崔三因为赶着上镜,顾不上照看自家小卖铺的生意。她那不识字的老婆一不小心收了一张一百块的假钱,她老婆说这一百块钱是二愣来买“红旗渠”时给的,可二愣死活不认账。
村里人都知道二愣脑子有点不够用,气得崔三狠狠地骂了他老婆一通。不过他又想开了,当群众演员按一天二十元计算,五天了也挣回这一百元来了——不要和二愣这样的人一般见识。
电视剧拍了三个月还没拍完,听说有些戏需要冬天有雪的时候才能拍。人们由开始的好奇,众人围观,到现在逐渐淡化,不稀罕了。再也没人去看热闹,人们各干各的事去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人们等待着将来在电视上好好看看,看看在自己村里拍的电视剧是什么样的。看看那些龇牙咧嘴的老汉们的“光辉形象”——哼!多么可笑啊。
四
现在的农村和城里差不多,通了有线电视,还有无线网,八十多个频道的节目丰富多彩。可是,老汉们除了喜欢看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外,对其他节目没有什么兴趣,基本不看。
他们倒是很喜欢听说书,七十年代的时候,村里很穷,那时候也缺乏文化生活。收完秋人们闲下来的时候,常常能看到一遛盲人在乡间的小路上行走,他们由走在最前面的一个稍微有一点微弱视力的人带路,其他人一只手拿个乐器,另一只手托着前一个人的肩膀。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条蜿蜒的蛇慢慢向前移动,他们慕名来到村里。
善良的庄稼人纷纷放下手头的活计,接过他们手里的家什,招呼这些看不到光明的可怜人来到大队部,安排他们住在大队部的庙宇里。再由大队起灶,大队保管给这些人做上酸菜手擀面。
那些盲人在这里一住就是好多天,他们每天晚上总是很认真地把最拿手的好书献出来,让那些当年还年轻的老汉们听得如痴如醉、回味无穷。
最后离开的时候,如果村里有钱,就给上几个零钱。如果没有也就算了,能在这里住下和吃上饭,这些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直到现在,老汉们还十分怀念那时候盲人说的古书。
现在的说书和从前大不一样了,除过内容是现代的了,有点和唱戏差不多。再也没有盲人宣传队来村里了,大队也不专门安排说书了。
现在村里说书,一般是谁家给老人祝寿,孩子满月,老人老了喜丧等等时候。私人自家请上民间说唱团来说唱上几天,条件好的人家还要请上两班说书的唱对台戏呢!
这天,是张老太太的八十五岁生日,老太太的老伴三十年前就离开了人世。经过几十年艰难的日子,老人受了无数的罪,如今,老太太的儿子也六十多岁了。孙子孙女都很争气,国家恢复高考后的几年里纷纷考上了大学。现在,孙子已经是单位的二把手,孙女也是一个机关的科长了。
和以前艰难的日子相比,张老太太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孙子们倡议,今年要请上最好的长子民间说唱团唱上三天,好好给奶奶庆祝一下大寿。
听说光请说唱团就要花费五千多块钱呢,老人家死活不同意。老太太想:那些钱要买多少白面呀。唉,过惯了苦日子的老人,怎么舍得花那么多的钱来为自己祝寿呢?
孙子孙女和自己的儿子都没办法说服老太太,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哄骗老太太。和她说那些说书人的头头,是孙子单位同事的一个亲戚,光管饭就行了不用出钱,老人这才疑疑惑惑地勉强同意了。
长子县的民间说唱团,在当地和周边的县市里都是很有名气的,那些说唱团现在已经发展成了有限公司。听说今天要来村里演出,老汉们高兴得不得了。他们早早就吃完晚饭,拿上烟袋,戴着老花眼镜,扛着板凳,来到搭在崔三家门口“文化中心”的简易舞台前面——要站个当中的好位置看得清楚。
晚上这么多人,崔三的小卖铺生意肯定会很好。本来,崔三应该好好照看自己的生意。可崔三是个老戏迷,权衡利弊,他还是觉得看戏要紧。于是,他早早就用自家的板凳占下了最当中的位置,气得他老婆狠狠地咒骂他:
哼!离开你,天照样刮风下雨,女人照样生娃娃!
舞台上,长子的那些男男女女正在安装和调试音响,他们时不时地拿起唢呐对着话筒吹一吹、试一试。这工夫,老汉们纷纷拿出烟袋抽起了旱烟。他们吐出的烟雾,经过舞台前面的聚光灯照射,就像夏天落山的太阳照出他们烧麦秸时的烟雾一样,分外缭绕。
姑娘媳妇们站在老汉们的板凳后面,天南海北地聊着天,孩子们你追我赶地嬉闹着。
今晚,这个山村又将是一个乱哄哄的不眠之夜。
演出开始了,台上先唱了几首流行歌曲,老汉们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倒是姑娘媳妇们很乐意听,他们还时不时地跟着舞台上唱得正欢的那个女人小声地哼哼着。
舞台上的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好不容易唱完了三首歌,接下来,她说还要再唱一首当下比较流行的歌曲《听闻远方有你》
坐在下面的老黑着了急,对着上面喊道:
“我们不听《听闻远方有你》,我们要听上党梆子,快唱上党梆子吧”着急听戏的老汉们都随声附和着。
上面的演员倒是很听话:
“大家静一静,我们就唱上党梆子”
换了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女人来唱上党梆子,那熟悉的锣鼓一响起来,老汉们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台上那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女人唱得还真不错,听得老汉们张大嘴巴,摇头晃脑,如痴如醉,也跟着在下面小声地哼唱着。
那些站在板凳后面的姑娘媳妇们有点心不在焉了。当然,也有个别爱好听戏的小媳妇们在静静地听着、哼唱着。
孩子们根本不管你唱什么,他们一直在你追我赶地耍闹着,还时不时地拿出和父母要来的两块钱,到崔三他老婆那里买上几根辣条吃一吃——童年真好!
从晚上八点开始演出,现在已经十一点了,演员都唱得累了。台上想结束今天的演出。可是,下面黑压压的人群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
他们纷纷朝台上高喊:
“再来一段、再来一段”
姑娘媳妇们的喊声是:
再唱一首《如果爱还在》
老汉们也不甘示弱:
来一段《皮秀英打虎》
有的小媳妇不知道自己的公公坐在前面,刚喊完,就听到自己的老公公也在前面喊,羞愧的红着脸赶紧离开了。
台上的演员不知道该听谁的,他们只好由年轻女人唱完《如果爱还在》再由那个老一点的女人唱《皮秀英打虎》
就这样,一首歌一段戏的一直唱到晚上十二点,直到张老太太的儿子走上台出面对众人进行劝说,才结束了今天的演出。
整整四个小时,老汉们都没舍得离开自己的坐位,憋了一包尿不说,老胳膊老腿的都坐麻了。
“老干部”孙有亮由于一辈子在城里享福,缺乏劳动锻炼,两条腿麻木的都站不起来了,老黑和崔三这两个“庄稼老汉”一人架着他一条胳膊硬把他扶了起来。
唉!想当年,豪情壮,顶风随便尿三丈。现如今,中了邪,顺风使劲尿一鞋——岁月不饶人啊!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汉们的生活依然如故,他们信奉着知足者,心常乐,能忍着,身自安的道理。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大事小事,他们每天依然吃罢高粱面黑圪条,来到“文化中心”,乐呵呵地享受着太阳光的照射,海阔天空地胡吹着,依然抽着自己的旱烟。
在历史的长河中,村里的老汉们虽然都是些小人物,但每个小人物,都是大时代的缩影。我们都是现实中的凡人,由于观念不同,追求就不尽相同,人们总是为了太多遥不可及的东西疲于奔命,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在生命的旅途中,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渴求,只需要灯火阑珊的温暖和柴米油盐的充实。回头想想,那些曾经让我们惊天动地的哭与笑,不过是生命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寻常经历,就像我们随手拂过的尘埃一样,那些哭和笑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风飘去。我们曾热衷于教育别人,后来才发现管好自己比教育别人更靠谱。
2022年1月6日(高平)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