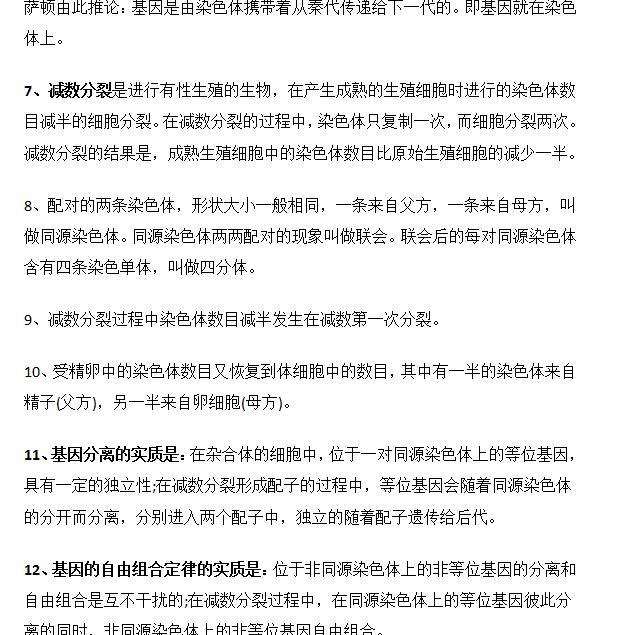张明敏对香港教育的影响(香港教育走过的弯路)
吴小莉:香港的教育问题,是有意还是无意发生?
黄均瑜:港英政府时期管得特别严,但随着它撤退,港英政府有意放松了对教育的控制。
吴小莉:你说过中学生的价值观,其实是不足的。
黄均瑜:所谓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在学生中占据了主流的模式。对于特别是未成年的学生,一些传统的价值观,仍然是一个基础。
本周专访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
黄均瑜

2021年8月10日,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宣布解散。其在2012年助推反国教风波。在2019年“修例风波”中,呼吁教师和学生罢课上街,这些举动严重影响了香港教育的正常运行。
教协解散后,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简称“教联会”),将承担起更多服务教师群体的职责。黄均瑜,自2014年担任教联会的会长。
起底教协,解散前为何壮大?
吴小莉:1973年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成立,1975年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成立。为什么教协成立之后,能不断壮大?
黄均瑜:他们有自己成功的方法。比如购置物业,他们比我们更有眼光。至于政府对教协的支持也比较明显,因为政府觉得教协代表着整个香港教育界。
吴小莉:您是说港英政府,还是香港特区政府?
黄均瑜:两个都是。
吴小莉:教联会在香港回归之后,都还没办法成为主流?
黄均瑜:这个当然是。因为政府以前的思维属于比较严守“政治中立”,所以在香港回归之前,教联会就被边缘化。回归之后,这个情况有所好转,它不将教联会边缘化了,但它还是严守中立,来平衡两边。就是说有教联的地方,就必然要有教协;有教协的地方,港英政府会去找教联会进行平衡。
放松对香港教育方面的管理?
港英政府,刻意为之

2019年香港爆发“修例风波”,近九千人被捕。其中四成是学生。
吴小莉: 2014年“非法占中”到2019年“修例风波”,有这么多学生走上街头。有人说尤其在回归之后,香港教育出了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均瑜:教育是责无旁贷的,但我觉得教育也不能背负所有的责任。因为学生所受的影响除了来自学校和老师,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学生受到了很大的外界影响。比如“占中”、“黑暴”,这些都不会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就算在学校里,有个别老师会做出一些出格的行为,我们分析过这样的老师不会超过1%。“黑暴”时期,教协提出要罢课,我们就提出不该罢课,要紧守岗位。我们看到绝大部分学校都没罢课,老师都能够紧守岗位。
当然老师的缺点或者我们的盲点就是,我们香港教育培养的老师是专业的,专业体现在他教的那一科目,但在政治方面对很多老师来说,的确不是他的强项,所以老师们会很容易受到传媒甚至社会风气等等的影响。
吴小莉:香港教育的一些细节问题,是有意还是无意发生的?
黄均瑜:大方向是有意的。港英政府对香港教育的管理是特别严格的,所以当时教育处处长的官位都比其他处长要高,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职位。
吴小莉:它们很明白,教育是改变人心很重要的一环。
黄均瑜:它们很重视对于教育的控制,但是随着它的撤退,有意地放松了对教育的控制,包括课程又不归政府管,是有一个课程发展议会,曾经还规定一定要请外面的人来做,不可以让公务员来做;教育学院现在变成教育大学了,以前教育学院是由政府管理,里面的教师是公务员,现在变成大学了,教育自主了;考试方面,又成立一个考试局,教育局又没得管了。
所以,课程、考试和教师,教育局全部都不管,全放开了。实际上,教育局能够管的方面越来越少,它鼓励的“代议政治”、“还政于民”,慢慢滋生了民粹的倾向,所以这个大方向上面就是有意为之的。
香港教育的主要问题:
泛通识化、考试、教师

吴小莉:你也提到如果是教育出的问题,通常是通识教育、考试,还有教师。通识教育没有教材、没有课本,都是来自报纸、媒体,这个情况可能造成了学生学习的碎片化,同时也造成了学生的政治早熟。
黄均瑜:通识科的弊病有很多,因为他只说正反,不讲对错,在历史科里面也出现这个情况,只说pros and cons, no right and wrong......这个对于年纪越小的学生影响就越大。因为在教育里,我们说价值观的建立其实是从小培养的,通识科所谓“通识教育”的理念它扩散到初中、扩散到小学,甚至有的扩散到了幼稚园,它都是用一个通识的倾向。
吴小莉:为什么会扩散到这么小的年龄段?
黄均瑜:通识教育成为一种潮流,它扩散到影响了所有科目。至于“碎片化”,这不只是通识科的问题,我觉得是香港课程里一个主要的弊病。因为我们会出现一些老师觉得难教的内容,我们就去掉它;学生觉得难学的或者没兴趣的,又去掉它。
吴小莉:物理、化学、数学如果难教就不教的话,那学生的基础就很差了。
黄均瑜:除了基础差,在每一科里面,如果学生没有一个很系统的逻辑思维的训练,他分辨是非的方式就是通过看人多人少,人多就是对的。为什么会这么多人会走上街?因为人多就是对的,人多就是真理。
再加上我们现在社交媒体、电子传媒等等都是碎片的,用一个标题去决定,现在没人看文章了,慢慢地一句夺眼球的口号就很容易挑起一些情绪,所以就会出现一些社会事件。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卷进去?因为他不能分辨对错,认为人多了做的事就是对的。
吴小莉:我不太理解考试也造成了一些问题,是因为考试的出题方式吗?
黄均瑜:考试一直都是一个指挥棒,基本法督导委员会就是要推广各个政府部门、全香港去遵守基本法。我当时提出一个意见,我说你组织多少活动,都不及在考试里出一道和基本法有关的题目。
吴小莉:这样所有的学生就必须读,而且要读透基本法。
黄均瑜:你不叫他看,他都会去看、去研究基本法,老师也一样。我提出这个意见,当时考试局同意了,它说需要一点时间,当时答应的是三年内就会有一道基本法的题目,现在三年又三年、再三年,那些考试局的人都换届了,我们还没有关于基本法的题目出现。所以,怎样用好考试这个指挥棒?当然,通识科它做了一个反面示范,里面很多的政治题目,指挥我们的学生走去了另外一个方向。
吴小莉:您提到中学生的价值观其实是不足的,尤其在责任感、坚毅和尊重他人的方面。为什么有这样的体会?
黄均瑜:现在的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开始式微。另外,一些所谓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包括一些所谓的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就在我们学生中占据了主流模式。但我始终觉得,特别是对于未成年学生,一些传统的基本价值观仍然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基础。
吴小莉:比如?
黄均瑜:我也批评香港教育局的十大价值观,现在列出来的没有孝顺。我们说百行孝为先,尊敬长辈,他将来才可以立身处事,而不是从小教他要自由、要平等、要公正、要改变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帮他打好基础,无论在家长、在学校都要坚持,不要让一些社会风气或者社会思潮带歪了。首先,做好自己,才可以改变别人,改变这个社会,追求更宏大的理想。
香港教材的编写,
让香港教育走了很多弯路

吴小莉:1998年您在福建中学(小西湾)做创校的校长。
黄均瑜:对,回归之前传统的爱国学校有几所,当时还是在港英年代,港英政府把它边缘化了,福建中学(小西湾)中学是回归以后,董先生首先批给了这个爱国团体。
吴小莉:因为董先生希望有“两文三语”,但是这个“两文三语”当中普通话的中文部分,是比较困难去找到教材的,所以您和您的同事们就开始编教材。
黄均瑜:比较成熟的就两套教材,一个是中国语文,一个是中国历史。
吴小莉:当时在学校自己编写教材,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吧?
黄均瑜:系统、成熟地编写教材是没有的,我们应该是唯一的。老师用空余的时间编写了这个教材,花了6年时间。当时语文的改革,我们发觉走了一段弯路,所以取消了课本。因为没有范文,大家自动就地取材。我们觉得就地取材不是一个可行的、有效果的办法,所以我们就自己编写了一个我们觉得合适的教材。
吴小莉:关于香港的历史教育,以前两种方法,“从香港看中国再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再看香港”。您觉得应该是“从中国去看世界”?
黄均瑜:举一个例子,我见过一个年轻人,他和我说他在香港的一间大学读中国历史,他那个教授和他说“抗日战争”是不对的,应该说“中日战争”,这样才客观。我听完之后火都上来了,我立刻说怎么可能,你跑来我家里打完、砸烂,又杀人、放火,然后就说两个人打架而已,怎么可能?
一位大学教授是这样看历史的,他是抽离的,他是一个“太空人”,没有了价值判断。“中日战争”、“抗日战争”是一个名词,但已经反映出我们历史观背后的问题。作为教育工作者,需要给学生一个清晰的“你作为中国人”的立场,从一个中国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做校本课程,本身也是老师学习的一个过程。
爱国教育,
如今可以理直气壮了
吴小莉:在香港回归之前,爱国好像并不是主流,甚至回归之后的前一段时间,你要讲爱国还要特别小心,有这种情况吗?
黄均瑜:肯定有这个情况。因为在香港就是我们爱什么都行,爱猫、爱狗、爱地球都行,但是爱国就不行,甚至成为一个禁忌,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所以,当时找我做校长,我有点“爱国,舍我其谁”的感觉,我们会努力地举行升旗礼,作为一个爱国的标志。
吴小莉: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坚守了这么多年爱国爱港的教育、服务教师的责任,终于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和认可?
黄均瑜:“爱国者治港”提出之后,特别是通过完善选举制度,确立了需要“爱国者治港”之后,整个香港的气氛都改变了,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去做了。

黄均瑜在纪念册写下,“润物无声”
吴小莉:作为一个老师、教育管理者以及一个教育联会的会长,您对于香港未来的教育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黄均瑜:“一国两制”是一个很独特的制度,怎样建立一个和“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这个需要一些技巧。比如说在“一国两制”之下,我们不会要求香港的学校,或者香港的教育向内地看齐,我们有香港的优势,但是我们也不是要完全脱离国家,而自搞一套教育。这两者之间,怎样取得一个平衡点?这应该是未来所有从事教育的、特别是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应该要去好好思考和实践的。

编导:梅苑
制作人:韩烟
编辑:马晋 张天放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