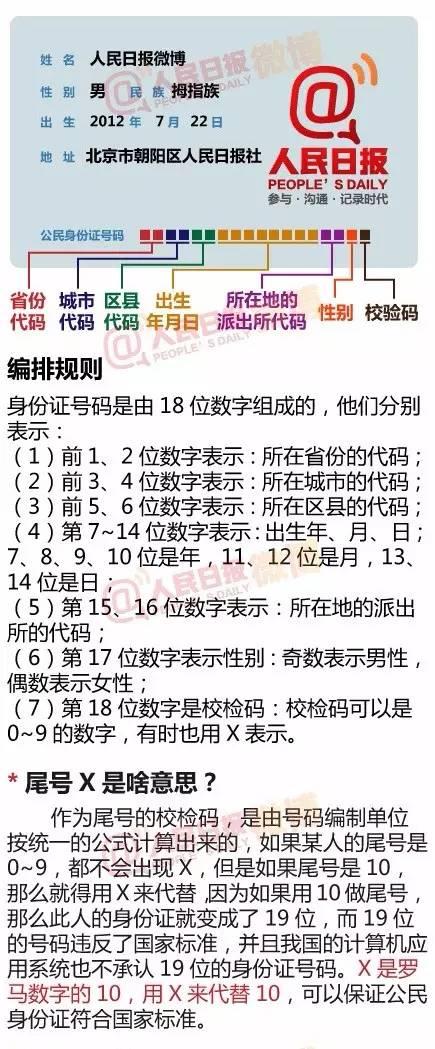晴空如洗霞光漫天(晴空万里如可托)

吕铁智、吕阳父子研究手工技艺






以上作品均为金马派风筝作品

吕阳正在制作风筝
前不久,北京金马派风筝第四代传承人吕阳首次以北京中轴线上的代表性建筑为主题制作的风筝,在一档京城大众文化节目中亮相。他用全新变脸的传统风筝讲述的中轴线故事,新鲜有趣,引发网友的关注和热烈反响。
三月九日,本报记者走进位于净土胡同的吕阳家,听两代传承人聊了聊金马风筝的那些事。吕阳生在胡同长在胡同,对胡同怀有很深的感情,用他的话形容,那是一种出了二环就找不着“气场”,看见鼓楼“就到家了”的依存感。午后的小院东屋,虽然空间不大、陈设简单,但听着那些悠长绵延的老北京风俗,触摸着传统风筝上的岁月纹样,满满享受到一份春日限定的风筝文化盛宴。
咬着牙试出来建筑主题的风筝
大家都说挺新鲜
走进吕阳家,不大的门厅被各式风筝、工具占领,墙上挂着、桌上摆着,连榻上也蹲着大风筝。他和父亲吕铁智坐着小马扎,围着小方桌,正埋头琢磨风筝课件。
一眼望去,吕阳新做的三个风筝十分醒目,钟鼓楼、正阳门、永定门端立其上,上面的建筑是他按照过去戒尺画的技法画的,每一梁一柱用毛笔画得非常细腻,“一拿出去,好多人跟着看”。起初是怎么想到拿建筑做风筝的?吕阳直言,有一次鼓楼人艺创始人方喆在家附近讲座,结束之后便和北京科教频道的李小芳导演到家里聊天,其间正好说起做一期中轴线的节目,大家就聊出这么个主意。“其实我原来问过老人,他们说北京建筑大多以灰、黄色为主,色调单一,不好表现。而且建筑是死的,改不了,不像做个沙燕,从外到里都能变化,艺术加工的空间非常大,所以从色彩、题材上,没人碰建筑主题的风筝。”不过吕阳还是想探索一下,他咬了咬牙,应声说试试。
吕阳先试做的是正阳门风筝。他想,正阳门过去是给老百姓立规矩的一个门,也是老百姓能够看到的规制最高的城门,便确定了“正午当空,金屋托日”的立意,“以前都说正阳门是四门三桥五牌楼,其实三桥就是一座桥,中间被分成三条路,中间走天子,两边走百姓。我画的时候,底下变成剪刀式的尾巴,不再是一个金屋,我觉得它以前是天子之门,现在是服务老百姓的了,这个功能性上的转换是非常值得表现的。”
第一个风筝做出来之后,反应不错,很多人看见都说“挺新鲜”,吕阳决定“干脆再来两个,钟鼓楼、永定门,一头一尾加中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几乎每一个风筝他都起码做了半年,一开始在电脑上用Photoshop(制图软件)设计就花了挺长时间。
随着想法不断修正,每一个风筝的图案都被推倒过数次。“比如一开始钟鼓楼是分开做的,我分别设计了钟楼和鼓楼。做着做着就觉得,大家一想到鼓楼,钟楼就出来了,一想到钟楼,鼓楼就出来了,钟鼓楼钟鼓楼,就跟老公母俩似的,一直在这待着,不能给分开了”。可是问题来了,怎么把它俩合在一个风筝画片上?琢磨半天,他想出用三维空间的手法表现,于是风筝上边画的钟楼,后边是鼓楼的影子;下边画的鼓楼,高出一块是钟楼的影子,出来一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钟鼓楼。”
吕阳直言,风筝的造型,学的就是老辈人沉淀下来的骨架形态,“有这些东西搁在心里,万变不离其宗”。刚开始他看父亲“咔咔”几刀就弄出来,就这点经验感觉他找了好长时间,“别的不说,这硬翅我最起码做到第50个的时候才有了感觉,再往后做的就都是样了。风筝放上去,它才能靠弹性自己在天上去找风劲。老传统讲究‘三停三泄’,每个形态的风筝都会有不同的停风面和吃风面,老祖宗已经在老架子上给总结出来了。做的时候,竹子的密度从根到梢都不一样,主条支撑风筝的整个结构、用于起飞。辅条用于塑形,要一边削一边凭经验去找它的弹性,即使风筝搁一段时间,每一步都可以调整,达到最佳飞行状态。”
2022年是吕阳入门学习金马派风筝技艺的第八个年头,他体会最深的就是传承的一定之规:风筝得从形、意、情、趣四个方面去欣赏,存二者为留,三者为传,四者为承。“四样都占着,才真正算得上传承”。作为年轻一代,和老辈人所不同的只是设计阶段,父亲用纯手工画稿,他则是用电脑软件设计,最后画片时手绘,除了画下来,他还要把画稿做成数字的,保存到电脑里。
“金马派”风筝两代人
共同制作了北影厂首部中外合拍电影《风筝》中的风筝
今年快七十岁的吕铁智清瘦儒雅,是金马派风筝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对金马派传承谱系如数家珍。清末民初,著名风筝艺人金福忠与近代工笔花鸟画名家马晋创立了“金马派”风筝,成为北京风筝的代表。京城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南城瘦腿子,北城黑锅底”,“南城瘦腿子”指的是南城哈记做的瘦沙燕风筝,“北城黑锅底”,就是指金家的胖沙燕风筝。
金福忠出身风筝世家,金家的“金氏三绝”——先糊后画、膀条一根成、骨架纸捻扎,很早就享誉京城。金家祖孙六代都在宫里的灯笼库供职,为宫廷制作风筝,“故宫现在还保存着三只宣统皇帝幼时玩过的风筝,相传就是金家做的”。清帝逊位后,金福忠在地安门火神庙摆摊售卖风筝。另一位创始人马晋自幼跟宫廷画家习画,马家也是京城风筝四大家之一,风筝以绘工笔重彩见长。马家与金家是世交,再加上马晋与金福忠都喜欢绘画,格外投缘,晚年时两位先生创立了“金马派”风筝。马先生的加入使风筝在绘画技艺上耳目一新,提升进艺术殿堂。
金马派风筝第二代传人关宝翔,由金福忠、马晋两位先生亲自教授,不但继承了金氏风筝骨架简练、起飞性能好的特点,在画技上更有马氏画工细腻、着色瑰丽的特点,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提到师傅关宝翔,吕铁智的言语间不乏崇敬而激动:关家在南锣鼓巷很有名,关先生的爷爷是清朝“京城四大财主”之一的奎俊,即清朝内务府大臣荣禄的叔叔,关先生的父亲是名震一时的京城京剧名票关醉蝉。北京有三处奎俊府,分别在雨儿胡同、黑芝麻胡同和沙井胡同,“我师傅就是在沙井胡同出生的。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首部中外合拍的电影《风筝》中,孙悟空的风筝就是金老和关先生共同制作的”。
1984年,摄影发烧友吕铁智在一次展览上看见关宝翔的风筝,十分震惊,惊叹还有这么漂亮的风筝!“侍女、和合二仙……各式各样的我都没见过,我就想这应当让外国人看看呀!”没想到他好不容易找到关先生拜师,却被婉拒了。吕铁智没有灰心,得知关先生爱吃肘子,就每星期天带个肘子,骑车去关先生家,听老人家聊风筝界的趣闻,聊老北京的习俗,一坐就是一下午。吕阳还记得,小时候到了腊八这天,“我爸总会带上饽饽盒子,还有我妈做的红烧肘子,带我一起去关爷爷家。一进门,关爷爷会招呼‘小子来了’,给我爸指个座位,让他坐下。他半坐在椅子上,弯下腰,冲着我边笑边说‘小爷们儿也来啦’。然后就招呼人从厨房端出热腾腾的腊八粥,上面用青红丝、果脯和果仁铺成像花一样的图案。”
磨了一年,看他是真喜欢,关先生吐口收吕铁智为徒。至今吕铁智还记得师傅的第一次训话:“小子,你真想学这个,那可得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啊。这东西大富大贵很难,养家糊口没问题。你想清楚了吗?”在别人听来是劝退的话,吕铁智却如获至宝,得偿心愿拜入金马派门下。
金马派风筝对画面要求特别高,这一点吕铁智体会特别深,“马师爷是工笔画家,是把风筝提到艺术殿堂的第一人,要求这画必须得能登堂入室。过去每到春节,鼓楼大殿里都展览马先生的画,同时也展览他的风筝作品。”他听师傅说过,“金师爷做架子,马师爷画画片,北京一绝。比如原来的鸟类风筝只画背羽,都是一个颜色。马先生觉得不妥,将里面的绒羽加入到画面中,分成绒羽、芊羽、正羽三层来画,色彩丰富又真实。现在大家看到的鹰,全部都是这样画的了。”
也有让吕铁智惋惜的事,过去金先生家祖辈给皇上做风筝,做一个留一个样。当时北京几个行当里的高手都见过金先生的风筝图谱,“只有我师傅能随便翻看”。可惜的是,十年浩劫,风筝谱没能留下来。他指着一直珍藏的师爷画的风筝慨叹,“现在留下的这几个,是当时他在火神庙摆摊,供客人订货挑选的样子。师傅去世时,我在国外,他老人家跟师娘说,所有的图纸,必须得给铁智,别人谁都不行。”
从根上先学好了,不丢根就不怕变
吕阳是八五后,年轻利落,说话直来直去,三岁半时就被挑走练了十年体操,进过专业队,拿过全国冠军。有一年封闭训练过年不能回家,妈妈去福建看他,正好赶上看见一个孩子从杠上掉下来受伤,便连夜买了火车票带他走。教练追到火车站规劝,妈妈很坚决地说,这孩子以后不能干这个。回来之后,吕阳既不能算退役,也不能以特长生进学校。好在学校答应让他先试半学期,考试要能及格,就跟着上。他就从乘除法开始补,一天就睡三个小时。虽然挺累,但他还挺高兴,“没训练那么苦了”。
吕阳大学学的编程。吕铁智那时也支持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没逼着他非得回来学手艺。吕铁智自己干了四十多年,收了一个徒弟悉心教授,可惜徒弟刚能上手干活,便不幸生病去世。那次回家,吕阳触动很大,“我爸头发原来油亮油亮,可黑了,这一下头发白了好多,人也瘦了。我知道金马派没有六七年连门儿都入不了,先不说理念,光练画就需要时间。他干了四十多年才收的徒弟,我觉得老爷子都有点没心气了,挺心疼他的”。可是吕阳内心很挣扎,因为工作正赶上事业上升期,犹豫不定间,发小的一句话让吕阳下了决心,“他说你要是坚持干编程,最多你自己得意十年,要是不回来学这个,传承了一百多年的东西到你这就断了”。2014年,吕阳辞职回家学习技艺,年近六十的吕铁智高兴又意外,“没想到他直接就辞了职,然后我就想再归置出来一个人,金马派风筝到我这也不会断了,他也能传承下去”。
刚回来的头三年,吕阳一度觉得备受打击,“自己说什么都不对,很迷茫”。有一段时间父子俩经常闹矛盾,“我妈就说,你俩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有一次他看到很多年轻人喜欢剪纸,觉得剪纸的单色很有视觉冲击力,就想把剪纸放在风筝上面。“我爸就说你这不是玩意儿,我俩吵得挺厉害,最后他摔门走了,后来我俩几天不说话。我画了几个门神之后,确实觉得视觉上也单调。我爸拿了几个素风筝,黑锅底、蓝锅底那种单色调的风筝给我,也不说什么。我后来想通了,老先生们用的就是这种单色版画的艺术理念,只是表达方式不同。我想尝试的,实际上老先生们都已经实践过了。人家的东西最后为什么能留下来?是因为整个是对的,市场也接受了。”
再后来,遇到想不通的地方吕阳就愣想、愣试,“比如我爸说这块不对,那我就试试他那种为什么对,我这种为什么不对。试出来的,摆在眼前了,就知道哪儿不对了”。吕铁智坦言,“我就是这么学过来的,师傅说什么就是什么,得自己悟。我也遇见过,自个儿觉得画得很好,兴致勃勃给师傅拿过去。关先生就一句话,‘你这不是东西,跟我这风筝没关系’。那就是否定了,我就得琢磨它怎么就不是东西?吕阳刚回来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想给搁进去。其实几十年的学习和训练,很多东西都在心里搁着,一看就知道出圈了,丢根了。”吕阳也体会到,“所谓师徒传承,有时候看起来是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告诉你这条路是错的,其实是让你从根上先学好了,你再变的时候就有一条边界线支撑着你,你就不会走太远,你做出来的东西才不丢根。”
吕阳领会到传统艺术的高妙,其实就是不丢根就不怕变,“金先生、马先生、关先生都说过,只有不断变化它才能活着。重要的在于怎么才能不丢根地变,有老味有时代性,才是把根留下来了。像我父亲画那种工笔的东西,老人一看,这是老活,年轻人一看,又符合他们的审美,这就是他的风格。像我做永定门、正阳门、钟鼓楼,题材没人碰过,但别人一看,它的老味还有,这是不丢根,这是创新。”如今吕阳高兴的是,自己在变,父亲也在变。他设计正阳门风筝的时候,前两版都是按照传统方式设计的,最后出来两版立体形制,全都拿给父亲看时,“他反倒更支持我做立体的。其实他的思想也在更新,他觉得你这东西没出圈,他一直在把控着这个根。”
老北京喝完腊八粥开始放风筝,到清明就收了
吕阳特别服气的,是父亲的坚持。他还有印象,80年代末改革开放时,父亲一度很难维持生计,但一直坚持到90年代迎来对外交流。那时,吕铁智以风筝助力中外文化交流,走访了二十多个国家,出国五十多次。同样因为坚持,国家还没提出“非遗”理念的时候,“父亲他们就已经先摸索出在学校做传统风筝技艺的教育之路”。
在吕铁智看来,中国风筝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而且风筝是中国原生的艺术,承载的意义很丰富。北京是古都,是文人聚集地,北京风筝也形成了文人雅致的风格。一直以来,吕阳教课的最大感受是普及知识的迫在眉睫,“先不说风筝背后的文化传承,单讲理论知识,就能给学生讲六个学期不带重样的,而且还都讲不完”。
吕铁智坦言,过去北京放风筝是一乐,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贵贱高低,唱戏的老板们爱玩风筝,拉车的板爷也爱玩风筝,只不过玩的风筝不一样。特别是一开春,大人都哄着孩子去放风筝,为什么?“中医讲,仰头看风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张着嘴,吐故纳新,能去内热,春天容易上火、嗓子疼、长口疮,放放风筝就没事了。看着蓝天白云,心情好,像肩周炎、五十肩什么的不知不觉也就好了。”
老北京人有个风俗习惯,到春节长辈一定要送给晚辈一只风筝,祝他春风得意,平步青云。“过去一喝完腊八粥,我师爷在地安门火神庙的摊儿就支起来了,人们随时来买风筝。北京人放风筝是有时有晌的,喝完腊八粥放风筝,到了清明风筝就收了,不放了。清明时候,讲究带着风筝去扫墓。香烛、贡品摆起来之后,放起风筝,等香烛快烧完了,拿香头把风筝线烧断,把风筝放飞。一年的灾呀病呀,随着风筝飞走了,叫放晦气。”
吕阳越来越觉得,他现在做这事比原来更有意义,“我是北京生北京长,经常接触一些外国人,老问一些北京文化的事,比如说起一个门墩,我爸就告诉他你听来的不对,会给他讲是什么样的。有一些我都没听说过,而且觉得自己不知道也很尴尬。后来一想,这就叫文化烙印吧。为什么老说北京城的北京味越来越少了,是不是这个烙印越来越少了?”吕阳觉得,“这些东西要是再没人说,没人学,没人干,那以后就更没人知道了。”
最近几年,吕阳更理解父亲了,也觉得父子俩在感情上更近了。“我们这一代的困惑,是如何让人们发自内心的愿意把它传下去。我觉得是时候该我发力了。”站在屋顶,望着古稀老槐映衬下的鼓楼,吕阳憧憬地说。
文/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吕阳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