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潮的代表作(书信中的张潮)

清王云《西园雅集图》,绢本设色,181×52厘米,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尺牍即书信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中,但当时文人将其归属于应用公文类,认为不能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因而一直到唐代都不屑于收入自己的文集中。至晚明时期,由于进步思潮的影响,一种形式自由、抒写性灵的小品文风靡天下,而尺牍被视为小品的一种,于是掀起了尺牍选本的印刷热潮,据学者统计,当时有尺牍选本二十余种。清初尺牍继续火热,士人非常重视尺牍的保存与传播,书商则在其中发现了商机,李渔的《尺牍初征》、周亮工的《尺牍新钞》等尺牍选本相继问世,在书籍市场畅销不衰。
清初的尺牍选本中,由张潮编辑出版的《尺牍友声》《尺牍偶存》,收录亲友寄复和他赠答的尺牍,存留了当时文人交游、创作、出版等活动的吉光片羽,因而弥足珍贵。扬州大学文学院王定勇教授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刊本为底本,参以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所藏版本进行点校,2019年由黄山书社出版,书名《尺牍友声集》,由前言、《尺牍友声》、《尺牍偶存》、附录四部分构成,收录尺牍1466通,是目前最为完备的版本。透过这些流露“心声”、“心画”的尺牍,我们可以一窥张潮的精神世界。
一个庞大的交游网络
张潮顺治七年(1650)生于徽州歙县一个官宦之家,字山来,号心斋,十岁时随父迁居扬州。父亲张习孔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但张潮却屡试不第,在“壮志雄心,消磨殆尽”后,转而经营盐业治生,以读书、著述、刻书为乐。张潮著述甚富,有《幽梦影》等书二十余种,又经营家刻诒清堂,出版《虞初新志》《檀几丛书》《昭代丛书》等丛书。康熙三十八年(1699),张潮遭人诬陷下狱,家产几毁,自此“生计萧然,日就疲惫”。
张潮在清初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梁嘉稷信中称:“天下读其书者,如见其人。即未读其书者,亦莫不想望风采,购求其书,而愿纳交于其人也。”清初扬州是风月繁华之地,盐商麋集,士人多如过江之鲫,张潮通过尺牍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交游网络,《尺牍友声集》涉及文人三百多人,其中既有文人高官、皇亲国戚,也有闺秀女尼,还有西方传教士,可见他交际之广。康熙二十五年(1686),孔尚任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治理淮河,他来到扬州不久,就组织了第一次文人聚会,张潮预会,翌日孔尚任致函张潮曰:“听雨之会,得足下为领袖,遂觉觥筹生色,吟啸可传,是日发辞吐论,惟足下为雄。”康熙三十二年(1693)夏,张潮主持红桥宴集赏荷。康熙三十三年(1694)闰五月端午,张潮主持蜀冈雅集。同年,张潮又主持西园送秋大会,据宗元鼎信中称:“翰苑名流,年翁为骚坛宗匠,弟不独重先生文章诗赋推为第一,而更重先生笃爱故交寒士,深为拜服。”次年春天,张潮又一次发起红桥雅集。由此可见张潮在扬州文坛的领袖地位。
张潮在信中坦言自己平生无所嗜好,唯好读新人耳目之书,《尺牍偶存》中有很多他向文友索要各类奇书的信札。他在《复钱十青》中谈及《虞初新志》的选稿标准道:“唯实事之奇者,方为载入。”钱十青的《金衣公子传》虽然笔致幽隽,但遗憾的是不符合“奇”的标准,所以不能入选。在给吴素公的信中,张潮又指出他的《义犬》“文虽甚佳,然义犬事颇多,载之不胜其载”,因而只能割爱。可见张潮选文态度之严,他编刻的书就给朋友们留下了“奇”的深刻印象,孔尚任来信中称:“捧读新刻,愈出愈奇,盖天地原有未发之秘,借年翁手眼,次第吐露。”黄泰来信中称:“新刻愈出愈奇,先生真一代之才,妙腕灵心,俱聚于此。”这种对“奇”的审美偏好,是从晚明凌濛初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
慷慨赞助社会公益事业
张潮家境富裕,他轻财好客,扶危济贫,是贫士的“及时雨”。陈鼎在《心斋居士传》中就有说:
淮南富商大贾惟尚豪华,骄纵自处,贤士大夫至,皆傲然拒不见。惟居士开门延客,四方士至者,必留饮酒赋诗,经年累月,无倦色;贫乏者,多资之,以往或嚢,则宛转以济,盖居士未尝富有也。以好客故,竭蹶为之耳。
吴应麟信中也说张潮:“近而井里,远而关山,凡有告者,靡不周急之,且拳拳无倦意。”他慷慨赞助社会公益事业,从信中可知,他曾捐资修建沭阳文庙、梁溪宝安寺大殿、黄山脚下慈光寺;赞助修复虎丘真娘墓、短簿祠等。许多困厄泥途的下层文人纷纷给他写信求助,张潮皆来者不拒,慷慨解囊。孔尚任居留扬州三年,因张潮资助而“出有车而食有鱼”;张鸣珂欲游历燕都,张潮赠送盘缠;顾彩冬天有南谯之行,向他索要裘皮大衣;张韵腰痛加剧,张口向张潮要白银数两购买鹿茸;吴应麟家门寒寡,沉疴缠身,为避免暴尸荒野,向张潮求告。冒丹书信中称赞张潮经纪其贫友之丧,“诚所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也。”朱慎客死扬州,张潮不但襄助厚葬,而且“始终照拂”朱慎家人。殷曙打算将祖先木茔移葬高岗,也向张潮求助。张潮的高情厚谊,令大家感动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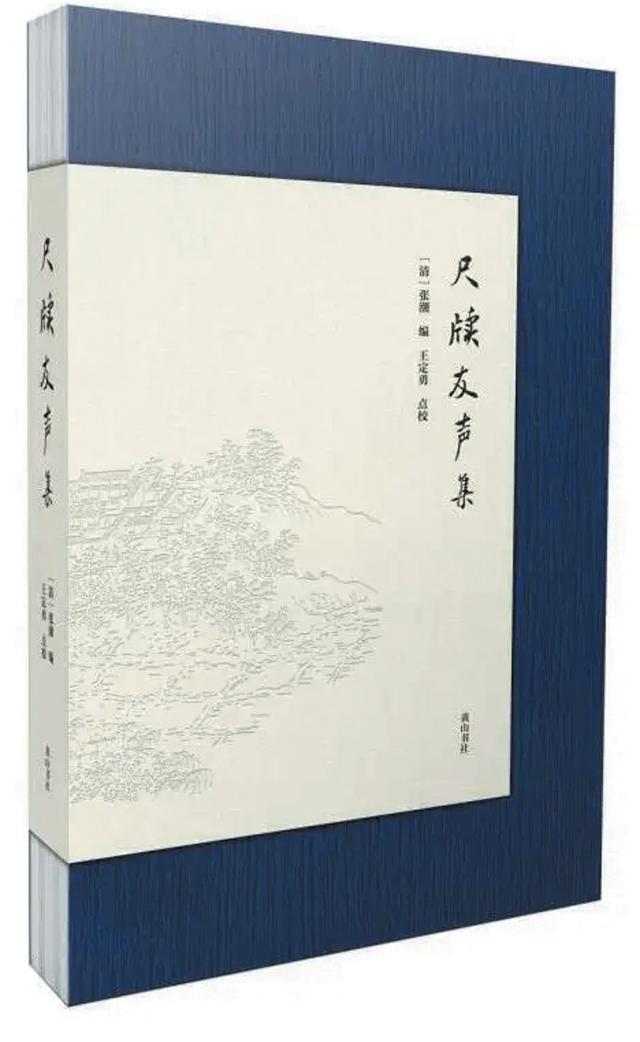
《尺牍友声集》,张潮编,王定勇点校,黄山书社,2020。
通过编书、刻书徼名
读书人最看重的是“立言”以不朽,希望生前能看到自己的著作梓行,一些贫士纷纷写信向张潮募捐,帮助刊印文集,张潮几乎是有求必应。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他出资刻印了吴绮的《天都振雅》、黄泰来的《清诗片玉集》、陈鼎的《留溪外传》、毛际可的《春秋五传考异》、张炳睿的《手让文》、余怀的《冷云集》等等书籍。吴肃公看到自己散发油香的《读书论世》,感激不已,“不朽之业实心斋先生造之矣。”张潮还乐于将书“广赠同人,嘉与后学”,不少人向他写信索书,张潮都一一满足。
《尺牍友声集》中还有不少借书论学的书札,如黄周星向张潮借阅当时流行作家李渔的《笠翁传奇十本》《闲情偶寄》,郑旭旦寄阅《汉宫秋》《金焦记》,并有数封信讨论制曲问题。张潮对算数、天文、地理以及从西方传来的各种科技知识抱有浓厚兴趣,意大利人毕嘉生命中的最后三年是在扬州度过的,张潮曾在信中向他询问有关西方的地圆说,张潮又与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孙兰去信,讨论西方测量方法。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科学对话的珍贵记录。
张潮一再表示“种种拙选只为扬芳,匪图射利”,即通过编书、刻书为众多识与不识的作者“扬芳”,其实也是为自己徼名。在科场上败北的张潮,希望通过写作、出版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资助文人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从信中看来,他的确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如沈琰信中恭维道:“先生当代文宗,风骚之主,真海内大手笔。”尧南札中称“先生道德文章足为当今领袖”。张竹坡札赞美他乃“昭代之伟人,儒林之柱石”。这些朋友还在信中吹捧张潮的文学作品和书艺,如汪楫谓“读心斋《下酒物》,真有一斗不足多之叹。《美人八咏》尽态极妍,虽韩偓、徐陵复生,罔以逾矣”。王永清说“今吾兄独宗李、杜五言,而意象无不毕肖,真是天衣无缝矣”。江之兰赞“尊作出,前无古人”。另一封信中又说张潮的“八分既妙,而飞白更具精品,不意吾兄两腕中有如许神通”。冒丹书称张潮的词《沁园春》当与李白《忆秦娥》、柳永“晓风残月”“并传”。另一封信称“承赐大诗,直与《三百篇》并传不朽”。这类奉承之词在《尺牍友声集》中比比皆是,所以周亮工在《尺牍新钞序》中批评道:作为交游应酬的尺牍,很容易“綷取从谀”,就是说谄媚的话。
《尺牍友声集》为张潮储备了丰沛的人脉资源,不但可以通过受助者的感恩传布自己的美誉,而且还请他们为自己的文集写评语。张潮频繁寄书京城文友代索评语,声称“其辞不须过誉,即与鄙意相反,或嬉笑怒骂皆无不可也”。张潮的《心斋聊复集》收文50篇,附有评语130余则。《心斋诗集》的三篇序文之后附有“总评”,每首诗后又都附有评语。《幽梦影》征集到评语699则。这些评语都对张潮的文章和才华赞美有加。
涉嫌攘夺著作权
与封建社会大部分读书人一样,张潮有强烈的功名富贵思想,但科场粉碎了他的梦想。康熙三十二年(1693),朝廷为征讨厄鲁特部噶尔丹向社会捐官筹资,张潮以银千两买了个不入流的“翰林院孔目”,而且是“挂名虚职”。许多亲友纷纷来信表示不解,张潮在回复江之兰的信中坦诚道:“弟自束发受书,其志亦颇不小,不谓初而偃蹇,继复因循。望翰苑中人,未免有仙凡之感,近以新例聊复效颦。虽不能身证仙班,亦可比于扫花弟子,正所谓不得已而思其次也。”由此可见,科场失败给张潮留下了多么痛苦的回忆,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安慰惆怅的心灵。另外,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交结权贵,张潮结识努尔哈赤孙、饶余郡王阿巴泰第四子岳乐、辅国公博尔都,都是通过书信朋友从中牵线的。他将父亲和自己的著作12种寄给岳乐,信中称“俾草野俚鄙之词,得接于屏藩之几席,其为荣幸,永世难忘”。企望自己的才华得到他的赏识,以此进入上层社会。李上德来信报知:“随呈主人大司徒马公,并旧主人显府殿下又三阿哥殿下。读大稿者,无不称快。”在众人的游说下,岳乐第三子岳端终于答应收张潮为弟子。
当然,书信不仅仅都是展现张潮华丽的面孔,有时也会露出一些斑点。如诗人孙默(字无言)汇辑的清初词集《十六家词》刻印于康熙十六年(1677),他去世后书版归张潮所有。余怀曾致信张潮询问情况,张潮回复敷衍搪塞,其实他已改名《国朝名家诗余》重刻,并且词集卷首署“张潮山来校”。著名诗人卓尔堪编成的《遗民诗》出版,张潮赞助了部分费用,该书扉页署“卓子任、张山来、印宣仝阅”,每卷题署甚至把张潮排在最前,而张潮并未参与编选工作。张潮在给友人张渭滨的信中道:卓氏所点定《遗民诗》因无力付梓,嘱托我与其他人代为雕板,所以没有列出“谁氏之笔”。这解释有些强词夺理了。张庸德的《四书会意解》,张潮出资七百余两白银,耗时三年告成,以诒清堂堂号刊行,扉页上印“江都张紫裳、新安张山来两先生合订”,每卷署“广陵张庸德紫裳补校、新安张潮山来参阅”。七年之后,两人因版权之争交恶。面对张庸德的诘难,张潮的回信道:“潮止列名参阅,岂捐梓者不可参阅耶?”作为书商与出资人,张潮认为在他人著作上署名“参阅”是理所当然之事。这未免有狡辩之嫌。这些事例都表明张潮涉嫌攘夺别人著作权。
正如朋友信中所赞,张潮“以斯文为己任,以朋友为性命者”,白璧微瑕,张潮为中国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万晴川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