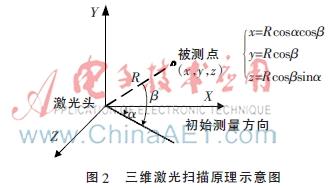让海王上岸的只有他自己(一分钟能辨别海王德我)
别人嘴里的海王似乎对我是认真的,可我今年二十四了,只需打量一分钟,就知道,此人绝不是我的菜,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让海王上岸的只有他自己?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让海王上岸的只有他自己
别人嘴里的海王似乎对我是认真的,可我今年二十四了,只需打量一分钟,就知道,此人绝不是我的菜。
我不喜欢不在自己掌控范围内的男人。
不过帅哥嘛,多看几次还是养眼的……
1
市中心的周六晚上依旧塞车,等待红绿灯的间隙,钟行将衬衫纽扣松了松,车子拐过街口,目光所见之处,酒吧门口已经没有多余的停车位,钟行没有多加思索,径直将路虎停在了路边。
Livehouse光线不佳,台上驻场乐队卖力演出,钟行跟着侍应生在场内绕了绕,终于找到沈向南所在的卡座。
落座时第一眼就瞧见了坐在沈向南隔壁的女生。
女孩子低着头,认真分割桌上的披萨,将将及肩的头发细碎地铺在脸上,她将一块披萨饼塞进嘴里,面上鼓鼓的,抬起头,忽而就瞧见了刚坐下来的钟行,有些蒙圈,那双眼睛纯得能透出水来,嘴巴一鼓一鼓地嚼着吃食,头圆脑圆眼睛,看上去和夜场格格不入。
钟行一把拉过沈向南,“好家伙,知道你喜欢妹妹款的,也不至于诱拐未成年少女了?”
沈向南正忙着和人摇骰子拼酒,被他陡然一拉,“哟,钟少,啥时候到的?”
而后沈向南按着女孩的脸,两人凑在一起,道,“睁大你眼睛看看,那是我堂妹,二十四岁了,没见我们俩长得格外像吗?”
钟行“啧”了一声,“不要脸。”却又多看了一眼沈知欢,道,“这看上去也太像高中生了吧,进来没被查身份证?”
沈向南懒得回答他的问题,径直要往他手里塞酒,“问题那么多,赶紧喝。”
钟行往卡座沙发一靠,挥了挥手,不去接杯子,“一来就让我喝,不行啊,我是空腹来的,待会没两杯就吐了。”
某位好友被他们聊天引来,疑惑问道,“你晚上不是带着新交的女朋友去吃饭了吗?”
“吃是吃了,还专门选了个看上去很高档的法式餐厅,地方挺漂亮,菜也挺漂亮,就是吃了俩小时不知道自己吃了些啥。”
钟行给自己倒了杯清水,喝了一口,“说实话,要不是你把我叫过来,吃完那份只有一叉子的冷盘意面后,我是真打算把人送回家后去吃份加大版兰州拉面的。”
说话间他伸手将自己的头发随意往上撩了去,发型有些乱,打破了刚来时那种处处完美,把平日里装出来的斯文绅士全丢一边去,露出随意的本质来。
钟行这话说得格外接地气,反倒和他方才进来时那种引人侧目的气质格格不入,招人的桃花眼此时卸去了面对狩猎对象的进攻性,几句话说得直白,周遭包括沈知欢在内的几个好友都笑了出声。
而后同沈向南换了个位置,坐在沈知欢隔壁,同她分享起那盘披萨来。
他是真饿了,披萨饼有些凉,芝士些许变硬,他却连着吃了两块,然后和沈知欢说,“初次见面,我是钟行。”
沈知欢给他递了盘炸虾卷,“总听我哥提起钟少,所言不虚。”
钟行吃东西时没故作斯文,大快朵颐,“他能说我好话?”
损友沈向南喝到一半,忽而想起一件趣事来,兴致勃勃地同大家伙分享。
他拍了拍钟行的肩,“我们大学隔壁班有个同学,加过你微信,不过你应该没什么印象。”
钟行挑了挑眉,“哪位?”
沈向南说,“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天他和我聊天,突然问到你,他问我,钟行什么时候准备和女朋友结婚。”
坐在沈知欢旁边的一个女生迷茫三连问,“钟少要结婚?啥时候结婚?跟哪个女朋友结婚?”
沈向南自己还没讲完,早就开始笑得喘不来气,“我也一样迷惑,于是我问他,你怎么觉得钟少要结婚了?你们猜他怎么说。”
沈向南卖了个关子,却不往下说,周围人想了一阵,通通没猜对原因,一致转头看钟行。
当事人举着威士忌杯耸了耸肩,试图表现得很无辜。
沈向南慢吞吞道,“他说,从大学到现在常常看钟行朋友圈常常秀恩爱,恋情很稳定,觉得离结婚就不远了。”
这位把聊天记录都讲得十分传神的沈先生幽幽地补上了最后一句,“于是我问他,‘你没发现他每次秀恩爱的对象,都不是同一个吗?’”
这个结尾不负众望把故事推到高潮,大家哄然大笑,话题中心钟少慵懒地靠在椅背上,举了举手,摆了一个请便的姿势,任由大家开玩笑。
馆内灯光晦暗不明,一闪而过的灯束将钟行眼底的浅笑印得清晰,沈知欢抬头瞬间正好对上他的抬眸的眼神,然后她听他笑骂沈向南道,“别说的我跟个渣男一样,各求所需而已。”
沈知欢顺口揶揄了一句,“养鱼就养鱼嘛,这么还要说成语。”
钟行笑道,“被你看穿了。”
他如此坦荡,反倒让人说不出一句不好来。
酒过三巡,夜场已过半,就连台上的rap都变成了民谣,桌上空掉的酒瓶越来越多,厚重的玻璃折射星星点点的桌面小灯,钟行和沈向南喝得有些多,勾肩搭背倚在沙发上,衬衫都有些皱了,醉意朦胧地靠在一起,怎么看都像俩败类。
一旁的沈知欢十分认真地跟其他人学习摇骰子猜大小,又一轮被他人赢了,很怀疑人生地思考为什么自己又被人骗了。
钟行侧首看了她一眼,低声道了句,“笨蛋。”
赌博弱鸡沈知欢转头,狐疑地问了句,“你在跟我说话么?我没听清。”
钟行道,“说你不能轻信他们说的话,人家说自己有什么点数,你不能真信。”
她眉头紧紧蹙一起,钟行轻叹一口气,接过她的骰子加入战局,没几轮就让对手们通通喝了一杯。
沈知欢给他鼓掌,钟行问道,“学会了么?”
她很诚恳地摇头,“果然帅哥都会骗人。”
钟行气笑了,“我帮你赢了几盘,你得了便宜还要说我两句?”
她接话很顺口,“我错了。”
侧首便对上钟行眼睛。
沈知欢眼睛圆,就连眼角都是钝钝的,格外没有攻击性,就是连钟行这种擅长于让女孩子面红心跳的选手都不得不败下阵来,自行惭愧于自己像只开屏的花孔雀,比起这种眼底都纯得像是能透出水的小动物,实在是过于肤浅。
一时之间他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只说了句,“原谅你了,下不为例。”
隔着这么近的距离,如此对视情景之下,沈知欢此时才细细打量起钟行来,即便钟行此时已卸掉白日里那些伪装,可偶尔一个眼神,桃花眼里透着的笑意下藏了两分掠夺性,棱角分明的脸和高挺的鼻梁把人衬得很是好看,让路过卡座的女生会投来一个目光,他看着人时习惯带笑,一副洒脱不羁的模样,可他一旦不笑时,总多了些生人勿近的意味。
若她沈知欢还是看青春疼痛文学的不谙世事的少女,大抵会被这种男人迷得七荤八素。
可惜她今年二十四岁,只需打量一分钟,她就知道,钟行此人绝不是她的菜。
她不喜欢不在自己掌控范围内的男人。
不过帅哥嘛,多看几次还是养眼的。
2
从第一次见到沈知欢后,钟行早就预想到未来的日子会常常见到她,毕竟他同沈向南简直是穿一条裤子的狐朋狗友,沈向南的狗窝等同于他钟行另一个家,如今沈知欢暂住在沈向南家,难免会碰上。
然而钟行没想到再次见到沈知欢时,会是在这样的场面。
那日恰逢是个饭局,推杯换盏间桌上的红酒空罐一瓶接一瓶地排列增加,整整齐齐地放在饭桌一角,有条不紊地将明黄吊灯的颜色折射成好多道平行的光线。
钟行酒量好,可偏偏不爱喝红酒,觥筹交错间胃里像是涌了许多暗红色的颜料油漆,酸涩的干红仿佛像是浓稠的血浆,让人一股一股地犯恶心。
合作伙伴笑容可掬地为他添酒,道,“钟少海量。”
他抬头看对方同样年轻的脸,十分给面子地一饮而尽,也不顾红酒需要细细品尝,带了“雅致”性质的红酒到了饭桌上与其他酒水无异,反正都成了酒桌文化的工具。
合作伙伴不经意间蹙了蹙眉,大抵是这种狂饮法着实伤胃,钟行心想,大概你我都不爱这样应酬,却非要应酬对方,最后两败俱伤。
可他又不能戳破这个尴尬的事实,只得在放倒别人同被放倒之间二选一。
空瓶变多,这场令人难受的饭局终于落了尾声,钟行脆弱不堪的胃难受的很,合作伙伴强撑镇定地问他要不要进行下半场,他摆了摆手,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算了,待会还有约。”
转而便给沈向南发了消息,让他赶紧来饭店捞自己,毕竟此时的钟少感觉吊灯都是摇晃的,想吐又吐不出来,想醉又不敢醉,非要客气告别合作方才敢瘫下。
沈向南这一日还算靠谱,来得很快,将他架上了车时钟行已经有些晕眩,待到车子行驶了十几分钟,他才发现前边的副驾驶还坐了个沈知欢。
原本他是没发现的,只是迷迷糊糊间听见有人在说话。
沈知欢很会戳人痛处,“钟少不会吐吧?”
此时钟行只是犯恶心,离吐还有一大截,就听沈向南说,“你别咒我,我昨天刚洗车。”
沈知欢好似探头看了看钟行,很犹豫,“我觉得他不太行的样子……”
任哪个男人被说不太行都想暴走,可惜钟少在暴走前直接丝血掉线,虽然脑子有反驳的冲动,但醉酒的身体压根不允许。
然后沈向南猛踩油门,将车开得飞快,沈向南说,“你别说这种晦气的话,他要是吐了你负责把他丢下车,我负责弃车逃亡。”
听这话,钟行十分想一鼓作气吐沈向南一车,然后他听沈知欢说,“再帅的男人,醉酒后吐一车都不帅了。”
她苦口婆心教育沈向南,“你可别给我丢这个脸。”
一时间钟行又默默收回了吐沈向南一车的冲动。
好不容易抵达钟行住的公寓,他被沈向南扛着扔到床上,沈向南在此时还算靠谱,嘀嘀嘀为他开了空调,凉风一阵吹在卧室,让初夏的闷热少了几分。
他迷迷糊糊睁眼,想礼貌性说句谢,就看到沈知欢放大的脸。
她蹲在床边,凑近了盯他,然后伸出手摇了摇他的脸,“钟少,起来喝点热水。”
钟行想开口拒绝,她却指使着沈向南把他扶了起来。
她手中拿了个类似威士忌杯的玻璃杯子,伸手一触是温热的,钟行想接过,可沈知欢却没松手,担心醉鬼下一秒将水撒了一被子,只是将杯子递到他唇边,让他小口小口地喝了一些。
温热清透的液体缓缓从舌根淌到胃里,将口中酒精涩味稍稍冲淡,又将充斥着冷酒冷盘菜的腹腔煨暖。
沈知欢问她哥,“你确定不给他把鞋拖了吗?”
沈向南后知后觉“哦”一声,看了看钟行已经将被子蹭脏的皮鞋,十分不厚道的拍了几张图发到好友群里,才去替他将鞋脱了去。
她这样凑近了看钟行,放大版的脸朦胧中看上去很像刚出生看什么都新鲜的幼猫,转而和沈向南说,“看来钟少也不是千杯不醉啊。”
不知为何,听了这话钟行格外想笑,想说是个人都不可能千杯不醉,可惜头疼的厉害,一下也笑不出来,也说不出话,然后他模糊间见沈知欢站起身,寻了空调遥控器。
女生有时总是比男人细腻些,她说,“哥,你这风也开得太大了,直吹别把人冻死了。”
沈向南很没良心,“肯定不会冻死,顶多几天上不了漂亮小姐姐的床而已。”
钟行:“……”
沈知欢:“……”
3
醒来时是个阴天,低头从落地窗看下去,风吹起地上的沙砾,连草地都是灰暗的一片,钟行胃里很空,喝了杯水后依然胃里很难受,酒在肠子里消化不良,口腔中还有残存的酸涩红酒味道,却怎么样也吐不掉,让人一阵阵恶心。
冰箱里空空荡荡,只有几瓶饮料和矿泉水,他找出将近没电的手机,点了个外卖。
放眼整个屋子,各色家具齐全,厨房的刀具都是全套的专业配置,可惜连外头的塑封包装都没拆开,住了两三年的屋子冷冷清清,像售楼处摆设的样板房。
有好友曾建议他找个居家阿姨,收拾屋子的同时也能替他准备早晚餐,可钟行不爱有人同他长居,宁愿选择点外卖这种不那么健康的行为,也不愿接受建议。
沈向南曾经吐槽过他的样板房,“你这屋子简直像专门用来带女孩子回来一样,要不是跟你这么熟,我简直要怀疑这房子是租的。”
他那时毫不留情地回击,“你以为谁的屋子都跟你一样乱得跟狗窝一样么?”
不过他那时深感沈向南地评价有些道理,为了显得屋子有些人气,他默默给冰箱添置了许多饮料,不过感觉效用甚浅。
手机短信显示有台风要抵达,呼啸的台风季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公司项目因此被迫延期,钟行在焦头烂额中度过了小半个夏天,直到再次能喘口气和沈向南相约时,已然是初秋时分。
秋日总是会给人些萧瑟之意,在沈向南的提议下,钟行在家中组了个火锅局,满足了狐朋狗友们总想要糟蹋他样板房的愿望。
和友人喝酒与应酬总归不一样,麻辣火锅把这间清冷的屋子熏得有些烟火味,碰杯中各自微醺红了脸,饭后残局便丢在餐厅,等待次日请位清洁阿姨帮忙收拾。
三俩好友各自在房间和客厅寻了葛优瘫的位置,试图今夜激情游戏电影到天亮。
大抵将近凌晨时分时,钟行反倒精神起来,忽而想起冰在冰箱已久的清酒,试图再和朋友进行第二轮微醺,走入厨房中却看见了沈知欢。
她倚在柜边,低头垂眸专注地看手机,另一只手中拿了个装了牛奶的玻璃杯,小口小口地呡。
听闻脚步声她抬头,钟行道,“怎么躲在这?”
沈知欢举了举杯,“晚上吃得有点辣,有些烧胃,喝点奶中和中和。”
却又戏谑,“你这冰箱里竟还有没过期的牛奶。”
钟行摊了摊手,“可能是阿姨帮忙买食材时候买的。”
他忽而觉得这种场面很神奇,毕竟从前这间屋子也有很多人来过,有时他醒来,能看到带了残妆的女人在冰箱翻找矿泉水,那些女人有些眼线花了,有些带了宿醉的低迷,有时假睫毛掉了一边,她们穿着宿醉后的衣服或是精心选取的吊带裙,大家心怀鬼胎共处一室。
偶有装作贤妻良母一派的,秉持抓住男人的胃就抓住男人的钱包的想法在厨房出现,一道道菜色背后却盖不住欲望。
很少有人坦坦荡荡站在这里,因为吃得太辣了慢吞吞喝杯热牛奶。
想到这里钟行都觉得自己是个人渣,一边勾搭那些本就如此的小网红,却又一边觉得不够诚恳。
他鬼使神差地发问,“你会做饭吗?”
闻言沈知欢一怔,放下手机道,“不太会,煮泡面还行。”
说着把自己逗笑,反问道,“你呢,当过留学生的一般都会做饭吧。”
“以前还会煮,后来做得少,估计已经不如读书时代了。”钟行道。
沈知欢对自己差劲的厨艺毫无遮掩,“以前有时特别想吃中国菜,可是自己煮的东西实在太难吃了,于是总是去其他同学家里蹭饭,日常吃百家饭。”
4
大抵聊了些国外菜色的奇葩之处,沈知欢手机忽而响了,她说了声抱歉,接起电话,和电话那头报备起自己今日的行程。
出于礼貌不偷听他人聊天,钟行侧身走入挨着厨房的阳台,隔着玻璃门,看着沈知欢放在厨房台面的牛奶逐渐变冷,没了白雾,他抽了根烟后,她还没有讲完电话。
约莫又过了一阵,她才将手机从耳边放下,隔着玻璃门钟行和她望出来的眼神对上,钟行第二根烟还没抽完,他却将烟掐灭,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回客厅去加入沈向南的狂欢,在这里等沈知欢结束电话,可他心里想这么做,他也就这么做了。
他拉开阳台门,问道,“这么晚聊得这么久,有什么紧急的事么?”
沈知欢摆了摆手道,“哪有什么事,是我妈给我打电话。”
她拿起手边已经凉了的牛奶,喝了一口后觉得不够烫,却又懒得再去加热,咕咚咕咚喝下去,“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听我妈抱怨我爸明明说好晚上和她去逛超市,结果又被朋友叫去饭局了。”
钟行有些差异,“所以就说了这么久?”
她却觉得十分正常,“对呀。”
钟行道,“看来你爸妈感情很好。”
沈知欢点点头,“天天斗嘴吵架,然后来我这互相告状,不过好的时候确实挺好的,好的时候丢下我过二人世界。”
一时之间钟行不知该说什么,他很难想象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十年如一日的在一起,就如很难想象她究竟和母亲聊什么,竟能一件小事就聊那么久。
从他记事起,父母早已各忙各的事业,起先他们还会意见不合地争吵,后来变成了互不干涉的合作伙伴,只有在重要会客场合才会笑容可掬地挽手出席。
所以他从不相信爱,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家。
可他此时竟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好似有些明白。
钟行想起自己起初进厨房的意图来,他拉开冰箱,从下层找出那瓶冰酒来,沈知欢看着他的动作,忽然道,“好像我每次见你,都是喝酒的时候。”
钟行找了开瓶器,将螺丝缓慢旋入木塞中,“生活所需。”
他笑了笑,道,“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其实不爱喝酒。”
沈知欢放下手机,侧首看他,“工作所迫是一回事,但你平时不也喝很多酒吗?”
她顿了顿,“冰箱里冻了那么多瓶,是因为心里很空,所以要找东西来补一补吗?”
钟行旋开瓶器的手顿了下来,转头去看沈知欢,厨房暖黄灯光下,钟行第一次看清,沈知欢那双看似懵懂眼中的清明。
她眼神依旧清澈,这样亮的灯下,他才看清,原来她神色是这样温和而清明,从不是他从前匆匆一眼所以为的懵懂和单纯,她好似能看清他人内心所想,而眼底的干净源于她对世事的敏感和透彻。
钟行怔了怔,一时无言,只说了一句,“也还好。”
厨房又一次沉默下来,客厅沈向南已经开始斗地主,笑声透过餐厅传来,钟行虎口抵在酒瓶冰凉的瓶颈,然后他打破僵局,“上两回见你还觉得你是小朋友,没想到你过得比我还清醒。”
沈知欢做了个鬼脸,装了一副小朋友的声音,“哥哥,人家成年很久了。”
难得的钟行没似平日一样接梗,只是很轻的叹了一口气,却又笑了,说,“走吧,一起喝这瓶酒去。”
5
很长一段时间,钟行总会想起那一日沈知欢那句反问他“想找点东西补一补”的问句,发言人只是把这话轻飘飘如羽毛般说过去,却让夜里常常有些失眠的钟行翻来覆去地想。
有一日同沈向南聊天时,不知为何话题便转到沈知欢身上,他那时问道,“你妹有谈恋爱吗?”
沈向南道,“好像没有,她近来沉迷工作,无心恋爱。”
不知为何,钟行那时松了一口气,嘴上调侃道,“你没给她分享点恋爱经验?”
沈向南“切”了一声,“她比我清醒多了,不把时间浪费在无用功上,她要真想玩,估计比我强多了。”
深秋初冬时的一个周五晚,钟行同下属开会开了将近六个钟,走出公司大厦时拨通了沈向南的电话,问道,“在干嘛,出来喝一杯?”
却难得的被沈向南拒绝,“我刚要出门去机场接沈知欢,太晚了,打车不太放心。”
钟行安静了一秒,没有任何铺垫地突然问道,“你在哪?”
沈向南不带思考,“在家啊,准备下车库。”
分明钟行驻足在公司楼下,却难得的说了谎,“我刚好在城南这边,要不我直接去接她,你就不用出来了。”
虽说他这儿去机场比沈向南近一些,却也仍是要四五十分钟的车程。
正穿袜子的沈向南闻言立马停住动作,准备继续自己的躺尸大业,“行,那我等你俩一起吃宵夜。”
然后沈向南说,“她十一点多点下飞机,取完行李估计十二点出头吧”
手机抵在耳边,钟行抬手看了看腕上的表,如今已将近十一点半,这个点沈向南要真出门接沈知欢,估计得让沈知欢等上个一段时间,他心中暗骂沈向南不靠谱,匆匆挂了电话发动了车。
开往机场的快速道此时车并不多,橙黄的路灯一盏盏从身侧闪过,偶有枯黄的叶子在风中飘过,钟行车中没有播CD,也没有打开电台,静寂一片,只有油门的轰鸣声和窗外微弱的风声。
他将车开得很快,一路疾驰抵达机场,抵达时他看了看时间,是夜里十二点零三分。
他将车停在出口处,此时夜色已晚,没有保安会来驱逐逗留车辆,钟行拿出手机,犹豫了一霎,然后从通讯录找到了沈知欢的头像。
他们的聊天界面很干净,什么都没有,上一条记录还是“您已添加沈知欢为您的好友。”
他发了信息,“走二号门出来,车牌XZ012。”
手机没有回复,钟行此时才按下车内音响的开关,让这辆空荡的车不要那么寂静,此时他才腾出手来松开衬衫领口的扣子,手机屏幕亮了,沈知欢回了短短一个字,“好。”
还没待钟行想着她回复竟如此干净利落时,第二条消息进来,“刚取完行李,走出去要三分钟。”
三分钟不长不短,不足以让人完全放空脑袋休息,也不至于一闪而过。
夜里车道大多是揽客的出租车,钟行手搭在方向盘上,一时之间觉得自己有些好笑,记忆中上一次开这么快的车已是很多年前在加州的事情,彼时是青春放纵,如今竟也有当年那么点愣头青的错觉。
机场大道车辆寥寥,一束束车灯伴着机场冷光色的白炽灯显得更加静寂,钟行思绪晦暗不明,眼睛漫无目的地看着二号门偶尔踏出的身影,不久他便看到了沈知欢。
沈知欢拉了个小型的暗灰色出差行李箱,没套上厚外套,只是披了条微厚的披风,她驻在门口左顾右盼,却在钟行准备摇下车窗叫她时发现了钟行的车。
大抵是坐飞机的原因,她把自己穿得很是舒适,浑身上下都是松松垮垮近似居家服的衣物,她瞧见了钟行的车,便拉着行李快步走来,中途还伴了几步小跑。
可她那身衣服偏偏不适合跑动,于是乎她便一只手拉着行李箱,一只手抓住披风不让它滑落,看上去十分逗趣,连钟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此刻嘴角是带了笑意的。
6
沈知欢上了车,靠在椅背上,幽幽道,“沈向南做什么去了,竟然麻烦钟少你来接我。”
她说话不快,却故意带了那种哀怨的腔调,“不会是见色忘妹吧……”
钟行虽是主动请缨来的,此时却面不红心不跳地接道,“可能是的。”
他启动了车子,此时车厢中恰好跳转新的歌曲,沈知欢伸手去触车载屏幕,手指划过歌单,选了首安静些的粤语情歌,钟行微微侧过头去,看见她细软的发丝一半裹在披风中,一半垂垂洒落,将将遮住了车载屏幕的一角,她神色认真,仿佛选歌这件事十分重要一般。
限速一百二十的机场大道上,钟行的车速仅有八十码,偶有身侧闪过的车辆疾驰而去,吉他主调的情歌缓缓流淌在车厢内,仿佛窗外风声不再呼啸。
他打破了沉默,“去C市出差,去吃了宵夜么?那边的宵夜生活很是丰富。”
沈知欢此时拿着披风给自己裹了一个舒服的姿态,懒懒的瘫在座椅上,很可惜地说,“本来想去的,可是每天都加班到半夜,夜宵摊都快关了。”
话题就此中止,钟行这种惯来会找话题的男人一时之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好似在沈知欢面前,他变得沉默而不洒脱。
却是沈知欢忽而想到什么一般,问道,“不对啊,我哥有夜生活,你怎么会没有?竟然能被他指使来做司机?”
钟行心里一时觉得有些好笑,却道,“我就那么像那种天天有夜生活的人吗?”
却被她说,“不像么?”
他一时语塞,一时之间被噎住,却依旧玩笑,“看破还说破。”
话锋一转,问她,“你怎么不像你哥有些夜生活。”这句话是个铺垫,他转而问了那句他真正想问的话,“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钟行目视前方,却止不住从后视镜去看沈知欢的表情,就见她轻微耸了耸肩,“不知道,应该喜欢帅的吧。”
然后她思索了一下,自我发问,“然后居家一些的?”
钟行顺口道,“我不够居家吗?”
一时之间将沈知欢逗笑,她工作多日的困意一时之间有些消散,笑道,“钟少,这话你都能这么理直气壮说出口的吗?”
钟行语气不变,依旧是个肯定句,“看人不可以只看表面。”
他把话说的轻飘飘,让人听不出话里的真心来,一时之间连他自己都有些恍惚,恍惚自己究竟是抱了什么样的心情来说这些话,到底是真想同沈知欢逗趣,还是自己有了什么其他的念头。
沈知欢调整了一下坐姿,更像只昏昏欲睡的企鹅,她困意氤氲,连眼底都有些水蒸气,却还撑着困同他聊天,她把头摇的像拨浪鼓,然后说,“不行不行,我不好你这一口。”
透过后视镜,钟行见她将自己上下打量了两秒,大概她觉得他是在和她开玩笑,然后她说,“虽然你很帅,可惜我是干风控的,你这种男生不是我把控得住的,我觉得不行。”
钟行不欲再让她强撑睡意聊天,于是止了话题,不稍两分钟她便睡过去,透着昏黄的照在她脸上得路灯光圈,钟行看清了沈知欢眼下的乌青。
车子速度变缓,四十五分钟的车程行驶了一个多钟,抵达小区时她依旧没醒,钟行没熄火,也没按掉车内音箱,生怕多一些动静就将沈知欢吵醒。
他也不看她,只是静静地在车里坐了很久,然后伸手为她将有些滑落的披风盖好。
有那么一刻,看着沈知欢洒在脸上细碎的睫毛影子时,钟行有想吻她的冲动,可最终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她较好的面颊,却连她洒在脸上的碎发都没帮她拢好。
听了很多首曲子,钟行轻身下了车,他从口袋中找出打火机来和烟盒来,却在火焰即将靠上香烟时他熄了火,转头看了看车内的沈知欢,最终还是没抽那根烟。
他就这样靠在车旁,任初冬的冷风钻进单薄的毛衣,此时此刻他忽而明白,不知为何,沈知欢于他而言是不一样的。
他说不出这种不一样源于哪里,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会面,也从未有什么深入的交谈,只是寥寥几面,他却连靠近都不敢唐突。
或许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便是如此,不知究竟从何开始,也不知为何她便变得重要。
很久后沈知欢醒了,她迷蒙的解开安全带,探着身子按下驾驶座的窗户,同钟行说,“到了很久了么?你怎么在外头站着。”
钟行将指尖未点燃的烟收起,道,“也没到很久,看你睡着了,就让你多睡会。”
她打了个小小的哈欠,一骨碌下了车,“你可以叫醒我的,没必要这么绅士。”
她从后尾箱将行李箱拿下来,然后说,“走吧,我哥不是说请我们吃宵夜么?”
可钟行却是将她送到电梯口,“不吃了,回去休息吧,我也差不多回去。”
她没再挽留,说,“那你到家说一声哦。”
钟行轻笑一声,那声笑音只是很轻地在喉腔震动,“还怕我被拐了不成?”
然后他说,“好。”
7
沈知欢的生日是在冬季,多次旁敲侧击后沈向南粗壮的神经终于有所察觉,某个干饭的中午,他忽而后知后觉地问钟行,“你最近怎么老打听知欢?”
钟行风轻云淡地抿了口茶,意味深长地给了他一个凝视的眼神。
沈向南活脱脱一副见了鬼的样子,“是你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
他“嗖”地一下站起来,“兔子都不吃窝边草,你竟然还想冲我妹下手。”
果然,再怎么兄弟情深,一旦涉及到亲妹,自己兄弟就成了想拱白菜的深山野猪。
钟行倚在椅背上,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桌面,“我是想追你妹,又不是想挖你墙角,你激动什么?”
沈向南咬牙切齿吐了句脏话,然后道,“那你还不如撬我墙角呢。”
钟行说,“可惜我对你的品味没什么兴趣。”
直到沈向南冲他翻了N个白眼后,沈向南道,“要不你还是算了吧,知欢估计不好你这一口。”
这回轮到钟行落了下风,他开始沉默起来,难得的没有将沈向南噎回去。
然后很久之后,他出了声,“你别管我,就跟我说,她喜欢什么礼物就好了。”
可惜最终沈向南想了很久,摊了摊手,“感觉她什么也不缺。”
直到沈知欢生日那天,钟行都不知道送什么,他逛遍了各类饰品,却都觉得她不爱这些,于是在她生日前一天时,他驱车路过花店,那时他倒了回来,想,那不如就买花吧,女生大多还是爱花的。
可却在踏进花店时犹疑了许久,店主建议他买玫瑰,他却怕太露骨,推荐他买桔梗,却又担心她看不出他心意来。
怕太夸张,又怕太简朴;怕她觉得接受不起,又怕她接受的坦然。
大抵这是钟行这么多年第一次如此选择困难,偏偏花材也不算礼物中十分贵重的,却让他思来想去很久,直到老板娘信誓旦旦保证给他混搭出一捧恰到好处的花束来,他才止住了纠结。
沈知欢生日那天天气不冷,钟行从沈向南那处得知她晚上还有聚会,便挨到了她结束聚会时将她堵在小区楼下。
沈知欢有些微醺,在楼下见到他,有些惊讶,“钟少,怎么今天有空来找我哥?”
他没将车子驶入车库,只是停在她公寓楼下,趁着夜色,他看到她眼底的坦然,却也看透自己心中的晦暗不明,他说,“不是来找你哥的,是来找你的。”
她陡然让自己清醒了一些,进入能正常对话的模式,可惜酒精上脑,说话有些迟缓,像一只行动迟缓的考拉,却把真性情表露无疑,她抬首思索了一两秒,发出了一个疑问的“嗯”字,然后问,“找我做什么呀?”
钟行开了后备箱,那束名为紫霞仙子的玫瑰混着多头的果汁泡泡赫然摆在里头,他舍得钱,自然老板娘也舍得花材,大抵一百多个花苞庞然的躺在那儿,一时之间让人有些视觉冲击。
钟行说,“过来祝你生日快乐的。”
他此时有些后悔起来,觉得这礼物一点也不好,鲜花花材花期又短,都没一支口红耐用,论实在还不如买个LV。
他送过很多女人包,也送过很多昂贵的礼物,此时他开始计较起这捧花不够贵重来,心中暗暗骂自己昏头,觉得这种礼物十分古早,活像上世纪令人吐槽的玛丽苏剧。
可沈知欢只是愣了愣,后备箱暖黄色的灯印在她有些迟钝的眼神中,大抵是有些醉了,她第一反应是“哇”了一声。
然后她很迟缓地问,“这是给我的么?”
钟行点点头,心中有些懊恼,可她却不遗余力地夸赞,“哥,你也太会了吧,这也太好看了。”
不知她是酒后吐真言,还是酒后更爱这样同人玩笑,“难怪女孩子们都喜欢你。”她装作捧了捧心的模样,“这么上心,谁顶得住呀。”
她话中意思是在调侃他对待周围女生都慷慨送礼的习惯,
可钟行说,“这是第一次真的上心。”
起初她还以为他是如往常般说笑,还想露出个笑说句“哇你可说得我心都化了”,却在抬首对上钟行深沉的眼神时噤了声。
她忽而间清醒起来,陡然地想起她初次见钟行的场景。
那时她想,他带笑时招桃花,不笑时有些生人勿近,如今她才觉得,原来他能有这么认真的神色。
那是种十分坦然的表情,好似他就想说他就说了实话,反正他的心意就这样了,于是就这样坦荡地将选择权交给了沈知欢,却莫名让沈知欢觉得有些压迫性。
沈知欢有些头疼,她觉得钟行只是一时兴起,即便他那种神色能让女人冲动地溺进深情中去,可沈知欢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大抵她这种人过得太清醒,此时这种场景之下还能找补,“我又不是肤白貌美大长腿。”
钟行波澜不惊,“喜欢就喜欢了,我说真的。”
他没有长篇大论,他从来不是那种靠巧言令色吸引人的人,诚然他确实想同沈知欢多讲些什么,可那些话到嘴边又咽下去。
他连给她负担都不想给。
良久,完全醒酒的沈知欢露出一个难以置信的表情,她说,“哥,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8
很长一段时间,沈知欢都觉得钟行是有些不太正常。
毕竟她的世界观里是毫无浪子回头这个观念的,或者说按她的逻辑看,钟行是脑子进了水,才会试图泡自己兄弟的亲妹妹。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沈知欢都觉得自己是猎物,所以后来她都能坦然的同钟行说,“哥,你放弃吧,虽然你真的很帅,但我真没跟你谈恋爱的心情。”
她从没相信钟行是真的喜欢她,自然,也从没真的心中有什么波动。
起初沈向南也没觉得钟行是玩真的,所以他十分义正言辞地指责钟行这种见一个爱一个的无良行为,直到大半年后的某个酒局,沈向南勾住钟行的肩,问道,“你不是来真的吧,八个月了,你竟然单身八个月了!”
钟行推开他的手,坐在卡座沙发一角,坦荡道,“不行么?”
姗姗来迟的沈知欢坐在对面,离他们有些远,此时听到这话题凑过来听,被钟行这种坦然的态度洗脑久了,她都习惯了,顺口道,“你怎么坚持的?”
沈向南装腔作势,“因为动心了,遇到真爱了。”说完不忘自己“呕”一声,对自己捏造的对话感到恶心。
钟行摇晃杯中的酒,言之谆谆,“不能是累了,休息一段时间么?”
他不欲给她压力,或是说,当真的动心时,他反倒没法把情话宣之于口。
沈知欢又加入别的聊天中去,沈向南拍了拍钟行的肩,“我开始相信你了。”
钟行给了他一个略带嫌弃的表情,然后沈向南深吸一口气,说,“但老钟,我怀疑你也可能就是享受得不到的快乐,毕竟你从前没怎么吃过瘪……”
钟行嘴角抽了抽,“我又不是犯贱……”
他说完这话时恰巧对上沈知欢不经意投过来的眼神,他说,“我也没什么疯狂的想法,我就是单纯觉得,她挺好的。”
9
直到新的冬日到来时,沈知欢被外派到隔壁G市工作两年,她是在那时意识到,或许钟行是真心的。
偶有周末,他常常会出现在G市,他并没做什么,只是偶尔去看看她,在商场的餐厅吃上一顿饭,或是单纯地去接她下班,送她回公寓。
他没有一刻的逾矩,既没有主动牵她的手,也没有送她上过楼,甚至从前一个冬日说了那句“这是第一次上心”后,也再没直白地说过什么。
起初她觉得自己有些看不透钟行,甚至问过,“钟少,你也不是那种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啊,不应该是崇尚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观念么?”
可他没有回答,好像他从前吊儿郎当那一套再没在她面前拿出来,只是沉默地拿行动来证明。
后来在无数次街角吃饭,很多杯冬日暖茶和很多件初春外套中,她逐渐明白,原来钟行是骨中是这样寡言而坚定的人,开始认准有些事时,他就变得同往常不一样了。
沈知欢见识过很多男人,其中不乏有些人十分爱将自己装得深沉而多金,恨不得钱包里有多少人民币悉数贴脸上,脑子里有多少知识都摆出来。
初见钟行是他却反其道行之,偏偏装的一副吊儿郎当公子哥的模样,人人都以为他那些温和好脾气是装出来的,实则到头来,他才是那个能坚持的人。
某个他依旧送她回家,准备回启动车子返程回酒店时,沈知欢敲了敲窗户。
钟行摇下车窗,问,“怎么了,落了什么么?”
却被沈知欢没头没脑的问,“你不累吗,连着一年多每周都跑G市,就是来吃顿饭?”
她打赌他坚持不过两周,可他却坚持了将近两年。
钟行熄了火,沈知欢说,“再散散步走走吧。”
他们就这样并排走在公寓附近的江边,夜里江对面灯火通明,那是一片夜生活集聚地,江这边的住宅区却已经开始寂静,只有他们缓缓漫步,许久才有从身侧慢跑过去的运动者。
钟行玩笑道,“嫌弃我烦了?”
沈知欢笑道,“谁敢嫌弃你呀钟少。”
好似他们已经在长时间的暧昧情愫中习惯彼此,甚至可以说笑起来。
钟行有些摆烂,道,“我年纪大了,能嫌弃我的人多了。”
他说话间还有些醋意,大概是在酸上周有个小沈知欢四岁的弟弟和她冲动告白的事情。
沈知欢觉得有些好笑,他说,“四岁四岁,我大你四岁,一前一后和你其他追求者差了八岁。”
虽然话这么说,沈知欢倒真没听出他语气里对自己魅力的怀疑。
可沈知欢忽然发问,“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她问的很直接,可却问了她近两年最想问的问题,不得不承认,她是个工作狂,可自从来了G市之后,她开始盼望周末,也不知道是盼望周末的休息,还是盼望周末能够见到的人。
钟行驻住脚步,他们寻了一个地方看江景,轻笑道,“突然就考压轴大题了么。”
沈知欢被逗笑,“谈恋爱又不是考试。”
钟行背靠着栏杆,起初没说话,也不看沈知欢,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你很好,非常好,可那些优点都是别人看得到的,可具体说我究竟喜欢哪一点,我说不出来。”
他终于侧首,眼神对上沈知欢的眸子,神色很温和,两年前那些带了漫不经心和玩味的表情已经很久没在他面庞上出现,好像和她相处的时间,他神色逐渐变得柔和。
“只是和你待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生活是满的。”
“即便是一分钟,甚至不说话,我也觉得,是被填满的。”
他不欲多说,其实他是可以讲大段大段的,可以举例子可以细数她的优点,把她夸得天花乱坠,可他没有。
可他说,“我希望你和我待一起时,也觉得生活是满的。”
江对岸依旧灯火通明,可隔着那么宽的江水,对岸的喧嚣一点儿也听不着,只有细碎的江水流动声,他们一个背靠着栏杆,一个靠在栏杆上看对岸橙黄交错的灯色,风吹起衣裳的一角,互相看不清对方表情。
很久,钟行听到沈知欢用很轻的声音说,“我是的。”
她手指微凉,掌心却是热的,她很轻地牵住钟行的手,“我们试一试,好吗?”
却被很用力地紧紧握住,沈知欢终于愿意侧身,和钟行面对面站着,钟行一字一句,“当然好。”
然后他说,“这是第一次上心,也是最后一次,我说真的。”
沈知欢轻笑,“我知道。”(完)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