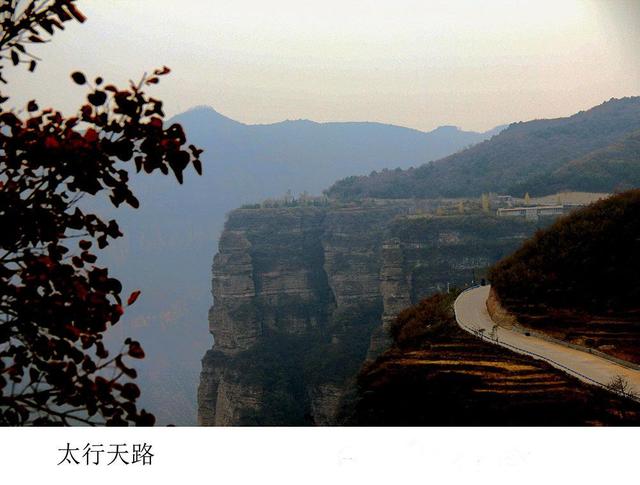一直听见蛐蛐叫(又听蛐蛐叫)
作者 马占顺

凌晨4点半,感到满世界的寂静,这是处在黎明前的黑暗,又是入秋后的日子。
突然,又好像在寂静中,听到楼下花园中的蛐蛐都在引吭高歌,我静静的站在阳台上,清一清好似还在沉睡的大脑,支起耳朵果然没有听错,就是蛐蛐又在齐鸣了。这声音是那么的清脆、是那么的悦耳、又是那么的熟悉,好像千军万马齐鸣一般,不需要指挥,不需要口令。
听着这熟悉的声音,我顿时就没有了睡意。虽然刚刚才经历了大蒸笼的北京,在立秋后的清爽夜晚里,人们需要休息,需要补充伏天里流失的各种能量,可听到这蛐蛐的鸣叫声,确让我兴奋不已。
记得是孩童的时代,我对蛐蛐就充满了好奇感:那时的小学语文书里就有一篇《蟋蟀和蚂蚁》的课文,从这篇带着插图的课文里,我才知道蛐蛐的大名叫"蟋蟀"。
这篇课文说的是到了秋天,小小的蚂蚁们都在忙着储藏过冬的食物,而蟋蟀却不慌不忙整宿躲藏在墙缝和草地里,扇动着脊背上的翅膀不停地在鸣叫。我们的语文申老师用他那特有的家乡口音,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讲解课文,还给我们讲了蟋蟀的一生和他小时候捉蟋蟀、养蟋蟀和斗蟋蟀的诱人故事,听着申老师的课程和他讲得那诱惑力极强的故事,再看看课堂上各位小伙伴们的姿势,真是太有意思了:他们有的伸着脖子,眼睛都瞪直了;有的一只手托着小小的腮帮子,小嘴里不时地还在念叨着什么。看的出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对蛐蛐充满了好奇。申老师的讲课和他对蛐蛐的感情,都让我们这群孩子好不羡慕啊!
下了课,我们都迫不及待的回到家里。我向母亲说明情况,她从那个包袱皮裹了一本旧书的夹页里,翻出印着红色图案的一块钱递给我,我手里攥着这张宝贵的票子,飞快地跑到胡同马路对面的宣武门内大街的杂货店去。进了店铺的大门,一看就让我目瞪口呆了,好家伙这个商店从厨房里的案板、锅碗瓢勺到地上用的墩布、扫把;从烟囱、火炉到枕芯、棉花被套;还有马扎、铁丝、瓷碗瓷罐,真是琳琅满目的各种生活用品应由具有。
我早就听说这有卖蛐蛐罐的,今天算是慕名而来。我不知道蛐蛐罐放在哪里,就鼓足了勇气问了一位站在柜台里的二十多岁的阿姨售货员。她一努嘴好像告诉我蛐蛐罐就在我脚边地上的木箱子里,恰在这时我看到她净白的脸上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小酒窝,我就感到在这肯定能买到蛐蛐罐。
我用手轻轻地打开地上的大木箱子,又剥开浮在上面的稻草,立马一箱子的蛐蛐罐就浮现在眼前。好可爱啊!我禁不住地叫出声来,那个年轻的售货员正好来到我的跟前,她的脸上挂着绯红,我不知道我触动了她的哪根神经,竟然还让她精神焕发了。
看到一个个的蛐蛐罐上还满涂着深棕色的釉子,在商店里灯光的照射下泛着光芒,我想这制造蛐蛐罐的师傅们肯定也是个蛐蛐迷,要不这一个个的蛐蛐罐怎么能够像蓬荜生辉一样的漂亮呢?要不那可爱的蛐蛐怎么可以在这蛐蛐罐里安家呢?我伸出手连忙在那个估摸着,足足装着上百个蛐蛐罐的大箱子里捡了3个罐体一样大小、花纹一样粗细、深浅颜色略显不同的蛐蛐罐,就去交钱。那位漂亮的售货员阿姨接过我那一张大"票子",找回我三张颜色不太相同的"票子",我接过一看一张是五毛的,两张各是一毛的。她还告诉我蛐蛐罐里要垫上一层略湿一些的土,因为蛐蛐这种昆虫喜欢潮湿,这样的环境可以适合它们"生活"。
我一听这位阿姨还是个养蛐蛐的内行,就多问了几句,原来他的弟弟也是一个蛐蛐迷,只是比我长几岁。他的父亲每年到秋天的这个季节,下了班可能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带着手电筒和蛐蛐罐,穿着大裤衩子骑着家里的那辆除了车铃不响,哪都"嘎嘎"响的破旧自行车直奔复兴门外的荒土地里、乱石头缝里去逮蛐蛐。所以耳闻目睹的她多少对养蛐蛐有了一些了解。
听着她的叙说,我心里早就迫不及待了。

不过让我高兴地是:花了三毛钱今天竟买了三个蛐蛐罐。我的心中充满了欢喜,对了申老师说还得有一个蛐蛐罩,这样蛐蛐就好捉住了。刚要迈出杂货店的大门,我又回来了,售货员阿姨问道:"是不是忘了买蛐蛐罩?"我红着脸点点头,她早就为我准备好了,这蛐蛐罩就放在他面前的柜台上。交钱拿货我拔腿就跑,恨不得马上就让蛐蛐住进我那心爱的蛐蛐罐,我看着它、守着它过上一夜,心里才舒服呢。
回到家里母亲也说蛐蛐罐不能空着,罐子底下垫上一层潮湿的黄土才行,我跑到院子里,在种花的花池边上,用小铁铲产出一点土,再找一块废旧的铁纱窗当筛子,这样筛出来的土又细又匀,没有一个颗粒。垫在罐子的底下。再用手按按让罐罐里的土平平的,就不会让做客来的蛐蛐拌着、摔着。当然罐罐里面还放点蛐蛐爱吃的小黄瓜头。
那个时候的北京,平房都集中在不太宽的胡同里。记得就牛肉湾的胡同里到处都是破旧的灰砖墙赤裸着,张着墙皮咧着墙缝,好不热闹。我早说一句,兴许你高兴了揪一根细细的扫把枝,随便往哪个墙缝里捅捅,就会蹦出来一个大蛐蛐。胡同地上的小草到了秋天就长得很高了,小秋风一吹它们会伸长了脖子向你点头。
我一直铭记着老师的教导,申老师在讲课时说蛐蛐就是藏在墙缝里或是草地的砖缝下。那怎么才能找到蛐蛐呢,晚上用手电筒照,你看不到墙缝里面,用手指头抠,太粗的手指头又伸不进去,怎么办,回到家里母亲说你从家里扫把上掰一根扫把枝,拿着它伸到不到半厘米宽的墙缝里,就能把蛐蛐斗引出来。哈哈,好主意,我想莫非母亲小时侯也养过蛐蛐吧。
再出门的时候,所有的家当都带在身上,两个蛐蛐罐用麻绳拴着挂在脖子上,一左一右,走起路来晃荡晃荡的,就跟吊着两个大铃铛似的;我一手拿着蛐蛐罩,另一只手还得拿着那根从家里扫把上掰下来的扫把枝,真是准备大干一场。
当我来到那片长满了草的裸墙之前。就看见住在胡同口上,班里的同学兰岩、毛二两个人,正撅着屁股跪在草地上一动一动的,我好奇地赶紧跑过去。在不远的地界还有一位好像要大我们几岁的半大小子,穿着个印着红花绿叶的半袖黄背心,一看就知道他脚上穿的是女孩子的塑料鞋,也在一蹦一蹦的逮蛐蛐。我看着他手里的蛐蛐罐是那么的熟悉,放到一起一比较竟然跟我的蛐蛐罐一模一样,一问才知道他就是那位售货员阿姨的弟弟。
"快,那边跑了一只"。兰岩急的脑门子直冒汗,顺着蛐蛐蹦的方向就追过去,可惜还是晚了一步,蛐蛐已经蹦的无踪无影了。"只可惜要到手的一个大蛐蛐跑了"。兰岩无奈的摆摆手,半卧在草地上,左裤腿被露水染湿了一大片,我心里琢磨这俩小子真会抢先。
"我手里捉住了一只,快,放在你那,要不就捏死了。"毛二看见我胸前挂的蛐蛐罐,急忙的说。我摘下两个罐罐,递给了毛二其中的一个。他把手放在罐罐上面,虽然他放在罐里的那只还活着,可是一条大腿让毛二捏掉了。我一看不禁"哎呦"了一声。

放在罐罐里的那只缺腿蛐蛐,就像适应了环境,不大一会儿还扇着脊背上的翅膀"吱吱"的叫着,滋着大牙,展现出高昂的战斗激情!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只活蛐蛐。虽然它"残疾"了,只剩一条大腿,但那只蛐蛐不屈的形象,高昂的战斗激情始终让我难忘!
记得在胡同里斗蛐蛐真是一场"盛宴"。两家斗蛐蛐,召的街坊四邻半大小子们都来,有穿着大背心的、有光着膀子的、还有拿着大芭蕉扇子的,能围上几十双眼观看。那天张老二拿出一只参加了几十场的战斗"英雄"。王五也放出大话,说自己的这只叫"猛子"的蛐蛐,也是"百战百胜"。后来才知道这张老二就是那位售货员阿姨的父亲。
雄性的蛐蛐好斗,它的尾部长着两个针一样的尖尖。当两只雄蛐蛐相遇时,先是竖翅各自鸣叫一番,以壮声威,激励斗志,然后就是头对头地互相瞄准着,各自张开钳子似的大口互相对咬,也有用脚踢的,斗志昂扬的一般要"厮杀"几个回合,败者无声的逃逸,胜者则高竖双翅,傲然地大声长鸣,好像是在向世界宣告"我胜利了!"显得十分得意。如果体力和个头或是战斗力不相匹配的,一个回合就会结束“战斗”。
那个秋天我养的一只个头十足大的蛐蛐,在几十场的"战斗"中都赢了!在狭小的战斗场地里,它张开锋利的牙齿经常是一个回合下来,就把对手咬的落花流水,真让我狂喜!
蛐蛐因其能鸣善斗,自古便为人饲养。据记载,中国家庭饲养蟋蟀始于唐代,当时朝中官员或是平民百姓,人们在闲暇之余都喜欢带上自己的"宝贝",聚到一起一争高下。据研究,蛐蛐是一种古老的昆虫,至少已有1.4亿年的历史了。
今天凌晨,又能听到这么熟悉的蛐蛐叫声,我静静的听、静静地在想。自从搬到了楼房,我就有这样的感觉,这恐怕只是永远属于乡居人们的了,因为我想哪只蛐蛐都不愿意随着人们迁进高楼大厦。这些小小的生灵们,它们离不开泥土和草地,在那里它们呼吸着负氧离子极高的空气、吸吮着草叶上透明的露水、享受着泥土中花一般的世界,它们即使是生活在平房的墙缝里,蛐蛐那有力的后退一弹,就会亲吻到泥土和草地。
我常想其实泥土原本就是人类的故乡,对土地的疏离,时间久了人们与土地之间也就渐渐地难以适应,人类感受不到自然的美好。
当又我一次听到蛐蛐的叫声,真让我回想,让我兴奋。这些年来人们深深地认识到"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于是大力改善环境,整治污染。
我想如今,这蛐蛐们的齐鸣高歌不就是大自然的原声吗?
写2018年8月20日
改2019年9月30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