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古村蝶变纪实(他们的良方勾勒出历史村镇未来的模样)
傍晚,四川眉山的柳江古镇,云色渐暗,星雨飘落。
这个距今800余年的历史古镇迎来了一批来自海内外的特殊客人。一场极具当地特色的民俗文化演出,雨水滴答,微风习习,灯光斑斓,宾客沉醉其中。
6月10日至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百余名海内外专家齐聚四川眉山,共话历史村镇之未来。未来什么样?上百名海内外专家学者把脉、问诊、开方,勾勒着他的模样。

↑ 6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史村镇的未来会议继续在四川眉山举行
在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心里,历史村镇的未来该是这样的:有村,也有好的商业,还有完备的设施,还会有城市的生活方式,有教育,有秩序,有良好的社会组织结构,人们出得去,回得来。“其实,就是元明清前的江南和四川村庄的模式。”
这,更像是一场回归,但又不仅仅是回归。问诊,是为了让未来历史村镇要走的路,更平顺。
【他们的状态】
有的正在老去 有的正接受“就诊”
6月11日的会上,如何让历史村镇有更好的未来,海内外的家学者们的分享和讨论依旧热烈。讨论越热烈,越说明当前历史村镇面临的状态。
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从农耕社会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急速转变,截至2017年底,中国城市人口已达到总人口的58.5%,自2000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1.3%。据媒体公开报道,近10年来,有90万个中国村落在消失,从2000年的360万个村落到现在只剩不到200万个。无疑,很多村落正在慢慢老去,甚至消亡。
住建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委会委员、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方明说,中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农村的人最多,村庄的数量可能也是最大,而城乡本身的整个格局在发展,城镇化的格局在不断变化,很多人往城市里聚集,很多农村空心化了,有些村庄甚至消亡,未来还可能会加剧,有些小的村庄慢慢就变成散户了,甚至一些小镇变回了乡了。“历史村落慢慢变成了老爷车,人们更向往拥有一台现代汽车。”
世界范围内的情形亦是如此。联合国2018年报告《世界城市化前景》显示,目前5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68%。世界无疑正日趋城市化,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异正在变得模糊。
不过,人们已经认识到城市化进程的代价,诸如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移民,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政策导致农村地区发展的落后。
自2012年起,中国实施了传统村落保护工程。通过5次全国性的调查挖掘和认定,国家级传统村落已达6819个。在传统文化遗产保护、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善保护机制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14年,中国发布“国家新城镇化规划(2014-2020)”。规划强调,要“保持乡村景观,民族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少数民族村落和乡土房屋”,保护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文化遗产首次融入国家一级的农村发展。
不止是中国,在中国之外多个国家和地区里,许多历史村落正在老去,逐渐消亡。当然,也有村落正在进行相应的保护发展工作。
【他们的病根】
有的无药可用 有的用错了药
6月11日,结束了上午的会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购买了当天返程的机票。临走前,他还要再去眉山城区的三苏祠看一看。这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父子的故居,其历史文化价值斐然。

↑ 6月11日,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长刘士林在会上
在这一次的发言中,从事多年城市研究的他,发言主题正是“文化”:历史村镇的保护和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引领。
刘士林说,关于历史村镇的未来,有一个核心、长期探索担忧至今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就是历史村镇作为一种延续下来的传统聚落形态,与当今世界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其核心是作为传统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与历史村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
一段时期以来,大家一直争议于“原汁原味的保存”“修旧如旧”“拆了再建”“复古建筑”等。整个过程中,虽然在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上有一定的进步,但总体上仍处于探索之中。
刘士林说,在历史村镇的改造过程中,有两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一种是老派的观点,就是完全不拆,追求原汁原味,不考虑经济和居住的功能。但实话讲,老房子实际上很多看着好看,住着确实不是很好。或者加一些现代的功能,保存原貌和空间,只在功能上做一些置换。”
另一种则是另一个极端,“拆了重建”。
“在旧城改造,传统古建筑改造,古城古都等上面,最初大家都想的是发展经济,因为老建筑对于承载现代建筑的功能很差,不比现代的大商场,空间结构也承载不了。以经济为代表的时候就是一拆了之,因为实际上往往保护比重建成本更高。”刘士林说,“而仿古建筑,则完全是假的。”
刘士林认为,中国传统村镇的保护不应该以经济为目的。但也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经过前面这些曲折的、片面的、粗放不可持续、质量不高的建设后,现在正在往一个正确的道路上转变。“人们开始注重这个村镇的文化引领价值,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收获。”

↑ 6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等人在洪雅县柳江古镇参观 文博摄
在住建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委会委员、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方明看来,中国历史村镇丰富而多彩,各具特色,可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们作为文明古国,文明大国,但历史的遗迹相对来说却不多了,这是很遗憾的事。”
“而让人困惑的是,乡村整体在衰亡,但我们的保护意识还很欠缺。因为资金、人们的需求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没有准确地判断好,或者说判断好也改变不了,从而带来了一些衰败和空心化。对身边的文化熟视无睹不当回事,过于追求物质,对文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方明说。
【他们的良方】
文化做“药引”城乡合力互补
这些状态各异的历史村落,如何才能从“老去”的状态中,恢复活力?海内外专家在两天的会议中,不断地就自己的专长,开出一张张“良方”。
四川省住建厅副厅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樊晟结合四川的实际,开出的“方子”是:小组团、小规模和微田园、生态化。
樊晟介绍,四川正积极研究适宜乡村特点的设计模式和施工方法,采用合理的模式,避免对乡村环境的破坏,在注重历史建筑的保护,推进应用现代新的技术,实施房屋改造,推动传统建造工艺的传承和创新,使乡、组、人三者成为紧密相连的生命体,着力让四川传统历史村落与传承活起来。
生态这个词,也出现在方明开出的“方子”中。他说,乡村的主要价值还在于生态,历史村寨在于它的文化价值,又在于它的使用和旅游价值。文化是长久价值,从局部来看可能并不是那么显现,所以可以依托旅游来刺激和激活,来启发本地人对文化的尊重和重视。
刘士林从事城市文化研究多年,在他看来,历史村镇的保护传承的关键,在于“文化引领,区域和城市高质量发展”。他说,“文化引领”是灵魂,而经济则应处于被引领的地位。这样,城乡之间才能在一定的机制中合力互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部合作及通讯部门主管多琳.杜布瓦和威斯敏斯特大学城市规划副教授朱力奥.维蒂尼两人的“良方”中,也把文化放在首位。
在他们看来,文化会起到桥梁的作用,只有文化才能明确传统村落有哪些优势,政策才能因地制宜去加以保护和推动。

↑ 6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等人在洪雅县柳江古镇参观点赞 文案摄
需要文化,当然,历史村镇中还不能少了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埃内斯托·奥托内在之前接受红星新闻的采访时曾表示,村庄里,人才是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埃内斯托·奥托内说,在农村地区,除了要改善村落的生活条件和水平,还要给年轻人提供条件,让他们能够获取技术,让他们能够联网获取服务的机会,让他们和城市的人获得同样的服务,生活方式。
【健康的模样】
因地制宜机会变多 大家都充满活力
陶渊明用《桃花源记》描摹心中安宁和乐的村居景,沈从文笔下流淌湘西的山清水秀和浪漫诗意,英国作家彼得梅尔以三部曲书写普罗旺斯的山居岁月……
按照专家们开出的“方子”,村落们“药到病除”后,会不会成为文人挥毫描绘的故土画卷?
“它或许是一台老爷车,跑向现在,跑向未来,跑向世界。”中国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方明认为,村镇和城市的距离感会逐步拉近,融为一体,真正热爱乡村文化和生活的人,会成为复兴老村老镇的主人。未来的中国历史村镇,会用传统的方式来发展现代化经济产业,住房交通等硬件环境将得到改善,在世界层面上,摆脱低端化和同质化,向高端时尚化靠拢。
“它或许会像元明清时期的江南或蜀中城镇,作为一个理想的小社会,每一个个体都能在里面找到合适的位置。”刘士林如此描摹未来的村镇,“商业兴旺、教育发达、秩序井然,社会组织结构良好……最重要的是,离开后可以随时回来,而不是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这样的未来,曙光初现。威斯敏斯特大学城市规划副教授朱力奥·维蒂尼在6月11日上午的会议中介绍,中国农村地区的许多历史村镇,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政策,明确了自己的文化优势,已经在现代化中有了耳目一新的变化。
“如青神县的传统竹制品就借助文化有了创造性,把匠人精神运用到了现代化生产中;幸福古村的文化景观得到了保护,网上销售的方式也使本地产业得以量化、铺展。柳江古镇更是一个成熟的案例,本地居民的积极参与也促进了旅游行业的发展。”朱力奥·维蒂尼说,展望村镇的未来,不同地区的村落会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政策发展。

↑ 6月10日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等人在洪雅县柳江古镇参加文化体验之夜 文博摄
在11日的会议上,眉山的苏东坡博物馆进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视角”,因为它曾遭遇火灾等,经历过改造和重建,目前的形态是20世纪初遗留下来的。如今,既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首要目的,又能为年轻人和老年人提供一个包容性的休闲场所,充满人文活力,而不仅仅是为了盈利而进行旅游开发。
充满人文活力,是许多专家对历史村镇未来的期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埃内斯托·奥托内如此形容,“保留着过去,生活在现在,未来是动态的,但又能留住年轻人。”在他的理解中,生活在现在,意味着历史村镇创造着有质量的空间和人文环境,能够使年轻人能够像在城市一样,便利地获得就业、服务、技术、生活方式的机会。
留住了人,就留住了村落,人年轻了,村落的活力,自然就有了。
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蒋麟 陈柳行 摄影报道
编辑 汪垠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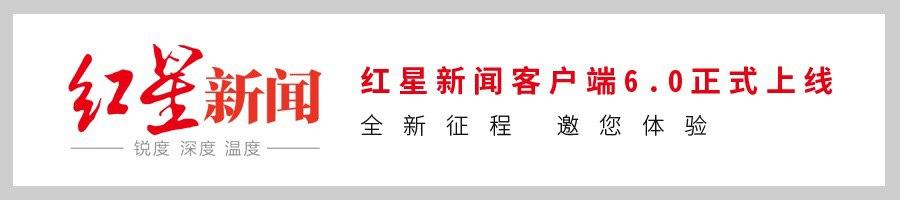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