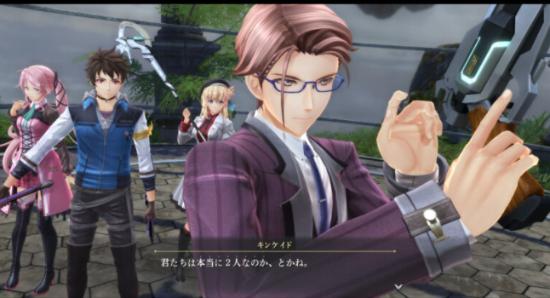历史周期问题解析(3000年来的历史周期率)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而且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被注意到。《诗·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是历史周期率之雏形。
孔子对此也高度重视,他甚至专门收集资料进行研究。《礼记·礼运》:“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最后孔子得出结论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至此,历史周期率已经成型。
孟子则直接为历史周期率的周期进行了界定,指出历史的循环周期是500年。《孟子·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公孙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现在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向天再借500年”,其数据就是来源于此。
到了西汉,董仲舒和司马迁都对历史周期率有所进一步发明。董仲舒提出了制度上历史是“夏、商、周”周流循环的著名的“通三统”理论。司马迁则这种历史循环的内涵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基于考古资料,并参照中国的文献记载。我对5500年前以来,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历次中西文明交流,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并绘制了上图(中西文明交流和历史曲线图)。从5500年前至1840年这5340年中,共发生了13次中西文明交流,平均445年一次。其中,公元前的周期稍长一点,500年一次,公元后的稍短一些368年一次。
实际上,可以识别出的最早的中西文明交流发生在8000年前左右,其重要的证据就是原产于中国的小米的西传,其他的证据还包括,彩陶在中国和西亚的同时出现。
但是,可以确认,大约5500年之后,中西文明的交流才常态化、周期化。我稍微详细地列举其中的10次,从中国尧舜唐虞时期开始,以让大家建立一个更具体的印象和认知。

第十次,尧舜时期至夏朝成立
这是正式的政府在中国出现的时期,尧舜之前中国没有正式的政府。同时这个时期也是古两河和古埃及文明中正式政府出现的时期,在此之前那里也没有正式的政府。时间在大约公元前4200年前至于公元前2000年之间。
政府包含三大元素:对和平的人间秩序的认知和维护,对权威的宗教式虔诚,暴力专制。可以简称为:秩序元素、宗教元素、暴力元素。自开始至今,政府都包含着这三大元素,只是不同要件的比例,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明中是不同的。
但是,这三大元素并非在一个地方出现的,而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秩序元素起源于东亚中国,宗教元素起源于西亚,而暴力元素则起源于中亚游牧。文明的交流将这原本分布在三个地方的东西得以融合在一起。这种首次大融合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其结果就是政府在中国和西亚的同时出现。
人类社会自身可以自然自发地维持良好秩序,这种理念起源于中国。在尧舜之前,中国就早已形成这样的秩序。《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说的就是处于这种秩序状态的上古社会。
“结绳”和“书契”是契约的最原始的两种形态,“结绳”是一对打着绳结的绳子,“书契”是一对刻有契齿文的木片或竹片。“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在政府出现之前,中国的上古历史是一个漫长的契约秩序时代。
而在政府出现之前,西亚则是一个多神教社会,没有独立的人间秩序的概念,而只有神的秩序。中亚游牧也没有秩序的概念,而只有暴力和暴力掠夺。
只有契约秩序,不可能会有政府。只有多神教,也不可能有政府。只有暴力,更不可能有政府。唯有三者结合起来,才导致政府的出现。这就是尧舜时期中国发生的事情。同一时期,同样的事情也在古两河,即古埃及文明发生。
对古两河文明而言,政府出现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成文法的出现。法律是用来维持人间秩序的,这对他们而言是个崭新的东西。法律起源于契约。在中国的语言中,法律和契约的亲密关系,依然被保留着。“法”就是“约”,“公约”。“约”就是绳子、结绳,也是契约。我在此前已经对“法”和“律”的甲骨字形做过详细考释,他们都直接来自契约机制,都是契约文字。
因为西亚缺乏契约实践,也缺乏独立的契约精神,因此,当中国的契约传播至古两河文明时,他们把契约多神教化了,从而就成为所谓的“法律”。在中国,契约是契约双方之间的事,基于两者的直接信任,即基于“诚”。但是,古两河文明却引入了一个具备绝对权威的第三方——神。他们把作为契约参与者共识的“公约”,说成是神的意志和指令。
古两河最早的成文法是《乌尔纳姆法典》,出现在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3-2006年)。最完整的则有后来古巴比伦的《汉姆拉比法典》。乌尔第三王朝对应于中国的尧舜时代,古巴比伦王朝则对应于夏朝。
同时,中国也对来自西方的多神教加以改造,形成具备一神教核心元素的“上帝教”,同时,将其边缘化。中国的“上帝教”是后来的一神教的最初状态。

第九次 商代夏
时间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中国出现商代夏,古两河和古埃及同步出现朝代更迭。古两河的巴比伦王朝被加喜特人摧毁,进入加喜特王朝。加喜特人是来自中亚草原的游牧人。而且加喜特王朝的存续时间也与商朝高度一致。古埃及则进入新王国时代。
同时,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亚该亚人进入希腊,出现迈锡尼文明,与加喜特人一样,他们都有中亚游牧背景。
中国的“上帝教”传入西方,一神教开始在西方出现。包括犹太教、埃及新王国时期埃赫那吞搞的失败的“新教”,以及印度雅利安人所信的婆罗门教。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是一神化的,但却失败了。婆罗门教是一种准一神教,有着多神教的外表,但是其内在精神是一神化的。
同时,中国的商朝比夏朝在宗教上更虔诚了,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祭祀方式,就是以文字为祭品的“策祝”、“策祭”,而文字的形态就是甲骨文。显然,甲骨文的出现是作为一种祭祀手段,而从当时的古两河、古埃及引入的。
但这绝不是说,甲骨文本身对中国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全部外来。我在以前文章已经专门讨论过从“文”到“字”的演变过程。甲骨文只是借用了古两河的用符号表达语言的做法,但是在字形构造上,却主要是继承和借用了早已在中国存在的“文系统”,包括契约符号系统和易经符号系统,以前者为主。“文系统”直接表达“意”的独立的抽象符号系统,与语言无关。
中国在“字”上的出现的确比古两河为晚,但是,在“字”之前,中国所存在的成熟的“文系统”,却仅仅为中国所有,而为古两河所无。即中国有“文”有“字”,但是古两河却只有“字”,而没有“文”。
上古中国的“文系统”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独立的抽象符号系统,而且为中国所独有。“字”在古两河的出现尽管比中国早,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中西文明交流和历史曲线图》中,处于第十二个次交流周期,但是,“字”并非最早的符号系统,“文”才是。只不过“文”是表达“意”的工具,但是,“字”下沉了一个档次,是表达语言的工具。综合各种资料,可以判断,“字”在古两河的出现,是中国的“文系统”西传的结果。符号系统的理念和习惯来自中国。

第八次 周代商
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当中国发生周代商的朝代更迭时。西方也同步出现了类似的变化。古两河的加喜特王朝被推翻,此后北方的亚述崛起,进入了亚述帝国时代。古埃及的新王国时代结束。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也在同期被终结。
整个世界都在遭遇新一轮的来自中亚东欧游牧人的野蛮攻击,同时也深受暴力的影响,此后政府中的暴力因素强化,专制形政府开始出现。最典型的就是以残酷征服而著称的,亚述帝国。中国周朝的暴力专制因素也明显比夏、商为高,开国之初,周武王的亲兄弟之间甚至自相残杀,系统的封建制就是在周朝形成。

第七次 春秋
春秋之后,中国开始经历“礼崩乐坏”式的空前社会剧变。周朝崩溃,而进入诸侯混战的时代。在社会制度发生系统性崩溃的同时,新学术和新思想开始突发式的出现,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最后这个过程被秦帝国的出现而终结。
类似的变化也同步在西方上演,而且比中国还要惨烈,他们不是制度的崩溃,更非朝代的更迭,而是文明的彻底消失。古两河古埃及文明,这两个与中国并存了4000多年的文明,从此踏上不归之路,最终彻底消失。同时,西方也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现象,不过已经不在古两河古埃及了,而是在希腊和印度。新哲学和新的宗教理念出现了。
帝国作为新兴的政治形态开始出现。帝国有三大特征:一是重视普遍适用的法律,二是重视暴力,三是以国家为国王个人私产。波斯帝国的出现是帝国式政治形态成熟的标志。然后又出现了三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印度的孔雀帝国,以及中国的秦帝国。
显然,帝国式政治形态在中国的出现,是受当时西方的影响,主要是波斯帝国的影响。而全球范围内“诸子百家”的出现,也是中西文明的结果。深入研究当时的各家思想,可以看到,希腊哲学和佛教的内核都来自中国的儒家,而中国非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其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西方元素,尤其是法家,明显是受到了亚述-波斯文化影响的结果。
总之,中国的诸子百家以儒家为核心,而全球的诸子百家则以中国为核心。全球诸子百家只是中国诸子百家的放大。

第六次,两汉之际,公元1世纪左右
三个新帝国同时形成:西方的罗马帝国、连接中国和印度的贵霜帝国,以及中国的东汉。
中国的经学初步成形,印度佛教开始经贵霜帝国而传入中国,西方则出现了基督教。当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的经学实际上也影响了佛教。同时,基督教的出现显然是受佛教和中国经学双重影响的结果。
大乘佛教的出现,是印度再次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更强调佛教的“天下”性,更注重人的内在心性。基督教相对于犹太教,也是更注重内在的心性,更强调人对上帝的信仰和情感。同时,基督教的“基督”为“王”说,“道成肉身”说,显然都是来自汉朝的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传》。

第五次,魏晋南北朝,公元五世纪左右开始
这是中国历史上再一次面临大混乱。最典型的事件就是“五胡乱华”,在北方游牧的攻击下,东晋政府惨败,被迫往南方迁移,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南渡”。
罗马帝国也同样遭遇了游牧人的攻击,并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印度的笈多王朝也在同期因为游牧入侵而崩溃。
在学术上,全球也发生高度一致的变化,都是更注重人的内在心性。中国出现了魏晋玄学,佛教出现了大乘有宗,基督教则出现了奥古斯丁主义。
魏晋玄学的目的就是反对汉朝经学中的“象数主义”、“文字主义”。“象数主义”认为,易经的根本在象数,即易经的八卦符号,易理根源于这些符号。这实际上是一种迷信的神秘主义。这样的看法在整个经学中,就表现为“文字主义”、“章句主义”,认为经学中的“义理”,是本于这样章句和文字的。魏晋玄学的最大贡献,就破除了这种学术上的神秘主义,尤其以破除易学上的“象数主义”为代表。对此作出卓越贡献的就是王弼,他提出的“得意忘象”的观点,让易学和经学的研究重心回归到“意”、“义理”。
而魏晋玄学的出现,是在佛教已经传入中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也是吸收了佛教更注重内心觉悟的理念。这就涉及到中西文明交流的相互性和反复性。佛教本身是受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而出现的,但是,当佛教传入中国时,却可以反过来影响中国,帮助中国破除新出现的迷信。
同时,佛教则再次接受中国思想的影响,而变得更进一步心性化。其标志就是大乘有宗的出现。释迦摩尼时代的原始佛教讲“因、果”,整个世界都是“因、果”的流变。这个“因、果”非常类似于《易经》中的“阴阳”。但是,佛祖却认为“因、果”流变是无常,无常就是苦。到了大乘时期,不讲“因果”流变了,而讲“空”。即“四大皆空”,佛教成为“悟空”的学问。但是,在中国的魏晋时期,一个新的佛教流派出现了,就是“大乘有宗”。
“大乘有宗”承认人内在的心性的存在,并以这种内在的心性为研究中心。不过他们不叫心性,而叫“佛性”。这一新兴派别在印度佛教是非常边缘化的,但是在中国却大行其道。实质上,佛性论的出现,就是受中国心性论的影响的结果,当然也出现了异化。
中国心性论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佛教,而且影响了基督教。作为基督教神学基石的奥古斯丁主义,就是受中国心性学影响的结果。奥古斯丁之后,基督教的神学体系才真正成型。奥古斯丁强调两点,一是上帝的绝对的善,可以概括为“神善”,或“神本善”,对应于中国儒家的“性善”、“性本善”。二是,人应该对神发自内心的信仰。
具体到神学设计上,奥古斯丁反对“事功救赎说”,而坚持“上帝预定论”。人能不能得救,并不受到其外在的事功的影响,而是上帝已经预定好的。这一看似严酷的神学设计,实际上逼迫人将对上帝的信仰化为内在的,而不能仅仅将上帝看成一个得救的工具。在将上帝内在化的同时,也就是将上帝之善内在化了。因此奥古斯丁实际上是基督教版的孟子。其实理论实质与孟子相通。

第四次,唐末、五代十国,公元八、九世纪
有人认为,五代十国的军阀干政时期,是秦汉之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我同意。但是,如果放眼全球,当时陷入黑暗的不仅是中国,而是全球同此黑暗。这个时期,是一个全球大黑暗时期。
当时的世界已经成三足鼎立之势:东方的儒家中国,西方基督教西欧,中间大片是伊斯兰,包括西亚北非、南亚印度的大部、以及正在伊斯兰化的中亚。导致这次全球性混乱和黑暗的,依然是主要是中亚游牧,这次是突厥人。
7、8世纪后,伊斯兰的扩张动力已经不是原来的阿拉伯游牧了,而是被新加入的中亚游牧所替代。主导阿拉伯世界的,不是原来的阿拉伯人,而是新加入的突厥人。表现上是,突厥人伊斯兰化,而实质则是,突厥人利用伊斯兰教这个平台,向世界扩张。突厥人的加入,也改变了伊斯兰教本身。
同时,中亚突厥向西、南、东三个方向扩张。向西是攻打残存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以及欧洲,向南则进入印度,向东是攻击中国。在西线和南线,突厥人都加入了伊斯兰教,以伊斯兰教为平台。东线的则没有。
正是突厥人的渗透,导致伊斯兰世界暴力倾向进一步升级,军人干政盛行。事实上,由于突厥的扩张是全球性的,也导致这种一状况全球化。
当时的西欧,只是世界的边缘,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是落后的。尽管如此,依然遭遇了突厥阿拉伯人的攻击。事实上,当时的西欧遭遇三股力量的攻击,除阿拉伯人之外,还有马尔扎人和北欧海盗的维京人,其中遭遇维京人攻击最为惨烈。因此,现代欧洲历史将这西欧的这一时期称为“维京时代”。但是,无论维京人,还是马尔扎人,显然都是受了中亚突厥的影响。这也是所谓的“黑暗中世纪”的起点。
在文明交流上,最突出的是,中国文化通过中亚游牧而西传。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纸的西传。其实除了纸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儒家思想。中国的儒家思想传到阿拉伯世界后,就成为他们的新哲学。其中有两位当时最为著名的哲学家,直接来自中亚,一位是法拉比(872年- 950年),另一位就是更著名的阿维森纳(980-1037)。这两位的出生地都是与中国毗邻的中亚。在唐朝时那里是中国的附庸国。在文化上显然都受到中国的教化。
现在中国的民间学界开始怀疑古希腊哲学的真伪问题。实际上古希腊哲学的最先出现不是在西欧,而是在阿拉伯,西欧人也是通过阿拉伯人才知道希腊哲学的存在。是阿拉伯人先对其进行重视,并进行解释。但是,尤为重要的是,后来的西欧的研究指出,阿拉伯对希腊哲学的诠释是加入了新思想的。而这些新思想,其实就是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当时流入阿拉伯的不仅仅有希腊哲学,而且还有中国的学术。但是,在当时所谓的阿拉伯哲学中,最前沿最革命性的新思想,其实都是来自中国。当时的阿拉伯哲学家也正是用来自中国的新思想,对希腊哲学做了重新的诠释。现代的西欧人往往将阿拉伯说成是西欧与希腊哲学之间的中介,其实是中国和西方的中介。
西欧则是通过阿拉伯才知道希腊哲学的存在。显然,经过阿拉伯传入西方的实则是中国化的希腊哲学。因此,才导致西欧的思想当时出现革命性变化。而开始用“理性”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从而形成了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中心的“经院哲学”。
同时,在进入黑暗的封建时代的西欧,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就是独立商人。这也是后来资本家的前身。商人群体在最初,居于很边缘的地位。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他们开始成群聚集,成为城市中独立的商人区,甚至独立的商人城市。商人阶级逐渐崛起,并最终成为社会中的重要和主导力量。这对西欧的近现代化非常重要。仔细深入研究可以发现,欧洲独立商人群体的出现,更可能是受到中国的商人的影响。因为,那时,唯有中国存在独立的商人群体,独立的商业职业。
在当时的世界,商品的主要来源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欧洲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商品。从根本上来说,当时欧洲的商人是以经营中国的商品为业的。这是后来为什么意大利的威尼斯商业最为发达的原因所在。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威尼斯成为中国商品在欧洲主要入口。中国的商品经由阿拉伯或拜占庭,然后再经过威尼斯进入欧洲。后来直通中国的海上航线被发现后,威尼斯便迅速衰落,则从反面证明这一点。

第三次,蒙古人建立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元朝,公元十三世纪
这次的主角依然是中亚游牧人,不过换成了蒙古人。蒙古人所建立的横跨亚欧的大帝国,让中国和西欧第一次直接发生了联系。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马可波罗的来华。
马可波罗之所以不畏艰险,从陆路去中国,因为此前通过经营中国的商品,早已知道中国的存在,认为那里是一个财富之都。
毫无疑问,蒙古人的行为,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和西欧之间的文明交流。我认为这是所谓的“文艺复兴”的真正原因。有一位英国退休海军军官叫孟席斯,处于对航海海图的兴趣,他开始研究早期航海史。他的结论是惊人的,在哥伦布决定要发现直通中国的新航线时,他手中是拿着已经画好的航海图的。那么当时谁有能力和资格画这种全球性的航海图,答案是中国明朝的郑和船队。
进一步,孟席斯还认为,是郑和船队到达了意大利,并且带来了以《永乐大典》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从而引发意大利出现“文艺复兴”。其实“文艺复兴”的出现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不过,孟席斯的基本观点是没有问题的,中国文化的传入是文艺复兴的重要原因。不过不是通过海路,而是主要通过陆路。这以过程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就开始了。

第二次,郑和下西洋,西欧大航海,西欧直通中国海路的发现
现代西欧人在鼓吹所谓的“大航海”时,却对两个基本的事实避而不谈。一个是,哥伦布决定航海冒险的时间距离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仅仅60年。另一个是,哥伦布航海冒险的基本动因,就是开辟直通中国的新航线。这意味着,西欧“大航海”无论在是航海理念和技术上,还是大冒险的基本动力上,都是来自中国的影响。
中国和西欧之间的文明交流并非从“大航海”之后才开始,但是,直通中国海路的发现,的确大大加快了中国和西欧之间的文明交流。除了商业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传教士。
“文艺复兴”所带来的新文化,再加上教会的腐败,两种因素叠加,导致基督教的“新教革命”出现。所谓的“新教”,其实不过是基督教的再一次“心性化”运动,更强调信仰的个人性、内在性。表面上是回归奥古斯丁主义,而实质则是西欧再次受到中国心性文化影响的结果。因此,“新教”与奥古斯丁主义还是有根本不同的。“新教”更强调去“中介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可以自主地去信仰上帝,而无需教会的中介。
为了抵御“新教”,天主教会决定发展新地盘,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一个叫“耶稣会士”的新团体。于是,耶稣会士就开始随着商人,坐上大船,沿着新航线而进入中国。此时正值中国的明清之际。
就传教的目的来说,耶稣会士是失败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惨败,因为,当他们将中国文化的资料传回西欧时,却意外地引发巨大热情,更多的西欧人感兴趣的不是如何让中国信仰基督教,而是如何让欧洲变成中国的样子。而中国的文化是非宗教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都是立足于人自然属性,立足于人的心性。因此,欧洲不仅再次经历一次心性化运动,而且这次的心性化还是完全脱离昔日的宗教系统的。因此,最终西欧推翻了上帝,抛弃了宗教,形成了所谓的“现代文明”。
西欧的近现代化过程,是以学术为核心展开的。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欧,包括整个西方,逐渐开始有了真正独立的学术,此前的学术都是依附于宗教的。包括他们极度讴歌的希腊哲学。他们也管自己的学术叫“哲学”,就是现代被中国学术界成为“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东西。
仔细研究就不难发现,所谓的“西方近现代哲学”不过是对中国心性学,尤其是对宋明理学的学习笔记,而且学的不太好。西方近现代哲学不过是异化的,甚至有点伪劣的心性学。尽管如此,西欧还是藉此以“启蒙”,而大胆地否定了基督教,进行自认为很光明的“现代文明”。
同时,这次文明交流,还影响了中国。现代中国和西欧都忽略了彼此的影响。西欧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明末清初儒家的影响,著名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人。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限制君权的“民主”思想,实际上就是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但却被现代人说成是思想创新。王船山、顾炎武的所谓新思想,也都是如此。
更为重要的是,在明朝亡国、清兵入关的压力下,清初大儒更加羡慕西欧的不讲道义、义理,而只注重实效的文化。于是,他们开始明确地反对偏重义理、心性的宋明理学。这一幕极具戏剧性,当西欧人拥抱中国的宋明理学时,清初的大儒却在极力抛弃。
最终,清儒将“实学”的精神,引入学术之中,他们决定以实证的文字考据,绕开宋明,直指两汉,企图恢复汉学,以及恢复真正的孔孟之道。
从学术上来说,清朝考据学实际是包含着西方文明要素的,这是这种因素,导致一心复兴经学的清儒,实际上缺乏对经学的真诚的尊重。这让看似严谨的清儒,实则非常轻率、轻浮,凭借文字考据,而动辄否定中国传统的经典。说这部书是假的,那部书是假的。
清儒的这种轻率、轻浮在晚清的康有为身上表现的尤为卓著。他们“名著”《心学伪经考》直接说王莽之后的《五经》全部为伪造。这本书出版三年之后,甲午海战爆发。在当时特殊情况下,中国人对《五经》的信心骤然崩塌。辛亥之后,孙中山临时政府的临时教育部长蔡元培宣布,废止读经。
因此,中国文化信心的崩溃,实则为西方文化两次入侵的叠加结果。第一次是和平的传教带来的,第二次才是鸦片战争之后。

第一次,鸦片战争
目前鸦片战争不过180年,此前的平均文明交流周期为445年,公元之后的要短一点,也为368年。因此目前依然处于这次文明的交流周期之后,尚不能下结论。
同时,按公元之后的文明交流周期,现在恰恰处于这次交流中期的中点。刚刚结束上半段,进入下半段。从中西文明的当前态势看,也正在面临巨大的反转。
过去的180年,中国迫于亡国灭种的压力,最终彻底否定了自身的文化,以日本为中介和模板,而引入了“全盘西化”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开后至今的40年里,中国迅速实现了经济的崛起。目前,不仅亡国灭种的压力已经解除,而且中国也由昔日的弱国,迅速晋身为世界唯二的新列强。昔日的西欧列强,在中国面前已成“列弱”。
中国发展重心正在发生转移,由重视硬经济实力,而转向重视文化自信;由经济崛起转向文化崛起。当前中国思想的最前沿,是历史反思和文化反思。不仅重新认识和反思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也在重新认识和反思西方的历史和文化。
180年之后,在中国面前,欧美失去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优势,而且还有文化和制度上的。在欧美内部,贫富差距二战以来再次戏剧性的加大,这引发普通百姓的普遍不满。开始出现反对欧美主流价值观,反对“政治正确”的“民粹主义”。
可以预期的是,下一个180年,中国将向自身文化的回归,而西方则会再一次地向中国靠拢,正如过去历次文明交流中所发生的那样。

最后做一个简短总结。
从5500年前以来,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中西文明的周期交流史。平均周期为445年一次,其中公元前500年一次,公元后368年一次。
在历次文明交流中,尽管交流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却是以中国为主导的。在每一次文明交流周期中,中国先是受西方文明影响,偏离自身的文化,而后又会努力回归。因此,整体而言,中国文明是循环的。
西方文明则不然,每一次文明交流,都是一次向着中国文明的跃迁。因此,西方文明整体是一个阶梯式上升过程,不断前进的过程。但是,西方不断前进的总方向,不过是中国文明的起点。当然中国文明的起点已经包含着中国文明的核心要素,正是这些要素支撑着中国历史永恒性延续。这个永恒性的核心要素就是“道义”、“义理”、“大义”。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