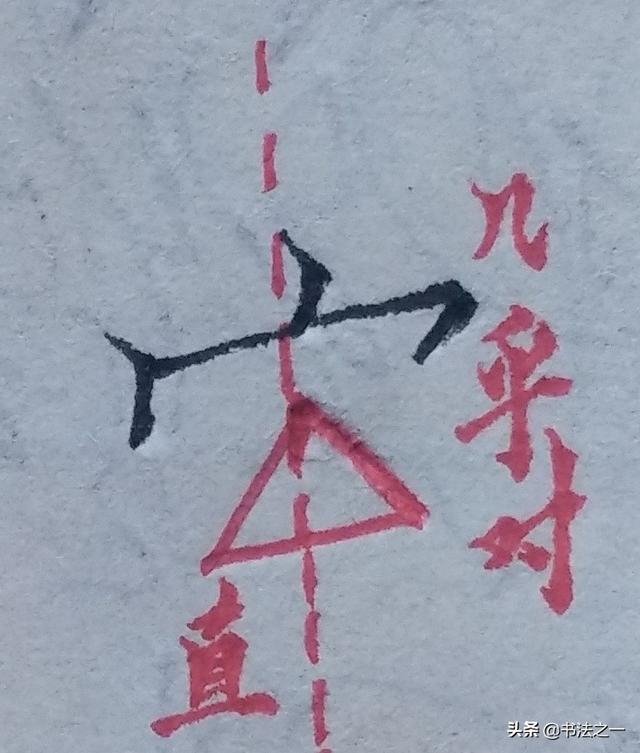送我上青云词句精选(送我上青云中的男性气质)
当姚晨扮演的盛男在电影中两度对男性表达自己的情欲时,导致坐立不安的除了故事中的四毛(李九霄饰)和刘光明(袁弘饰),还有电影院中的观众。而在这其中,男观众或许会像电影中必须面对盛男这一自白的男性一样,既觉得不自在,又会感觉被刺中;而对于女观众而言,这一情节或许同样会引起两种不同的反应,一是感同身受,二是觉得害羞甚至羞耻……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滕丛丛导演的这部《送我上青云》中最让人惊讶又惊喜的部分,惊讶是因为我们似乎很少在国内公映的电影中看到过女性如此直白地对自身欲望的表达和诉求,惊喜则是在一众看似无涉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当下国产电影中,这部电影其实揭露的正是前者中存在的隐形的男性性别意识和角度。
我们似乎很少听说有哪部电影被称作具有强烈的“男性意识”,因为它太过普遍和久远,而直接被当作日常和“正常的”模式存在于电影结构内部。因此只有当出现像《送我上青云》这样的电影后,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些“无性别意识”的电影之中的性别意识。而在《送我上青云》中,有两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很值得讨论,一是关于女性情欲在社会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中的被压抑和遮蔽;二是伴随着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传统男性气质也随之改变。在《送我上青云》中,不同的男性角色所展现的其实是一种新型的男性气质间的角逐与压迫。
一、自我言说:女性的欲望
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反驳了关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性保守的观念。他通过研究当时各种关于法律、医科学和日常生活的资料与文献,发现当时存在着大量围绕着“性”而产生的新话语,从而建构出一系列新的性经验和性观念。但有意思的是,福柯所发现的这些性话语的膨胀最终所产生的直观印象却反而是性保守,而非性解放或自由。这一看似悖论的状况其实始终存在。在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布吕克内的《爱的悖论》中,他便发现了伴随着现代社会中关于爱与性的话语的不断生产,带来的却并非激情与浪漫,反而是对于性的焦虑、不安和恐慌。布吕克内发现,性话语的繁盛导致了性的枯竭。
但在另一个层面,当我们梳理这些繁盛的性话语和性表达时,却发现它们大都产生自男性,并且也大都表达了男性的性观念、欲望与焦灼。在这其中,女性的性欲望表达总是十分有限,且往往遭到压制与遮蔽。而这一状况其实在东西方传统主流男权社会中都如出一辙,即女性的性与欲望始终是被控制甚至抹除的一个在场的不存在者。

对于传统中国而言,女性的性最主要的目的便是为了生育,即为父系家族诞下男性继承人,以保证家族的绵延。除此之外,女性的性便被约束与忽视,很多时候还会遭到来自男权文化和社会的结构性控制。除了用于生育,存在于传统文化中的女性之性还会作为男性所消费、购买和掠夺的商品,因此和“母亲”这一存在于家庭伦理秩序中的角色截然相反的便是妓女。与“母亲”之性不同,妓女之性带有更多的情色和商业色彩,从而把女性之性置于市场中进行交易和流通。
而无论是为了生育还是消费,传统女性对于自身的性都为主流男性所掌控,因此也为其塑造和建构,但即使如此它依旧不会出现在社会公共场域之中,而被严格地控制在特定的空间内。而反观男性之性,它则无处不在,并且渗透着日常生活和实践,在不知不觉中被巩固与再生产。在传统的电影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鲜明。
以好莱坞经典时期的爱情电影为例,它们大都描述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追逐与互动,但其中一个典型的共同点便是它们大都站在男性的立场来书写整个故事。就如英国著名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在其关于电影中男性凝视(gaze)的理论中所指出的,电影中充满了男性的目光,而构建出这一目光的正是主流男权意识形态。电影中的男性始终是展开凝视的主体,而作为被他们目光所笼罩的女性则依旧被安放在客体位置上,从而失去了说话和表达的能力。
自我言说是建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颇为重要的手段,但“开口说话”对于传统文化和社会中的女性而言,其实遭到了普遍的控制和压制。而在这有限的声音中,因为性禁忌的存在,而导致她们根本不可能吐露自我的性欲望。因此在近代中国的女性解放中,性解放始终是一个重要范畴。在丁玲著名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引起争议和讨论的便是作为女性的莎菲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性欲望,而也正是在这一自我言说和袒露中,她从被男性凝视和规训的客体,变成了自我的主人。(可以作为补充比较的还有郁达夫一系列关于性苦闷、压抑和变态的小说,虽然主人公是男性,却依旧因为正是自身的性欲问题而得以进行自我觉醒和赋权。)
在《送我上青云》中,盛男对于自我性欲的关注来源于她得知自己患了卵巢癌,以及在网上看到手术后可能就会失去获得性快感的能力,因此她想在手术前再次体验下性快感。在电影中,盛男单身很久,也没什么性生活,似乎也正属于这几年国内媒体经常讨论的那一群渐渐“无性生活”的年轻人。就如布吕克内所发现的,在现代消费社会和互联网中,性无处不在,各种影视书籍资源以及各类交友软件都使得人们对性更加了解和触手可得,但现状却是许多年轻人渐渐失去了性生活,造成这一状况的除了一些年轻人对其失去了兴趣,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深入,人与人之间的单子状况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最终导致传统的伦理关系渐渐被市场和资本逻辑中的加减乘除所取代,从而导致亲密感的匮乏,由此使得亲密关系难以建立。
生活在现代大都市中的盛男或许同样面临这一状况,如果不是得知自己身患卵巢癌,这样的状况或许依旧还会延续。而盛男自我性欲意识重新觉醒除了因为得知自己患病之外,还与她因为需要赚手术的费用而答应给自己一直鄙视的李总的父亲写自传这一过程中所遭到的种种来自主流男性社会的为难、羞辱、冒犯和打击有关。在电影中,盛男身边除了母亲之外都是男性,并且这些男性又可以根据年龄和阶级进行细分,如四毛、刘光明和盛男年纪与学历大概相仿,而李总及其父亲则在社会阶级和年龄上都与盛男不同。因此当这些元素进入性别结构中时,我们便发现由此织成的网把盛男牢牢地笼罩在其中。
其中以李总这类人最为典型,在电影中温泉房的一幕里,四五个大腹便便、赤裸着上身的男性在温泉里说笑、谈论商业与投资等等,而盛男则站在门外,等着李总出来签合同。(在这里,男性对于身体的展现完全没有因为外面站着盛男而感觉有什么不妥,他们或许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性展示对于他人可能造成的不便。并且如果我们把这一场景中的男性女性角色对调,或许就会立刻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男性对于身体和性的展现完全被日常和正常化。)而当李总对盛男进行一番说教时,我们发现以上的那些元素——年纪、阶级和男性身份——便融为一体,开始对盛男进行规训和压制。这一模式历久弥新,构成了主流男权意识形态中最为核心的手段。
电影中还通过对盛男好友四毛在性生活上的活跃和他对此的津津乐道与炫耀进行对比,进一步展现了女性在性表达上的被局限和控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会听到男性在各种场合中对自己性能力与性表现夸夸其谈,而关于性的笑话和话语更是无处不在。相比之下,女性对此更为保守,而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她们被禁止对此诉说,尤其当它涉及到自身的性欲望时。当盛男对四毛说出自己的性欲望,四毛以朋友身份而拒绝了她;而当盛男对颇有好感的李光明表达了这一意愿时,后者则吓得撒腿就跑。
在S.M.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所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中,作者通过对西方19世纪女作家们的作品分析发现,在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中,总是存在一个“疯女人”,她们公然无视妇道,花枝招展、野心勃勃、作恶多端,最终都为此而遭到灭亡。这一看似疯狂的角色其实正是主流男权社会在对女性进行控制和打压时所创造出的,并且男性意识形态也以此来对那些出格的女性进行规训,从而造成“好女人-疯女人”二元形象,以此来达到统治的稳固。在《送我上青云》中,自白自身性欲的盛男便很可能被当作“疯女人”。而电影开始和结束时都出现的那个精神病,最终反而与盛男之间形成了某种理解和共鸣,因此才会说“我爱你”。在由四毛、刘光明和李总等男性组成的世界中,盛男就像个女性中的异类,只因为她表达了自身的性和性欲望。
在电影中,与盛男开始直白地表达自身性欲形成对比的是她的妈妈。盛男母亲19岁便嫁给了盛男父亲,最终辞了工作成为家庭主妇,但伴随着丈夫出轨盛男的女同学,而对她冷淡,她便开始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不存在的人。为了重新获得注意和得到幸福,妈妈开始更为精心地打扮自己,并且最终和李总父亲产生一股惺惺相惜之情。
盛男母亲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来源于主流性与性别意识形态对于女性自我和性欲表达的控制和遮蔽。人们似乎忘了盛男母亲作为一个女性所有的性欲望,而早早地开始对其去性/别化,从而导致她成为传统帝制社会中“无性”的女性,如《红楼梦》中形容年轻守寡的李纨时所说的“槁木死灰”。
当电影展现盛男母亲这样中年女性的性与性欲望时,我们发现对其的压制不仅仅只来源于传统的性/别结构,同样还来源于作为女儿的盛男。在她与母亲的矛盾中,有一个重要冲突便是她也在潜意识中遗忘了母亲作为一个女性所本该拥有的性权利。这一意识形态源远流长,在传统中国便已经根深蒂固,即通过成年子女来对父母进行约束,尤其在性问题上更为严格,似乎父母一旦进入中老年,他们就彻底没了“性”、欲望与享受性爱的权利。因此,当面对母亲时,盛男其实同样是传统压制她性欲表达的男权性别意识形态的帮手和再生产者。
因此,就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作用的不仅仅只是在场域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权力者,它同样渗透在边缘的被压迫者身上,使其成为自身巩固和再生产的工具。当盛男面对自己的性欲望时,她遭遇了主流性意识形态的压制,从而成为反抗者;但当她面对母亲的性欲望时,她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一颗螺丝钉。而在这张大网中,除了像盛男和其母亲这样的女性遭到规训与压制外,一些非主流的男性同样面临着被侮辱与伤害的境况。
二、“有钱”:新式男性气质
在澳大利亚学者R.W.康奈尔的经典著作《男性气质》中,她指出传统中认为的本质性男性气质其实同样会随着不同社会历史文化的改变而被建构,并且“男性气质”本身就是一个与其他诸多历史范畴有着十分密切联系的存在,如经济、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等等。康奈尔指出,在男性气质这一场域内部同样存在着等级和种种区隔,从而导致相对于外在的压迫女性气质,内在的它同样压迫那些不符合主流男性气质的男性。在《送我上青云》中出现的几个男性角色身上,我们便看到在不同的元素作用下的男性最终出现了鲜明的等级分化,不同的男性气质由此被建构,并且成为束缚、羞辱甚至是压迫这些男性的工具。
就如上文所指出的,在《送我上青云》中,四毛和刘光明在年纪、学历和社会阶级/地位上都处于差不多的位置,而与他们形成对比的则是以李总为代表的中年商人男性。在电影中,四毛对李总卑躬屈膝,希望能得到他提拔和帮助,以让自己学会或是找到赚钱的机会;而作为李总女婿的刘光明更是唯唯诺诺,承受着来自岳父的冷嘲热讽和种种羞辱。电影通过这些情节与故事展现着一个十分典型的处于男性群体内部的等级划分和由此产生的诸多压迫与伤害,而李总这样的中年成功男性商人之所以能够占据这一内部场域中的主流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来源于他“有钱”。
近当代中国的主流男性气质并非一尘不变的。戴锦华教授在其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的著作《隐形书写》中指出,在近代中国男性场域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知识精英在新中国建立后由于遭到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渐渐被去势,最终彻底失去了曾经依靠知识而获得的主流男性气质特权。但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被压制几十年的男性知识精英再次凭借着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话语权,夺回了被压制的男性气质。然而这一结果似乎并未持续很久,即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诸多知识人开始“下海”成为商人,赚得第一桶金,由此而开启了现代中国消费主义大潮。《送我上青云》中李总的成功与上世纪末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有着十分直接的联系。
正是伴随着资本的强势进入,男性气质也在其影响下而随之改变,其中最典型的一个特征便是知识的神圣性遭到瓦解,而“有钱”的商人在其基础上建构出了强势的话语权和选择权,由此开始成为主流男性气质的重要模板。在《送我上青云》中,那些有着高学历的年轻人处处遭遇来自学历不高的李总等人的冷嘲热讽,尤其以对女婿刘光明的嘲弄最典型。在电影中,李总为了娱乐自己的客人而让女婿刘光明给大家表演一下背诵圆周率。这一滑稽的场景背后其实正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现状,即在资本和消费市场笼罩一切之下,知识掉价并且成为人们娱乐的玩具。而代表着知识的刘光明在阶级、资本和主流男性气质的围攻下,只能站在镜子前背诵圆周率。
这一极具羞辱性的节目最后被看不下去的盛男打断。因为盛男自身本身同样是高学历出生,且对自己的知识十分看重,所以能对刘光明遭遇的羞辱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刘光明作为一个男性而遭到男性群体内部的打压和去势,最终沦为小丑,这一经历对盛男而言同样熟悉。因此,就如康奈尔所指出的,占据男性气质主宰地位的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压迫性不仅仅作用于被贬低的女性气质,还会伤害其他不符合这一主流男性气质的其他男性。而一旦遭到来自男性群体内部的排斥和污名,这些男性所遭受的困境甚至可能更为艰难,因为他们始终都还有“男性”这一身份。所以在电影中,刘光明选择自杀。
就如当下诸多文章所指出的,如今人们——尤其是年轻男性——所崇拜的已不再是曾经年轻人所追随的哲学家、小说家或诗人,或是如詹姆斯.迪恩、马龙.白兰度这样的时代明星,而大都变成了成功的商人。这大概是市场逻辑和社会中必然会出现的状况,即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男性气质同样与之紧密连接。在《送我上青云》中,四毛便在想着如何才能赚钱,如何才能成功。电影中反复出现关于金钱的讨论,关于它与生活和人生的联系。而其中一个典型的观念便透露着一种“金钱万能论”的态度,从而彻底为现代社会的资本逻辑所俘获。
就以四毛为例,他曾经是一个颇有报复的记者,但最终还是因为冒犯了权贵而遭到公司开除,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而让他开始相信只有“有钱”才能摆脱作为底层人在生活和社会中遭到的羞辱与不自由,因而开始追求如何才能变得有钱。在这一转向背后所折射出的其实也是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再次出现有关。
当刘光明面对盛男时,他夸夸其谈自身的满腹学识,似乎希望能够从盛男这里获得某种安慰。而令人好奇的是,虽然他有满腹经纶,但却依旧未能看清或是去反抗资本逻辑下人们对于金钱万能的谄媚和坚信,反而是参与其中,忍受羞辱。正是在这里,通过刘光明,导演再次展现了盛男的倔强和勇气。并且有意思的是,当得知盛男是个博士时,刘光明同样颇为惊讶。而盛男也似乎在有意地“降低”自己的学历,从而不必面对社会中对于高学历女性的诸多污名和讽刺。
在性别结构中,即使是遭到主流男性气质伤害的刘光明依旧还是比作为女性的盛男拥有更多的性别权益,因此他才会转向她,滔滔不绝地与她谈天说地。或许是因为他许盛男为知己,或许也只是为了找一个机会炫耀自己的知识罢了。因为无论是面对自己的妻子,还是岳父,他的知识都会变成一个供取笑和娱乐的东西,完全为金钱所衡量与笼罩,就如他的男性气质一样。
三、结语
在《送我上青云》中,导演有意地在破除和揭开传统男性社会里的种种神话和谎言,其中以女性对自我情欲的言说和展现最为典型。在四毛和盛男发生关系后,其中的一个细节便是对传统男性性观念的讽刺,即盛男最后依靠自己获得了性高潮,而非四毛。男性对此十分敏感,正是因为在传统性话语中,男性总是被描述为性行为中的主动者或主体,而女性只能作为承受的客体,因此即使是在此类的性话语书写中,也常常是以男性的作为性描述的中心,而彻底忽略了女性在其中的经验与快感。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女权运动中,出现了许多女性互助小组,而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便是鼓励女性言说关于自己身体、经验、性经历与快感,通过此让女性渐渐意识到和夺回属于自己的主体性。也正因此,我们之后才在许多西方电影中看到关于女性对于自我性欲和经历的讨论,如经典的美剧《欲望都市》,便是围绕着四个不同的女性好友的生活与性,展现现代女性生活中的重要一面。
在雷金庆的专著《男性特质》中,他以“文”“武”来概括传统中国的男性气质,但伴随着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状况,男性气质也随之改变。在《送我上青云》中,唯有有钱且成功的商人李总才能成为男性气质场域中的权力者,不仅压制着女性,也同样束缚着四毛和刘光明这样的男性。在电影中,导演似乎想通过某种形而上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最终处理有限,因为它所展现的其实是一盘棋子们无法掌控的棋局。
本文源自中国青年报客户端。阅读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中国青年报客户端(app.cyol)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