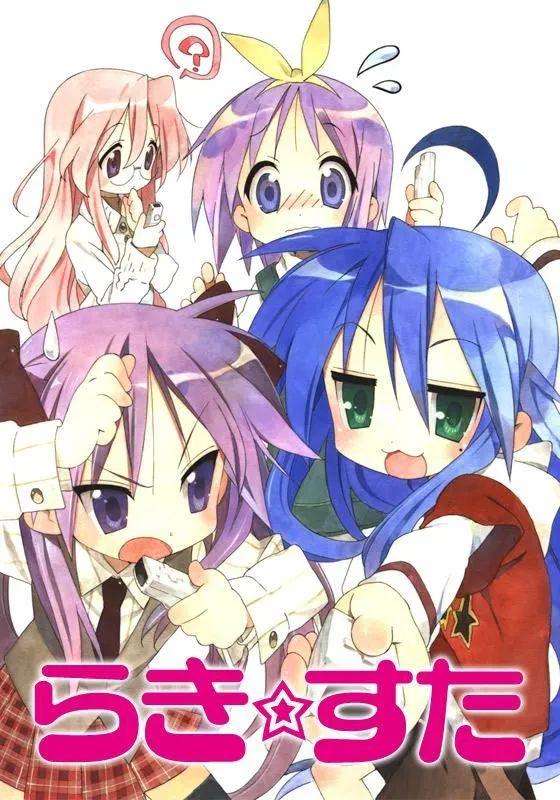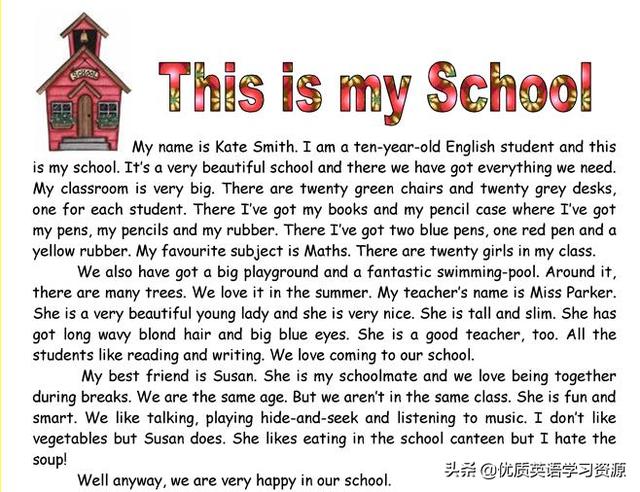知乎宇野常宽(宇野常宽零零年代的想象力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青春存在于何处?——从《blue hearts》到《paranmaum》
|为什么要回顾“学园”
前一章虽然谈论了有关昭和怀旧主义浪潮,但接下来打算思考一下关于零零年代后,作为日本电影新兴代表的另一潮流,“学园青春”热潮的话题。
众所周知,这一热潮的起因,是2001年所公开的矢口史靖导演的《五个扑水的少年》一片的大热。本作起初只有小规模的剧场公开,但在口口相传中人气慢慢得到了扩散,另外也涵盖了如翻拍电视剧版等media mix性质的多媒体展开活动,是起到了零零年代日本电影热潮中点火石般作用的作品,因此不断产生了许多与此类似的企划。以矢口史靖本人的作品《water boys》(2004)为首,《恋上五七五》(2005)等也可以称得上此类的代表例。《扶桑花女孩》(2006)中虽然只有部分体现,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继承了其本质特征。
这些电影作品都具有以下特征:(一)以广义的社团活动为舞台、(二)不重视诸如成绩等社会性的成就达成、(三)相比而言过程中的连带感方与成就感相关联,都共通地使用了这个模式。每年都会有一部遵照这一“矢口模式”来制作的青春电影被公开,今年(2008)也公开了《歌魂》《吹奏吹奏乐乐》这两部作品。文艺评论家诸如小谷野敦等,认为这类相似企划如此频繁出现的现象比较棘手的,并不在少数,但不论《摇摆少女》还是《扶桑花女孩》,都是可以称得上是公开当年的代表大热作品,持续获得着强烈的支持。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如直接来思考这个“矢口模式”能凝聚出如此深厚支持力的原因。
学园,是在这个岛宇宙化的时代中为数不多的共通体验。因此在零零年代左右,与这个“岛宇宙”一同形成的本土化的自恋情结,以及为了将其正当化,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与其他岛宇宙的斗争(决断主义的大逃杀)的舞台,在一时便被设定为了“学园”。学园这一概念具体而言,是一种缩影——在单一结构系统的基础上有着不同价值观的社群之间相互冲撞、是这种决断主义的动员游戏=大逃杀性质的现代社会模型被浓缩总结得出的缩影。
那么《五个扑水的少年》和到那为止的“学园青春故事”有哪里不同呢?这部电影的具体内容,都不太有必要单独介绍。在实际存在的埼玉县立川越高校的游泳部,80年代左右的时期曾经存在一种“纯男子”的花式游泳作为文化祭的表演项目。本作便是从这所高中里真实发生的情节中获得灵感进行创作的电影。身为主角的男子高中生们,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得以将这一独特的企划落地实现,影片故事便是将其过程用喜剧轻松的方式来描写成形的。
到目前为止的重点,直说的话,就是在这之中所描写的“青春的美感”,基本不依赖于与“成功”抑或“社会性意义”之类的“意义”这个特征。在矢口的作品中被重视的往往是过程而非结果。既不是“在全国大会上取得优胜”,也不是“谈一场大恋爱(青春期仅有的特权性质的)”。相反,在上述的这些特殊意义(被社会所保证的“有价值的事”)被削弱剔除之后才反而得以浮现的,团结协作这一行为本身自有的乐趣,以及演技或演奏本身自有的乐趣,才是被强调的表现重点。(融合了昭和怀旧系和矢口模式的《扶桑花女孩》中,被稍微赋予了一半“小镇振兴”意味的社会意义)
那么为何,“意义”一定要从青春当中被剔除掉呢?这就是本章节的主题。这种“青春”主题,尤其是矢口的这种“青春”观,是一个绝不仅仅局限于零零年代日本电影热潮的,具有极广影响范围的问题。
泷本龙彦为什么“家里蹲”了
首先复习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谈论到的内容吧。(译者注:你可真能复读,,)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什么是正确的/有价值的”变得越来越暧昧模糊。在日本国内,由于受到了1995年前后这种社会形象变化的推动,九零年代后半便被一种“反正这世上什么都很难懂,干脆什么都不做算了(家里蹲)”的这种对社会性自我实现缺乏信赖的思想所支配。作为其结果产物出现的,便是被反复论及的90年代后半的以幻冬舍文学为代表的想象力,以及(经历了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后)作为其继承者的泷本龙彦的小说,也就是所谓的“世界系”作品群。
在《五个扑水的男孩》热潮正盛的2002年所发表的,泷本龙彦的《欢迎来到NHK!》,可谓是前文提到的90年代后半特有的厌世观的绝佳样本。主人公青年佐藤,正属于“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就干脆什么都不做了(家里蹲)”所描述的,抱着90年代后半特有厌世观从大学中途退学,窝在家中的青年。他的这种厌世观,被“比自己弱小的”美少女(负有精神创伤的“小岬”)表现出的无条件的需要所填补了。作品中为了让男性受众获得“有切实价值的事”=生存的意义,也是将具有身体障碍或精神创伤的女性在性意义上占有(被少女无条件地需要),具有某种层面上属于雷普幻想(rape fantasy)的构造。因此本作也被人称“被削弱了的肉食恐龙”这类文化系大男子主义者所强烈追捧。
在这种扭曲的(世界系性质的)大男子主义的产生背景中所存在的,是某种具有推卸责任意图的自恋情结。泷本龙彦所描绘的主人公们,因为这世间无法予他们以浪漫而畏惧退缩,因而可以从占有比自己弱小的少女这一行为中得到一种超越性。当然,这种超越性也不过是与在决断主义中被选中的这种本土化自恋情结同质的。从这个(作为前提的)世界系,到(作为其出口)的决断主义,这个回路当中所孕育出的暴力应当如何被消解正是本书的主题,不过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在第七章至第十二章的内容中有所阐述了。
泷本龙彦笔下主人公们所绝望的,是一种“虽然有物但无故事发生”的郊外性空间。不过,这种“郊外的”空间真的是带来绝望的存在吗?在具有“郊外性”的现代社会,获得自由的代价则是必须要靠自己来为自我调配好“趣味”、“活着的意义”、“认同欲望”,也就是浪漫和故事都需由个体自给自足。因为无论国家还是历史还是社会,都不会给予这些。但这就意味着世间是不幸的吗?我不这么认为。确实,世界也许变得“冰冷”了,但与此相对也变得“自由”了。对于像青年佐藤那样,将“被赋予的浪漫贯彻执行”的老式人类而言,这可能确实是不好生存的世道。但相反,对于“一切由自我建立”的新式人类而言则是极好生存的世道。在这个层面上,世界虽然在变化,但也可以判断为整体上并没有倾向优化或是劣化(个人认为是有所优化的)。
于是所谓现代,其实正如第七章所讨论的《木更津猫眼》这类优秀的郊外小说所描绘的一般,是只要自己主动伸出手,便能在日常中前所未有地自由地捕捉到故事的世代。浪漫,反而正是存在于日常之中——宫藤官九郎、木皿泉、吉永史——即使那些迟钝而视野狭窄的自诩的“评论家”们并没有将其提出,但零零年代的丰富想象力已经在此得以彰显了。
矢口史靖的作品为何会在青春电影中获得如此全新的评价地位呢?以及,泷本龙彦作品中的主人公为何选择家里蹲,并梦想着由如此扭曲的大男子主义凝结而成的雷普幻想(rape fantasy)呢?答案已经很明确了。矢口的作品与泷本的作品之间是有一道分水岭清晰隔绝开的,他所秉持的态度是从这个郊外的空间里展开的日常生活“之中”来提取浪漫,是基于这个前提而成立的。所以,矢口的“青春”像不会追求特定的“意义”。仅仅相互连结,然后享受其中就可以了——如此简单直接的赞颂便能够使世界变得多姿多彩。
不过,关于这一点的讨论不会就止步于此。比如倘若是十七岁的我读到这儿肯定会觉得愤慨吧。“这在说啥呀,仅靠这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连结之类的东西就能获得自我满足?”“自己不可能是那种能被日常生活之流就给填满自洽了的人。”肯定会这么进行自我说服,这种正值年轻才有的那股误解使自尊心不断膨胀,进而能够获得一种满足感。然而对于还有八个月就要结束自己二十多岁这个年龄阶段的我来说,非常可惜,即使觉得这种少年意气的气势也不乏可爱之处想要好好珍惜,但也做不到对这种心态完全释然并予以肯定包容。因此在这里,我想反过来问问十七岁的自己,你所追求的事物,真的只存在于日常的外侧吗?浪漫的所在之处,实际是哪呢?
凉宫春日的忧郁——“世界系”的临界点
谷川流的轻小说系列作品《凉宫春日的忧郁》在2003年发表了系列的第一卷,成为了足以代表零零年代轻小说热潮的大热作品。紧接着2006年,其电视动画版也直接爆红,企划制作了续集作品。
同时,这部作品对于思考“这种浪漫的所在之处”以及围绕青春主题的各种问题而言,恐怕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作品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本作毋庸置疑是一部有着在“旧式‘青春’观念”和“新式‘青春’观念”之间架起了衔接桥梁的内容的作品。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必须对本作这套复杂的,甚至有点过度防御性质的设定进行解说。
故事的舞台设定在一个普通科高中。在那里,故事的讲述者男高中生阿虚,和一名孤独的少女春日相遇了。春日是痴迷于超自然现象的“不可思议酱”。是在高中入学的当天,面对着第一次见面的同班同学,做出了“我对普通人类没有兴趣。你们当中如果有宇宙人,未来人,异世界人或者超能力者的话,就来找我吧。以上。”这番宣言的少女。此后,对完全交不到朋友的春日产生了兴趣,并唯一和她搭话的阿虚被春日报以了好感(!),被她生拉硬拽着加入了她创立的社团“SOS团(为了让世界热闹起来的凉宫春日的团)”,被指名成了成员。之后,随着春日用同样的伎俩捕获到了其他几名团员,阿虚等人从召唤宇宙人开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超自然活动。当然,实际上春日并没有成功遇到什么宇宙人和未来人,SOS团的活动本质上,变成了草地棒球、独立短片拍摄,在离岛上夏季合宿等等,这种跟随处可见的大学活动社团所办的项目一样的东西了。
不过,在这里作者又进行了一段巧妙的设计。除了阿虚以外,其他成员都是在佯装成一名普通高中生,实际上分别都是宇宙人、未来人和超能力者,这一点在故事的开篇就已明确。
而春日本人更甚,虽然她本人没有任何自觉,但其实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改变和创造世界,是这种近乎于“神”的超越性能力的持有者。SOS团内的成员都是遵照着各自所属组织的指示来监视春日的。而这一切的当事人本尊春日,无论是对于自己已经在跟宇宙人们接触了,还是对于自己持有的这个能力,她都毫无意识,还在单纯地讴歌着青春。
本作可以说是狭义世界系(雷普幻想系)作品的一种最终形态。为了在不伤及他们膨胀的自尊心的前提下,满足这些被削弱了的肉食恐龙们的大男子主义意识=“对比自己弱小的少女所持有的占有欲”,在此,提供了一种极其周到的构造装置。这里来解说一下。本作最大的要点在于,有着与“神明”近乎等同力量的女主角春日,将世界的大部分都视为“无聊”的东西并抛弃,但依然只对消费者视角的男性角色阿虚投以无条件的需要他,并且作品也把这描绘成了一种少女心的无意识的单纯恋爱感情。以此,春日对阿虚抱有的恋爱感情被当成一种超越性来被消费。不如说,这种超越性的本质与前文所述的大男子主义无二。但这种暴力的构造被极其周到缜密地隐藏起来了。比如说,在《欢迎来到NHK!》或《AIR》中,残障或患有精神外伤的女孩”=“包裹着直接‘脆弱’符号的少女”,被替换成了春日这种“表面逞强其实非常孤独寂寞的不可思议酱”, 进行了一层表面上的遮蔽(但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另外本作中,乍一看是采取了“不可思议酱”春日将故事讲述者(受众视角的角色容器)阿虚玩弄得团团转的这种构造,但越仔细想就会发现,在系列的第四卷《凉宫春日的消失》中讲述者阿虚本身,正如他自己坦白的那样,“是这个不可思议酱必要的心灵寄托”,以此可以看出这种大男子主义的占有欲没有得到满足就无法生存下去的反而正是阿虚(读者)。也就是说,本作是采取了“占有在世界系世界观下生存的少女的世界系(元世界系)”的形式,将《欢迎来到NHK!》和《AIR》中表现露骨的大男子主义用一种迂回路线提供给了消费者。在岛宇宙的时代,本土化的自恋情结在经历了安全疼痛的自我反省(游戏)后,得到了一种被再次强化了的性质,这一点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谈到,本作将这层意义通过数层的迂回实现了全面强化,可谓是世界系的临界点。
作为“脱世界系”的春日
不过,《凉宫春日的忧郁》并不是一部就到此为止了的作品。作为“世界系的临界点(元世界系)”的春日解读,恐怕只能传递出其半分的魅力。那么余下的半分是什么呢?
从结论上来说,本作作为世界系的临界点,满足了持有九十年代后半厌世观的消费者们的大男子主义占有欲,而作为这么一种补足存在的同时,不,正是因此才得以中和了这种强者怨愤(ルサンチマン,ressentiment),也有着能够接续到矢口史靖类的赞颂等身大自我实现的想象力。没错,本作剩下的半分魅力,正是其作为“脱世界系”作品的可能性。
虽然有点突然,不过有一个存疑是根本性的,春日所寻求的,真的是宇宙人、未来人、超能力者这类“非日常”吗?答案当然是“否”。在本作中满足了春日的,同时模拟地充实了消费者们愿望的事物,其实反而正是与社团伙伴们的草地棒球、夏季合宿等烂大街了的青春,矢口史靖类的作为“日常中的浪漫”的“青春”像。
引用一下伊索寓言里《酸葡萄》的故事应该就很好懂了。憧憬着生长在高处的葡萄的狐狸,在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不足以使自己得到葡萄果实的瞬间,便开始主张“那个葡萄一定是酸的”“所以自己其实也没那么想要”。这则寓言基本完美表达出了《凉宫春日的忧郁》的本质。
春日想寻求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存在于日常中的浪漫。既有在草地棒球或夏季合宿中挥洒汗水的时刻,也有对同级生充满少女心的关心好奇。即便如此,春日(可能是由于膨胀的自尊心)却对此并不承认,自己所寻求的东西并不存在于日常中,宛如像在说服自己一般坚持主张着这一点。而这种《酸葡萄》一样的构造,也不难想象,是能唤起很多消费者的共鸣的。即便渴求着日常当中的浪漫,但却不能坦率地承认这种渴望——这是社交技能低下的十几、二十几岁的世代很容易陷入的一种别扭心态。本作要说起来的话,可以算是为了那些不能率直地说出、想获得像《蜂蜜与四叶草》中一样等身大的学园青春的人们服务了的、充当了像自行车辅助轮般作用的温和作品。如果不进行前文所述的那种迂回路线,便无法坦率地接受自己对“与社团伙伴一起打草地棒球”“在学园祭的舞台上热唱”这类活动心怀憧憬的女主角,以及被乖僻和劣等感等心理所困而同样无法坦率的消费者们——本作为他们编织出了一层又一层的借口,甚至可以算是有点防御过剩的性质了。
实际问题层面上,提出“日常当中并不存在浪漫”这种主张的人们,根本算不上什么浪漫主义者或者别的云云。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浪漫主义者这个概念也宛如推卸责任一般,变得跟自恋主义者同义了呢?
凉宫春日所抱有的这种“忧郁”,其真正面目到底是什么呢?那并不是因为,这个不存在未来人、宇宙人和超能力者(也就是浪漫)的“无聊的世间(日常)”而产生的忧郁。而是在面对未来人、宇宙人和超能力者都存在着的(浪漫切实存在)这个充实的日常时,被膨胀的自我意识和自尊心所阻碍、无法察觉到这一切的春日自身是如此的笨拙,因此而引发的“忧郁”。无聊的,不是这个日常世界,而是使这一切既存的充实都无法被察觉并调动起来的,春日自己的这份膨胀的自尊心。不过在故事当中,春日已经开始慢慢意识到了。不管是草地棒球还是夏季合宿还是文化祭的舞台,都感受到了对于自己而言这些是跟与未来人、宇宙人、超能力者相遇有着同样的,不,是在此之上的美好体验。
举个例子,系列中第六卷的短篇集中所收录的,同时在动画版第十二话中放映了的《LIVE A LIVE》中,偶然登上了学园祭舞台演唱的春日,对意外收获的好评产生了印象深刻的困惑。在此之前,对于一直对学园祭所象征着的等身大日常中的浪漫抱持否定态度,豪言(强行说服自己)能够满足自己的事物在日常中是不存在的春日,这份充实感,起到了促使她自我觉察到自己的这种“酸葡萄”式憧憬的作用。
当然,同系列作品目前还在连载中,本作中是否会体现对这种“酸葡萄”构造的自觉性,最终是否会沿着“去发觉在日常中的浪漫”这条逻辑线行进也还尚不明确。不过在这里我想主张的一点是——这种照顾到消费者心情而周全设计出的一连串元世界系的,“酸葡萄”性质的过度防御,从结果上而言,是以一种反证的方式证实勾勒出了春日的(同时也是预设消费者们的)内在真实欲求,即这种日常中的浪漫是切实存在的。
从《春日》的强者怨愤到《幸运星》的排除型社会
如此考虑的话,《凉宫春日的忧郁》TV动画版的制作班底接下来制作的,2007年同样一举大热的《幸运星》所体现的消费倾向也显得非常有趣了。以美水镜的同名四格漫画原作为基础的本作,是吸取了第十一章所介绍的《阿滋漫画大王》风格走向的一部作品。用完全发散的各种疯癫小故事(neta),描绘了女子高中生们琐碎日常中傻乎乎的各种小互动(在网络上被归为所谓“空气系”的作品群所属)。
这类“空气系”的作品,与《春日》相比并没有使用前文所述的那种以强者怨愤为牵引的这种过度防御的动员。作为其替代,唯一被有意设计的,是为了迎合作品对象的消费者的性癖而被量身定制出的“萌系角色”这种狭隘性(狭さ)存在。如第二章所述,这是基于角色这一回路,数据库消费这种形态而诞生出的排除型社群的“狭隘性”。除了用以唤起消费者占有欲而被设计出来的“萌系角色”之外,其余都被当作背景那样来描写的狭隘性(暴力),在两作中实现方式不同:在《春日》中,是基于在故事层面上描绘的强者怨愤而设计出的女性歧视式回路,依据这个回路来确保全能感;而在《幸运星》中,则通过表现层面上的最适化\优化、来展示这种设计(译者注:全能感的确保 = 暴力;想想幸运星主要人物没有男性这个设定)。
但是,这同时意味着《幸运星》相对而言并不需要像《凉宫春日》那样的“酸葡萄”式的借口\理由。如果是通过在学院祭华丽的舞台上做出“切”这样酸葡萄的反应、来确保消费者的共感——若称其为“春日”式的,那坦率地表达憧憬并作为更直接的代偿行为而被消费,就是《幸运星》了。比喻而言,从世界系到空气系的流向,表明御宅族文化开始一点点地开始汲取矢口史靖式的“青春”观。[1]
[1]这里其实孕育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上一章所说的御宅族(オタク系)文化的成熟回避态度和“战后”这一政治上建立起来的空间之关系问题。大冢英志等论者,认为要保持御宅族文化的强度就形同成熟回避式的强者怨愤,他们多以旧世代为中心。比如说大冢的立场是,曾经被揶揄为“十二岁的少年”的、拥有战后日本及其宪法九条这般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隐藏着的“天真”的战后民主主义式日本,通过接受这种伪善(硬要停留在“十二岁的少年”)而能够生成一种伦理,并且可以说,对于御宅族(おたく)文化而言也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说,大冢所说的“御宅族(おたく)”文化的强度,是通过硬要“不去成熟”、“停留在十二岁的少年”而产生的强度。然而,在冷战结束经过了十五年以上的现在,这个回路真的还在发挥机能吗?例如,在零年代更加显著地表现出来的,从故事中独立出来消费角色的回路(如东浩纪、伊藤刚指出的)中,成熟忌讳式的强者怨愤是否起了作用呢?在那里起作用的,不如说是更单纯的大男子式的所有欲与其最适化吧。
比起其作品内容,《幸运星》的特征更体现在它的消费形态上。在2007年开始决定性地普及开的“niconico动画”等视频分享网站上,作为由粉丝们之手(二次)创作出的动画短片的素材,同人创作角色开始普及,成为了其作品人气的源泉。《幸运星》无论在作品层面还是消费层面上,都是与那种(以成熟回避的强者仇恨作为后盾的)故事方向迥异的“不相合”的作品。
只不过,目前看来“空气系”的作品群所描绘的世界,只是在男性受众所谓“占有”欲能够被保障的范围内所赞颂的日常性。正如第二章所论述的,以对特定角色的承认为维系条件的空间,是一种在不会出现“误配”的再归式共同性中,能够让本土化的自恋情结得以确保的一种空间,不过是一种能够高效摄取“萌要素”供给的箱庭罢了。
《幸运星》在开辟了去故事\叙事化的可能性的同时,在被(决断主义性地)完全隔离的封闭箱庭中,是以“完成”这种可以安心消费雷普幻想(rape fantasy)的这么一个空间为目标的。这一点我想需要在此好好标出一下。对于决断主义的动员游戏=大逃杀的这种模式,在将每个单独的岛宇宙从元视角出发动员了起来的强者(比如夜神或者鲁鲁修)的角度看来,是表现为一种动员游戏的;但在那些被他们所动员的弱者(角色信徒、“新历史教科书创作会”或者“2ch那样的neet论坛”)的层面来看的话,则是作为一种基于地域主义性而稳定的本土自恋情结的乐园、这么一种存在而出现的。
以突破这种决断主义所孕育出的“不存在误配的再归式共同性”的闭塞(暴力)为志向的作品,正是从第七章至第九章为止都有所介绍的宫藤官九郎和木皿泉,也正是吉永史所挑战的内容,在此也想重新强调一下。[2]
[2]同样在零零年代出道的推理作家米澤穂信与辻村深月,以各自的方法克服了“春日”式的强者怨愤 = 对于日常之中的浪漫的“酸葡萄”式过敏反应。
米澤穂信是一个对于理、特别是侦探小说这一类型\题材的结构极为有意识的作家。侦探主人公——拥有着执行“解决杀人事件”这一“确实地有价值的事情”之权利 = 特权性地掌握着真正的“物语”——依据向此种侦探主人公的同一化而供给自恋的传统的侦探小说之回路,原本与在后现代状况下存在的叙事回归有着非常高的亲和性。
米泽穗信的小说,是在对于这些侦探小说的结构极具自觉性与批判性的理解之下写就的。米泽作品中的侦探们挑战的,既不是迷宫式的杀人事件,也不是震撼世间的猎奇杀人事件。那通常是,日常生活中丢失了东西、被盗事件之类的“日常之谜”。例如,在“春季限定草莓蛋挞事件”(2004年)开始的“小市民系列”中,小鸠君和小山内这个少年和少女的组合,面对的是在学园生活中遭遇的不值一提的小事件 = 日常之谜。这个“小市民组合”,既是优秀的侦探式知性(才智)的拥有者,同时又拒绝了通过行使自己的能力、过一种引人注目的 = 戏剧性的生活,为了不引人注目而对自身规定要谨慎地过“小市民”生活。但是,面对依据自身的侦探才智而去获取故事\叙事 = 依据无自觉的决断主义产生的故事\叙事诱惑,小鸠不时被诱惑所败、行使了他的能力,而他的这种软弱也驱动着故事前进。
这讲起来就像《AIR》《GUNSLINGER GIRL》等世界系雷普幻想式结构的变奏。小鸠对于侦探式超越的欲望,想来是如同《AIR》里大男子主义 = 对于病弱少女的所有欲那样的东西。正如《AIR》里的大男子主义那样,在作品里,小鸠的欲望经过“自我反省” = “在自觉了侦探式超越性的欺骗性(欺瞞)基础上,仍要……”这一回路的输出而得到了再强化。小鸠的这个欲望,在作为续篇的《夏季限定热带水果圣代事件》(2006)里,被作为伙伴(相棒)的、唤起读者“所有”欲的美少女角色 = 小山内所利用,小鸠对于超越的欲望,在“表面上”被小山内所挫败了。当然,小山内这样超过了小鸠的超越式的知性设定,再强化了小鸠原有的“在自觉了侦探式超越性的欺骗性(欺瞞)基础上,仍要……”这一回路。小山内这个上位的存在,既促进着小鸠进行“安全地疼痛”的自我反省,也因此反而保全了其的自恋主义。小山内是被小鸠 = 消费者“所有”的美少女角色,同时也是“安全地”叱责其自恋主义的“母亲”。不,更正确的说法是,小山内既然是作为美少女角色,那么她的无法变成“拒绝”的“叱责”,就不能越出母亲式的“安全的叱责”领域。(同样的回路,在《算计(インシテミル)》等其他很多的米泽作品里也能指出来)
米泽正确地把握了这件事:在现代,最自由、最有魅力的意义供给回路就是从日常之中汲取酝酿故事\叙事的回路——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然而其追究\追述方法,却限于通过自我反省而再强化了的质朴的叙事\故事回归(参考第十三章)之变奏。小鸠,要说的话就是“再稍微努力了一点的春日”。
另外,辻村深月还写有《冰冻鲸鱼》(2005)、《スロウハイツの神様》(2007)、《寻找名字的放学后(名前探しの放課後)》(2007)等,这些作品描写了拥有世界系决断主义式的厌世观的少女、通过获得作为“容身之地(居留所)”的共同体与人际关系而成长的过程,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在拥有着强力的父性的男性之庇护下得以成立着的共同体。在这些作品里,父亲式的存在为了少女的成熟而设置了(新教养主义式的)箱庭(诡计\戏法),并在结局中将其真相呈现给读者——这样看着相当精炼\推敲的构成,但也可以暴论说,那是通过父女相奸式的结构、尝试将少女幸福的自恋主义进行软着陆的态度(少女の幸福なナルシシズムの軟着陸を試みる態度)。可以说这相当草率\粗糙,但也是对于现代中的“成熟”之成立条件、所迫近了的果敢而危险的挑战。
从“blue hearts”到“paranmaum”
矢口史靖以及以“空气系”为代表的零零年代的想象力所描绘的“学园”和“青春”,是作为从他人(社会、历史)所赋予的浪漫,转变为自己主动去抓取存在于日常中的浪漫,这两者之间所发生的变化的特征出现的。同时,这股流向也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去·故事\叙事化的趋势,到现在也可谓仍在进行之中。
那么,作为这一连串趋势的象征作品,我最后想举出的,是来自山下敦弘导演的影院电影《linda linda linda》(2005)。
《linda linda linda》可以说是基于一种对先前迅速席卷了日本电影界的矢口史靖类作品的批评性视角而构成的电影。内容也不必过多介绍。在某个高中的学园祭舞台上,四名女学生出于偶然突然结成了一个blue hearts的翻唱乐队(由于主唱是韩国留学生,于是便命名为了韩语中表示“蓝心”之意的“paranmaum”)(译者注:The Blue Hearts是一支现实存在的日本朋克乐队。成立于1985年,1987年以单曲Linda Linda出道。1995年解散),本作平铺直叙地描绘了她们在此间的练习过程,基本不存在故事结构(story)。没错,在这里,连矢口史靖出于强烈职业服务精神而想要在作品中大量注入的戏剧性设计(与周围大人们的对立、组织上的困难、资金困难等)都完全不存在。paranmaum所面对的困难全都是在日常范畴内就能囊括下的极其常见的问题,没有什么能在此单独明确列出的矛盾。
不过,如果要说本作是一部缺乏起伏的冗长影片,也完全是错误的。作品中描绘的各种琐碎交流,都是只要曾在学校这个场所待过、就都亲眼目击过的,正是因为毫无特别可言,才显得独具魅力。没错,本作是将矢口史靖所指的方向性,更加全盘彻底地进行了升华的作品。如果浪漫真的就存在于日常中的话,那其实应该连矢口类作品中戏剧性的“故事”都是不需要的——本片画面中的角角落落都彰显着这样的确信。
比如说,有这么一场戏。paranmaum成员所属的轻音乐部的顾问老师,想对学生们说点鼓励的话。老师正想要开口讲述,自己曾是学生的时候是怀着什么心情的,以及现在身为老师看着她们的身影有什么感想的时候,犹犹豫豫之间,就被学生“老师,我能先走了吗”的话语直接打断了。是的,这种多余的(矢口类的)说教(故事)都是不需要的,青春只要存在在这里就已经很美丽了——这正是传递出了制作者们这种态度的一个名场面。
而最能够代表本作“青春”观的内容,则是对blue hearts的音乐所持有的立场了。表达了对某种泡沫(化了的文化)的批判,以强者怨愤为原动力高歌着“为了所有的渣滓们”的乐队blue hearts,即使这种泡沫批判的主题已经随着时代变迁过时了,但其所代表的某种反正统文化幻想的思想寄托——虽然是“不愿被主流驯服的自己”“没能力能做的很好的自己”,但也正因如此自己才能实现真正纯粹宝贵的事物,这种文脉直到现在都一直被人们所青睐。
不过,本作中出现的blue hearts,被彻底剥夺掉了这种反正统文化性质的“意义”。
paranmaum的四人选择演奏blue hearts的曲目,并不是因为怀抱着“我们只有不被世间潮流裹挟,方能窥见真实”的这种反歧视的自恋情结。假如确实如此的话,裴斗娜所扮演的韩国留学生主唱宋,就应该被安排上宣泄在异国他乡居住感受到的疏离感的这么一段情节才对,其他成员也应该被安排上各自怀有的疏离感或是内心矛盾来作为歌唱的“理由”。然而,这部电影却是在将这一切都排除在外的前提下成立的。Blue hearts只是作为几乎已经没有“意义”附加的一种“老歌”,出于“单纯的,是让人觉得爽的东西”这种理由被唱了出来。
回顾一下九十年代摇滚乐的发展就也很好理解了,发达国家中反正统文化的立场越来越难以立足。简单来说,随着后现代状况的不断推进,需要反对的对象=“坚固的世间普遍价值”也逐渐变得难以成立,主流\正统缺席的时代到来了。如此的话,便产生出了小众的岛宇宙们乱立而存的一种局面(决断主义的大逃杀),即使想要反抗也失去了能够反抗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这十几年间,“blue hearts”风格的“我们只有不被世间潮流裹挟,方能窥见真实”的这种自恋情结,其所设定的假想敌“世间”的形态已经由“一个宏大的世间”转变为了“多个小的世间乱立”,其结果自然是使得这种假想敌难以成立了。如今,即便单手拨着琴弦豪言“别随波逐流服从于世间啊我们!”,也只会被视作“这只不过是你们的世间跟别的世间不太一样而已吧...”。
Blue hearts是乐队浪潮当中先驱级的存在,他们所出现的泡沫时期,是“宏大叙事已经消亡,拟似的宏大叙事”在勉强发挥机能的时代(由此获得了一种“反抗消费社会犬儒主义”的立场)。然而正如再三提到的,现在已经是“即使想撬开一个通风孔,墙壁本身也已经不复存在了”的时代。其结果,就是在这部电影中所歌唱的,是只表达了单纯赞颂[祝福]的(被除味了的)blue hearts(译者注:没有糖的零度可乐是吧,,)。这种“从blue hearts走向paranmaum”的转变,可以说恰恰直接地表现出了零零年代想象力流变的一大方面。同时完全不采用反正统文化的这套逻辑回路 = 连《幸运星》中可见的决断主义的本土自恋情结也不采用,这种彻底的态度是具有压倒性的激进意味的。
讽刺的是,前文提到春日在文化祭的舞台上歌唱,意识到了在等身大的日常中所存在的浪漫,包裹着困惑不解的《凉宫春日的忧郁》TV动画版第十二话,是带着对这部《linda linda linda》的致敬所制作的。也许制作人员们并不是有意为之,但在这个片段中的春日所展现出的,正像是伫立在“从blue hearts走向paranmaum”这条长路的途中的状态。
在同一话的舞台上,春日所歌唱的“即便在这样的世界里,也能唯独在对你的爱当中找到超越性的力量并以此活下去”这番内容(大致含义),要说起来的话其实是“世界系歌曲”。然而,当他人(社会、历史)不再给予个体浪漫,转而接受了自己亲手所抓住的世界的这个瞬间,她所歌唱的内容也便不可能再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自恋情结了。那或许正是,“单纯地赞颂日常”的除味后的blue hearts = paranmaum形态的《linda linda linda》了。
原作者:宇野常宽
翻译:阿栖 柴来人
校对:春琦美空
仅供学习目的,译文基于CC BY-NC-SA 4.0发布欢迎规范转载
屋顶日语角提供校对协作帮助,欢迎加入屋顶日语角进行志愿翻译!
欢迎有志者私信加入或投稿(翻译或原创):lab_on_roof@163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