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性侵案例很可能是公开报道的(现行法律能否把造谣者送进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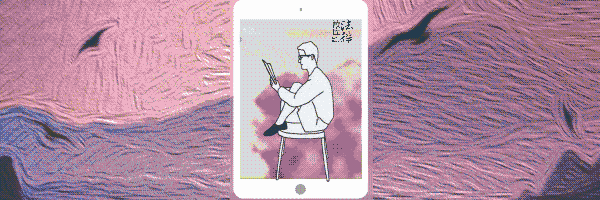
作者:魏思年 来源公号:东窗律疏
chapter / 01
6月26日,微博名为“鹅组兔区爆料”的网友发文称 ,在贵州省毕节、凯里等地,疑似有福利院幼童遭到性侵。针对传言,黔东南网警官方微博及时回应,相关部门随后对当地4000多个儿童机构进行了紧急排查。
这件事情在热搜榜上整整霸榜两天,吸引无数人关注。由于事件带入性极强,愤怒情绪汹涌而来,大家一致希望彻查,以切实保护儿童权益。也有人希望能恢复远古酷刑,车裂、炮烙、凌迟、剥皮,仍是不解恨。
贵州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紧张地忙了整天,结果查明,照片均为网民赵某从网上收集,孤儿院儿童被性侵信息系编造。
原来,今年1月至5月,赵某把自己从QQ群中收集来的图片陆续通过微博私信发给网友,“为了增加可信度,于是捏造自己干过这些事,到过贵州”。按照赵某的说法,这么做仅仅为了在网上“刷存在感和猎奇”。6月27日,赵某被刑拘。
网友们愤怒的矛头迅速调转过来,指向那个造谣生事的赵某。贵州公安也发文,表示会依法追究责任。网民浪费了情绪,政府机关浪费了警力,这笔账当然要算清楚了,不找你赵某找谁?大家在这一点上出奇一致。
对付可恶的传谣份子,需要运用法律武器。那就必须一本正经地分析,在这起事件中谁作出了什么行为、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相应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当然,如果不严格依照法律,就不如直接把赵某拉出来用口水淹死,也好让案牍如山的公检法早些下班。

chapter / 02
谣言作为虚假信息,一经广泛传播可能会影响社会秩序甚至公共安全。对于传谣者需要承担责任的说法,法律依据在哪呢?
以前,对于传谣责任的规定主要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按照这一规定,传谣者的法律责任最多也就是拘留十天、罚款五百,对于一些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行为来说,显然有些不对称。
法律的出台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2008年的“蛆橘事件”、2009年的新疆乌鲁木齐“7·5”事 件、2010年山西 “地震谣言”、2011年日本震后的“抢盐风波”、2012 年的“军车进京”事件,以及2013年“秦火火”“立二拆四”事件,都让人们感受到网络谣言的威胁性,使得《治安管理处罚法》有点难以招架。这就迎来了遏制网络谣言的“元年”——2013年。
2013年,公安部启动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顺应时代潮流,所谓“救火式应对”,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部司法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
“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寻衅滋事罪,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触犯这条罪名的人很多,最有名的可能是上文提到的“秦火火”。该案中,“秦火火”在微博上编造铁道部向外籍遇难旅客支付3000万欧元赔偿金的谣言,最终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但在实践中,只有严重的网络谣言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大部分造谣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只能依《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行政处罚。虽然有了“净网行动”与司法解释,“某中央领导在青岛做空A股”、“天津港爆炸死亡1300多人”、“有毒气体正向北京扩散”等谣言仍然肆意蔓延。
终于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了。这次修正,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第291条之一中增加一款,成为独立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该款规定:
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现在,所有武器“配齐”了。

chapter / 03
表面上看,对付赵某,咱们的武器是足够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够他喝一壶的,现在既然被刑拘了,要么是涉嫌寻衅滋事(最高刑期5年),要么就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最高刑期7年),这小子得脱层皮。
但是仔细分析下来,问题好像不是这么简单。既然已经被刑拘,行政处罚就不提了,重点看这两个罪名。
如果认为赵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在客观上必须满足“编造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和“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两个要件。
首先,这次的谣言非常特殊,赵某是为了满足自己“猎奇”或畸形欲望,在与网友私聊中编造了虚假信息,而不是通过发微博这种向不特定多数人呈现虚假信息的方式。散布的含义是广泛传播,紧接着造成严重社会影响,在条文的语义上是有所承接的。赵某每次都单独找一个网友聊天,虽然可能都发送了虚假信息,但是否能说得上互联网环境中的“散布”?
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如果扩大解释“散布”的含义,认为只需要向特定的某个人传播了虚假信息,就构成“散布”行为,这必然会导致人人自危。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无法愉快聊天,否则,本来是吹牛的一句话被截图发微博,造成影响,可能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而如果认为“散布”的对象包括特定人,条文用词完全可以是“发送”、“传递”、“告知”等等。
其次,赵某编造、发送虚假信息的行为本身尚不足以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而是经过半信半疑的好心网友曝光后,虚假信息迅速扩大影响力,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也让贵州的工作人员白忙活一场。
赵某的行为作出时没有造成社会影响,他没有想到的是,跟他聊天的网友社会责任感很强,寻求渠道进行曝光,结果促使赵某编造的虚假信息产生社会影响。
曝光者对信息真实度是是保守克制的,不能承担责任,但是要说赵某向特定的一些对象寻求存在感的行为本身构成寻衅滋事罪,恐怕有些难以服人。毕竟,社会影响不是赵某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没有足以证明间接故意的证据。

chapter / 04
接下来咱们看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要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需同时满足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两个条件。单纯的“编造”行为不能构成犯罪,否则将介入公民的思想领域,导致刑罚过于提前。
寻衅滋事罪在规制网络谣言时,用语是“散布”,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用词是“传播”。从文义上看,“播”的本意是“撒种”,有广泛之意。因此,有学者认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犯罪主体也必须通过信息网络或媒体向不特定对象传播。如果向特定对象发送虚假信息也能构成本罪,仍会造成刑法侵入私人空间之虞。
在司法实践中,大都认为虚假信息的传播对象是不特定的。例如:
❶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8刑终186号案件中,蒋某某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他的犯罪行为是:把虚假信息发送到多个微信群中。
❷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2017)吉0211刑初196号案件中,高某某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其犯罪行为是:使用“快手”平台,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向观看直播的观众编造并传播吉林市洪水灾害死亡一百余人、政府故意屏蔽造成丰满区旺起镇通信中断、救灾物资未全部发放到灾民手中的虚假灾情信息。
❸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6刑终330号案件中,郭某、何某等人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到一年不等,他们的犯罪行为是:在微博上发布“何某某被强奸”的微博,在网上被转发12374次,评论3650条。又发布“我侄女被西华警方单独询问两个多小时,不让我们家属在跟前!恐吓威胁我侄女不能讲真相,做假笔录”的微博,被转发20310次,评论7241条。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穷举法的论证方式是存在漏洞的:我们无法举出所有生效判决,即使所有判决都一致认为“传播”一词意味着对象不特定,也不能必然得出”传播“的立法规制对象不包括特定对象的结论。
一个典型的反例是,对于恐怖信息,检例第9号李泽强案认为向特定对象传播也可以构成犯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即使在法条中同样没有明示。
当然,在“贵州性侵儿童”这起谣言中,赵某编造的虚假信息显然不属于恐怖信息。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令人觉得恶心、担心就属于“恐怖信息”,这里的“恐怖”,必须是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慑等对生命安全产生直接、即时威胁的信息。
这样一来,要用这条罪名将赵某送进去,必须将传播做扩大解释,认为包括向特定对象发送虚假信息。

chapter / 05
无论是寻衅滋事罪,还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严格解释起来,我认为都很难将赵某入罪。虚假信息是确实的,对现实空间的社会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散布”或者“传播”却难以有令人信服的周全解释。
说到这里,我们来做两个有意思的假设。
假设一
如果民间组织从6月初接到消息后一直私下督促警方调查,警方积极作为,三下五除二就找到了赵某。经过调查,警方发现赵某所说是子虚乌有。而这整个过程,网民全不知情,此时赵某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假设二
如果民间组织从6月初接到消息后立即曝光,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让贵州各部门紧张得不得了,大张旗鼓大动干戈,最终查出赵某所说是子虚乌有。整个过程,网民都积极参与、奋力发声,此时赵某又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我相信答案可能是不一致的。在上述两种假设中,赵某的行为没有任何区别,责任承担似乎并不相同。
同样的行为,其责任不取决于行为本身的恶性,不取决于行为导致的直接影响,却取决于行为人完全无法掌控的曝光度。你想起了什么?“强行转发过500”?这恐怕是网络时代最可笑的事情吧?

鉴于刑事立法的专业性、庄严性和严谨性,民意或舆论与刑事立法活动的关系理应张弛有度。但近几年来我们看到,有些所谓的“民意”或“舆论”似乎有过度介入或影响刑事立法倾向之嫌,由此导致不理性的情绪性刑事立法现象频频发生。刑事领域中的情绪性立法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立法秩序,其所结出的“毒树之果”也必将损害法律的权威,腐蚀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
——刘宪权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