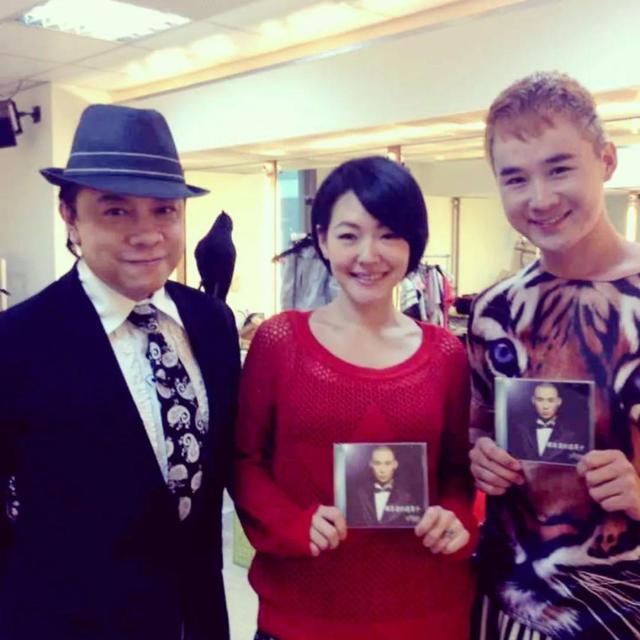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爷爷奶奶)

一
我爷爷去世得早,没有留下多少信息,董氏家谱上只留下一个姓名——董连士,更不肖说一张画像或照片了。
听奶奶说爷爷殁时才三十九(39)岁(这个岁数有另一个说法:大姐记得奶奶说过爷爷死时是二十九岁。我对二十九岁的说法有疑问,如果是这样,意味着爷爷比奶奶小十岁,即爷爷在十五岁时就当了父亲,这个可能性不大)。爷爷去世时是1947年,那时我父亲才四岁,父亲对爷爷的样貌没有多少印象。
按爷爷殁时三十九(39)岁来算,他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出生,生肖属猴,以此来说,爷爷比奶奶大两岁。爷爷具体的生日、卒日已不可考。可考的历史是我曾祖父的生卒年月日,曾祖父的牌位上记载得很清楚。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以便能估算出爷爷的合理的出生年份。
1947年,爷爷被征役到梁山那边抬担架,不小心被大车上的钉子挂伤了腿,得了破伤风,不治而亡。也不知道爷爷是为哪一方抬的担架,国军、共军?皆有可能,但往事已不可考。
爷爷弟兄两人,爷爷排二,哥哥叫董连柱。供奉我曾祖父牌位上的落款就是我的大爷爷董连柱(长子)的名字。
爷爷死后,是我大爷爷和奶奶共同撑起了这个家,养大了父亲和姑姑。地里的重活都是大爷爷一个人干;农闲时,村里人常常见到大爷爷挑着箩头在村庄里转悠,起早贪黑地拾粪。
奶奶和姑姑负责平时的一日三餐,农闲时纺花织布,逢集卖布。后来大爷爷去世,奶奶又多操持了一个营生——蒸馍、卖馍,这时父亲十五岁,已经当了泥瓦匠的学徒,跟着学砌墙盖房。父亲没活儿干时就帮着奶奶蒸馍、卖馍。
卖馍除了在集会上卖之外,通常多是下乡转悠着卖。父亲讲过有一回天蒙蒙亮时出去卖馍,在漫地里碰到一头像牛又不是牛的动物(眼睛比牛眼大,鼻子比牛的小。根据父亲的描述我觉得有点儿像麋鹿)朝他猛冲过来,把他吓了一跳。父亲赶紧掏出卖馍的秤杆和秤盘,用秤杆猛敲秤盘。那个怪物听到响声才拐了个弯,从父亲身边嗖地一声就冲了过去,蹄子踏地的声音嗒嗒地响,像盖房时用砖头砸墙。
二
奶奶姓蔡,没有大名,娘家人称她的小名三花。奶奶排行老三,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嫁到董家后奶奶就变成了“董蔡氏”,家谱上也只记载了一个“蔡氏”二字,权当是奶奶的名吧。村里人称她为“士奶奶”,这自然缘于爷爷的名字董连士。
奶奶生于清宣统二年腊月十八日(公元1910年1月28日),生肖属鸡。这一年也是费孝通、华罗庚、钱钟书、曹禺等出生以及霍元甲、马克·吐温、列夫·托尔斯泰等逝世之年;卒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廿二日(公元1995年6月19日),这一年也是邓丽君和张爱玲去世的年份。

(奶奶的遗像)
奶奶享年八十五(85)岁余,也算是高寿了。
奶奶的个子不高,方脸,脑后梳着一个发髻,有时用黑丝网扎着,有时只用一个竹簪子别着。奶奶冬春时常常戴着一顶黑色的绒布帽子,有时蒙着一方蓝黑色的斗纹头巾,这是那个年代中原地区的老年女人常戴的头衣。在我的记忆里,奶奶的脸一直是祥和的,根本看不出曾经受过的那么多的苦难。
奶奶的娘家是周庄的,在我们村西北方向,离我们村有七八里地。
五月廿二日,奶奶去世当天的下午,我还在课堂里上复习课,正忙于考高中。家里也在忙着收麦子、打场。放学后回到家里,见头门口放着一捆秆草和一沓烧纸,预感不妙,因为奶奶已经病倒卧床近一年了。院子里有几个族人和邻居,都是来帮忙的。我径向堂屋里望去,奶奶躺在当门的小床上,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只有去世的老人才会被摆放在这个位置。我木然地走过去,跪倒在床头前,放声大哭。
奶奶病倒是因为牵牛一事。一九九四年(公元1994年)深秋里的某一天,家里人都在地里摘拾棉花,只有奶奶一人在家。这时候突然下起了雨,奶奶见牛还在院子里栓着,正当头淋着雨,于是赶紧颠着小脚去牵牛。奶奶给牛解开缰绳,畜生也怕淋雨,缰绳一开它就着急忙慌地往牛屋里闯。进门时牛的大肚子一挤就把奶奶抗倒了,摔了个屁股墩。年轻人墩一下倒没有啥,但老年人的骨头脆,于是胯骨就被摔裂了。敷了药、打了石膏卧床休养了一个冬天,骨头的裂缝是长住了,但奶奶从此也下不了床、走不了路了。于是躺到第二年收麦时就不行了。
奶奶的去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奶奶最疼我,我在家里是老小。一到冬天我就和奶奶睡在一张床上,给她暖被窝、暖脚,暖了很多年,直到我上初中二年级。那些年奶奶给我讲过许多旧社会的故事,我对历史文化的启蒙和兴趣主要归功于奶奶。
奶奶走时,父亲、母亲、姑父、姐姐、哥哥都在床前守着。
我姑姑去世得早,她于1987年撒手人寰,年仅五十四(54)岁。姑姑临终前叮嘱姑父要替她尽孝送终。奶奶病重时,姑父一直守在她的病床边,伺候了四五天,直至奶奶咽气,然后又接着守灵,圆满地完成了姑姑的遗愿,替姑姑尽了长女的孝心。
三
奶奶这一生只养活下姑姑和父亲两个孩子。姑姑生于1933年,属鸡。姑姑出生时我爷爷是二十五岁,我奶奶是二十三岁,这个年龄在旧社会已经是高龄了。旧社会男女结婚早,十七八岁、十六七岁或更早就结婚了。
姑姑比父亲大十岁,听我父母说,从姑姑到父亲的这十年,奶奶的孩子一共夭折了三个。而父亲下面还有一个弟弟,约在一岁时夭折。这样加起来就夭折了四个孩子。奶奶二十三岁时才生下姑姑,可能姑姑不是奶奶的第一个孩子,姑姑的上面很可能还有孩子,只不过未能活下来。这些未能成人的孩子在奶奶的心里永远是一个伤痛。于是等到父亲出生时,奶奶心里的悲痛达到了极点,当父亲一落地,奶奶就狠下心来把父亲的一个小指的指尖咬掉了一小截。这是奶奶听信的一个偏方,说这样能留住孩子的性命。
于是父亲活了下来,也因此而倍受爷爷奶奶的宠爱。爷爷的去世让奶奶更加珍惜亲人的生命,越发地宠爱她的女儿和小儿子了。父亲在奶奶的呵护下像养娇闺女一样地长大,以至于后来父亲有了一个“二妮”的外号/小名,同龄人多称呼父亲的小名。
姑姑是奶奶的长女,她的过早病世,给了奶奶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不知道那时奶奶该有多伤心,但我知道的是在奶奶有生之年的最后七八年里,奶奶常常因为过度思念姑姑而发生被“鬼扑身”的事,每一次都是姑姑“扑身”到奶奶身上,发生时奶奶说的话,发出的声音都是姑姑生前的。
四
奶奶是一介农妇,不识字,但这并不妨碍奶奶是一个善良、坚韧、伟大、智慧的女人。
奶奶不仅能挣钱贴补家用,还能把家里的大小事务、亲戚邻居红白事的礼向往来等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奶奶持家的能力直接熏陶和培养了姑姑,以致于姑姑嫁人后成了婆家的实际当家人,就连读过书、当过兵、有见识的姑父都由衷地佩服姑姑持家的智慧。
三四年灾害时期,因为没有粮食吃,姑姑只好把她的大儿子(我大表哥锁哥)放在她的娘家,由我奶奶帮着养活。姑姑带着小儿子操持着姑父一家人的生活,空闲时就回到董堂的娘家,帮着我奶奶纺花织布,或者到地里遛拾大队里收剩下的红薯、萝卜。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那几年正是大表哥长身体的时候,但顿顿吃不饱,每天都饿得前胸贴后背,身上没有一点儿力气,走路时总想贴着墙根,用手扶着墙才能走。奶奶顿顿省下口粮,以让我的大表哥和父亲能够多吃一点。几个月下来,奶奶被饿得浑身浮肿,脚脖子肿得和腿肚子一般粗,小腿迎面骨上一摁一个坑,久久地难以消去。如此灾害的日子如果再长一点,奶奶肯定会被饿死。
在这个特殊的困难时期,由奶奶帮着养活的还有她娘家侄女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姑的大女儿,即我的表姐令姐。令姐和锁哥大小差不多,都在外婆(我奶奶)家住着。奶奶省吃俭用地抚养着他们两个,没偏没向,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
后来奶奶每每说起这些事,连连感叹那时候的日子真叫难啊。
后来锁哥和令姐也多次感叹:如果没有姥娘顿顿省给我的那一口稠的,我早就被饿死了!
因此,锁哥、令表姐常常来看望我奶奶。锁哥来得最勤,每一次来都会带很多好吃的:麦乳精、水果罐头、午餐肉罐头、高粱饴糖、冰糖等等。这些,在那个年代都是高级的营养品,只有在大的供销社里才能买到。
表姑是奶奶的娘家哥的女儿,嫁在了大寨,离我们村不远。所以表姑时常来看望她的姑姑(我奶奶)。我印象中表姑也是小脚,高高的个子,圆脸,表姑和我姑的样子有些像,长得像两姐妹一样。她们挽着发髻的样子跟晚年的宋庆龄有几分相似。
后来表姑跟着他的儿子移居到了遥远的西宁城里,每一次往老家打电话,表姑都会问起奶奶的状况,关心着奶奶的身体健康。而此时表姑业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奶奶去世后一直瞒着表姑,她每每问起奶奶,家人就会用一两句话来搪塞,说奶奶糊涂了,认不得人了等,怕她知道后伤心。
五
奶奶的姐姐嫁到了薛庄,生有三个儿子,姓任,老大叫秀坤,老二叫二榜,老三叫三鹿。老大成家后常年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老三智力有问题,没有娶上媳妇。二榜的智力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长得一表人才,一对大眼双眼皮,国字脸,红脸膛,牙齿洁白而整齐。但不知怎么就落下了一个结巴的毛病,说话连不成长句,越急越结巴,急得脸得红了还说不成。因此也没能娶上媳妇。
奶奶平时则照管着二榜大爷和三鹿叔叔的衣服鞋子,常常给他们做上几身衣裳和几双鞋子。有时也给他们套上一两床新被子让二榜大爷背回去换洗。奶奶就像半个娘一样操心着两个没有媳妇的外甥。
因此,二榜大爷直到五六十岁了还常常来看望他亲爱的姨(我奶奶),次数之多跟我的表姑和大表哥(锁哥)有一拼。
二榜大爷不怎么会骑自行车,他喜欢步行而来,肩膀上常常搭一个灰不溜秋的褡裢一样的棉布袋,从他家到俺家十多里地,走上半晌就到了。一到家,来不及擦掉额头上的细汗就从鼓囊囊的布袋里掏出奶奶爱吃的东西。有时是一大块豌豆黄,用草纸包着,还有些许温热;有时是三五个花皮大甜瓜,外皮深绿色有白纹的像青蛙皮的那种,这种瓜的瓜瓤是桔红色的,瓜肉是粉红色的,汁水像蜜一样的甜;有时是一串用柳条穿着的油条,一大嘟噜有十来根的样子,油条上粘着楝树叶;有时是几个鼓囊囊的烧饼,每一个的里面都夹满了酱牛肉;又或者是一包用草纸裹着的还冒着热气的水煎包……
奶奶总骂二榜大爷乱花钱,让他以后甭再买这么多东西了,自己又不太会赚钱,光靠给窑场里拉砖坯出苦力,能赚几个银钱呢!?二榜大爷听了多是憨憨地笑,嘴咧着,门牙瓷一样地白;有时也会断断续续地说上一两句:有钱,花-花-花不了-几个钱!
姑姑、姑父、表姑、大表哥、令表姐和二榜大爷他们对我奶奶的知礼、感恩和孝顺,深深地启蒙和影响着我长大成人后的价值观。他们知恩图报的根源何尝不是来自我奶奶善良的心底,从此也可以一窥旧社会的伦理道德。这是“老礼儿”了,不说也罢。新社会了,钱没有多到花不完,“老礼儿”也没有剩下多少。
六
晚年时奶奶的眼睛患上了轻微的白内障,看东西像蒙了一层细纱。而父亲那时却没有想到带奶奶到医院检查或动手术,连这些意识都没有。农村人的认知能力有限,不能苛责父亲。
那时奶奶的眼睛常感到有一点儿干涩,点上一滴氯霉素眼药水就没事了。我常常跑到诊所里给奶奶买眼药水,总是操心着奶奶的眼药水何时会用完。奶奶为此不止一次地夸我细心,会照顾人。如果这些是我的优点的话,何尝不是在奶奶的言传身教里形成的。
奶奶常常留一些好吃的给我,我总以为奶奶最疼我。可我也常常听姐姐、哥哥他们说起过奶奶也常留好吃的给他们。就在前两天二姐还在说奶奶最疼爱她呢。
奶奶的爱是博大的、无私的。
2022.04.28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