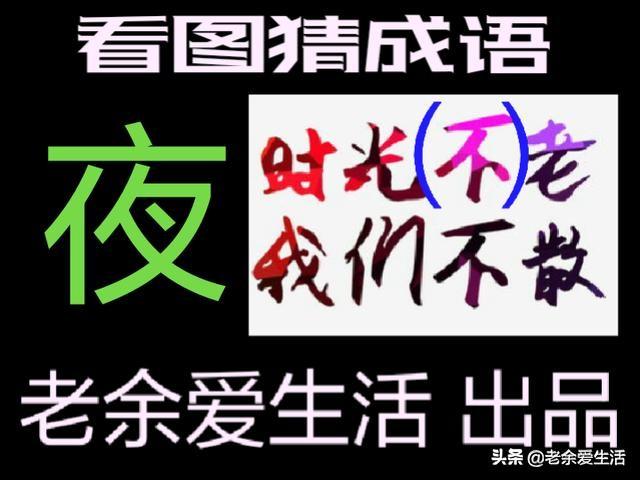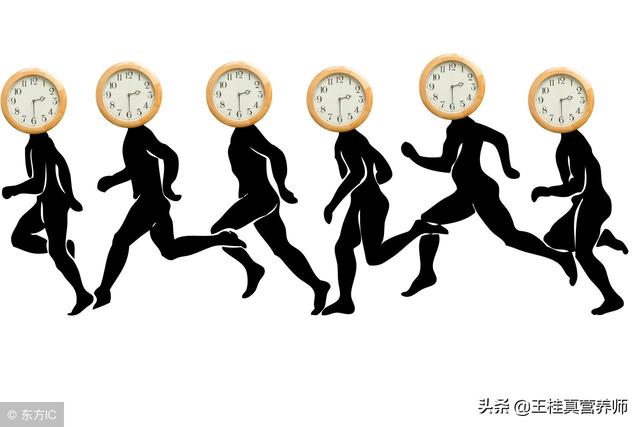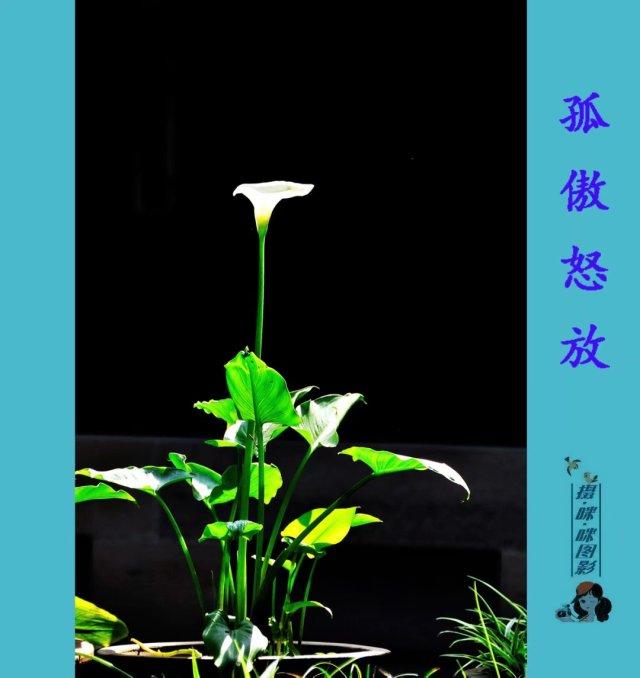文豪朱自清晚年有多惨(一代文豪朱自清饿死之谜)

朱自清与陈竹隐
1948年,是朱自清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对于一个学者、作家,这意味着思考和创作的终结,对于曾经从其思想文化遗产里受益的人,意味着深长的思念和不尽的感慨。
朱自清1948年的意义绝非仅止于此。这年,他的某些言论、文字和行动,被塑造为接受人民呼唤,终于从象牙之塔里走出的斗士,其晚年的“选择”和“转变”被界定为知识分子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宏大命题。
194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在朱自清的生命年轮里,又发生了什么?
1948年,是两个阶级搏斗初见分晓的一个特殊年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论他们曾持何政治立场,一个旧时代即将被埋葬,这点,哪怕终日兀坐书斋不问世事的人都会有所感知。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摆在面前,这就是面对这样的历史巨变与转折,你兴奋也好,沮丧、惶惑也罢,无法回避选择。
1948年的特别意义还在于,这一年,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的失败使国统区物价上涨,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面临着物质条件的困窘和生活状况的恶化。
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各种变化都不意外,只是这种变化往往有辐度大小之别、微调和巨变之异。
朱自清属于哪种呢?朱自清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不仅缘于天性,也是客观环境所致。朱自清最初以新文学家出名,后来却长期在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从他日记中可看出他在学术上是有压力的,充满了焦灼感,这种压力驱使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到学术研究上。当然,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没有政治倾向。朱自清的政治倾向,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个“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承认现有的秩序,认为这种秩序是保持“平静”的要素,但也可能因现实的刺激偶或流露不满,并对秩序的反抗者部分地表示同情。
当然,最重要的,这种人始终珍视个人的自由,对所有以各种名义挤压个人空间的企图敏感而警惕。
这位向来以诗一般的抒情散文著称的新文学家,还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阅读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有才的变迁》和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的情景,称赞赵树理的小说是一种“新体裁的小说”。
这时候,朱自清的写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他开始讨论“朗诵诗”和“标语口号”这些原本在学者教授视野之外的东西。他强调以“政治性”和“群众性”见长的朗诵诗“应该有独立的地位”;一边批评代表集体力量的标语口号是非理性的起哄,但又说:“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
朱自清晚年变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扭秧歌”。秧歌这种革命的符号虽然很受有左翼倾向的学生和大众的追捧,毕竟很难让国统区高等知识分子接受。于是,朱自清的“扭秧歌”就显得特别醒目了。
那些热烈赞颂朱自清“转变”的文章,最热衷提及的就是朱自清热情扭秧歌的意象:冯锺芸回忆,“在参加‘五四’青年节的联欢晚会上,他加入青年们长长的行列,扭陕北秧歌,和青年学生的心贴得更近。”
柏生回忆,特别使人记忆最深的是,1948年元旦晚,在余冠英家里开同乐晚会的那感人的情景。
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格,亲昵地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朱先生呢,对这来自解放区人民大众化的演出形式和内容,十分喜爱。他这种精神使在场的许多师生受到感动。
除了此时的朱自清多少带有一点民粹倾向,对原本是民间文艺形式的秧歌有了解之欲望外,似应更多地从其性格特点上去分析。
朱自清是个外圆内方的人,待人随和,不愿拂人面子,但这在很多时候并不代表他自己的真实想法。其早年日记里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一个他很不喜欢的人向他借钱,他借后,在日记中大骂那人“下流”。
按照一般分析,你不喜欢他,不借就是了,可朱自清不愿如此,借了又不甘心,于是转而向日记发牢骚。这种似乎有悖常理的做法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朱自清的性格。他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后也是如此,经常有学生请他讲演,并且题目都拟好了,朱自清不高兴,但几乎每次还是去了。
读了朱自清与秧歌有关的日记,又明了其性格特点之后,回头再看回忆、解读朱自清扭秧歌的文章,是否都不同程度地有“过度阐释”之嫌呢?因为“扭秧歌”,许多人盛赞朱自清晚年“表现得十分年轻”,在他们看来,这是找到精神皈依的人的自然心态。但透过另一种个人色彩强烈的文本——旧体诗,我们就会发现一片“悲凉之雾”。
1948年2月,在病中的朱自清看到吴景超夫人龚业雅的一篇散文《老境》,其中的萧瑟况味触动他写下了一首七律: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衰疾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室人相敬水同味,亲友时看星坠光。笔妙启予宵不寐,羡君行健尚南强。
诗中的衰飒之气是一个稍有旧文学修养的人都能体味出来的,难怪当时传抄到俞平伯、叶圣陶那儿,这两位老友都为之“不怡”。细细想来,在1948年那个特殊的年代,缠绵病榻的朱自清的这种悲凉之感谁说不正是人情之常?
除了“扭秧歌”,晚年朱自清还有一件事为人艳称,这就是“不领美国救济粮”。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的始末,王彬彬有一文作过精细的考证,这里不赘。
但有意思的是,因为此事,又因为一篇名文对此事格外论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篇名文关于朱自清的一段是这么说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自由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这篇名文在革命史、思想上的意义不必多论。
但有一个直接后果出人意料,这就是人们对朱自清之死的臆测。
自朱自清1948年辞世至今,关于其死因,权威的说法是他“贫病交加而死”,而在不少读过像上面这篇名文这样文字的读者印象中,朱自清居然是“饿死”的。不必奇怪,笔者当年束发读书,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朱自清“饿死”的印象从何而来?那篇名文的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因素,因为那段话从形式逻辑上讲,的确可以理解为“朱自清要么领救济粮,要么饿死”,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朱自清最后没领救济粮,当然就只有“饿死”一途了。但文章的艺术不能硬套逻辑,事实上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是真,拒领也肯定会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没饭吃了。
从根本上说,容易让人生出朱自清饿死印象的缘于另外一些大判断。什么样的大判断呢?朱自清所处的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的时代。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在那黑暗时代里,岂止是知识分子,可以说除了达官贵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颇为艰辛。
但是在这样的大道理的下面,在主流和大局之外,应该还有支流和个案,比如像朱自清这样全国有名的文化人,他的生活似乎还不会沦落到要被饿死的地步。
朱自清实死于严重的胃溃疡。这种病的起因与生活的颠沛流离有关,日寇侵华中朱自清所服务的清华大学曾几经搬迁;战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大大降低,这也是容易引发胃病的重要因素。
但教授们的生活水准究竟低到了何种程度?是否瓶无储粟屡告断炊?恐怕也不尽然,查阅朱自清的日记,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被公认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是经常会有饭局,而且隔三差五就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打打桥牌,很难想象,一个空着肚子的人会有心思和闲暇去斗这样的巧智。
可以认为,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处境不佳,但和大多数底层百姓相比,他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更不用说像朱自清这样名牌大学的教授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看不清世界大势,集中资源于内战,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波及,许多学生愤然冲出校门,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时如火如荼。
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和所谓币制改革使经济接近崩溃,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不能不大受影响,知识分子也一样,但揆诸现实,我们就会发现知识分子所受的这种影响肯定要小于一般底层群众。
《人民日报》的女记者金凤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回忆了1947年底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情景:中午时分,学校食堂送来白面馒头和菜汤,一旁监视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嘲笑我们:“你们吃得那么好,还成天喊反饥饿,你们挨饿了吗?”
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为老百姓反饥饿。全国老百姓不是被内战拖入绝境了吗!”
学生们对特务的反击自然是有力的,但从中也可反证我上面的判断:在校学生的生活是像金凤描述的这样,教授生活又如何呢?具体到朱自清,其实他应该是最不容易被联想到“饿死”这一凄惨图景的。不仅因为他的声望、地位和收入水平,也由于他的病。
稍有常识的人就都知道,胃溃疡这种病对进食有很多顾忌,既要禁吃某些食品,更不能多吃,稍不注意,就会呕吐,使胃大受折磨。
朱自清的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