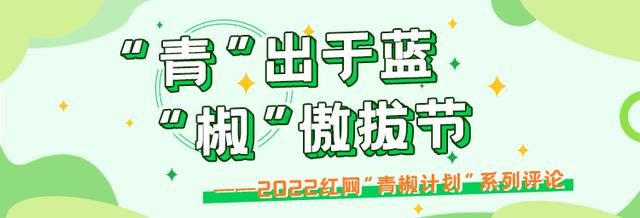明朝公主婚姻如何(语讷天下左思)

冥婚陋俗史考证及当代批判
作者|左思
一、什么是冥婚?
《周礼·地官·媒氏》有云:“禁迁葬与嫁殇者。”
什么是“迁葬”?汉末经学大师郑玄《周礼注》云:“迁葬,谓生时非夫妇,死既葬,迁之,使相从也。”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周礼正义》云:“迁葬,谓成人鰥寡,生时非夫妇,死乃嫁之。”其中“死既葬”是关键。
什么是“嫁殇”?“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礼相结,死而合之,是亦乱人伦者也!”(郑玄著《周礼注》)东汉经学家郑众云:“嫁殇者,谓嫁死人也,今时(即汉代)娶会是也。”贾公彦疏说:“殇者,生年十九以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殇娶者,举女殇,男可知也。”嫁殇就是“嫁死人”。清朝经学家惠士奇在《礼说》中有“周曰嫁殇,汉曰娶会,唐曰冥婚”之说。
其实惠士奇之说,也有不确切处。迁葬和嫁殇都称之为冥婚,只不过形式不一样,有略微的区别。所谓冥婚,又称阴婚,就是指生前没有夫妇之名,死后移棺合葬,并举行婚嫁仪式,以成夫妻之名。举行婚嫁仪式的双方,或者只要有一方已死,或者双方皆死,都应当称之为冥婚,迁葬和嫁殇正好是这两种情形。
所谓迁葬,就是欲行婚嫁的双方都已经死去,全由他们的家人做主举办婚嫁仪式,以成夫妇名分,俗称“鬼娶鬼”。这一类中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男女双方生前已定有婚约,但未来得及结婚就双双过世,由双方的家人代行婚礼,然后迁葬一处;二是男女双方生前并无婚约,但双方皆是未嫁而亡,由“鬼媒人”牵线搭桥,由双方家人代行婚礼,然后迁葬一处;三是生前曾为夫妇,后来夫死妇女改嫁,或者夫妇离婚,妇女改嫁,前夫后死,再嫁妇女被前夫儿女接回前夫家中,然后过世,或者再嫁妇女在现夫家过世,又与前夫合葬一处,类似于“复婚”,也算作冥婚。
所谓嫁殇,或谓娶会、娉会,是指婚嫁的双方,一方活着,一方已死,一般是因为早有婚约(也有没有婚约的),一方死后,仍然履行婚约,举办婚礼,以成夫妇之名,一般俗称“抱主成婚”。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男女双方定婚后,女方死去,男方将未婚妻的牌位(神主)请回家,与之举办婚礼仪式,俗称“娶鬼妻”。这种情况,一般男方可以再娶其他女子为妻子或妾室,以传宗接代,只不过原配正室的名分归“鬼妻”所有。二是男女双方定婚后,但男方死了,女方依旧嫁到男方家中,并抱着未婚夫的牌位(神主)或者公鸡等象征物,举办婚礼仪式,俗称“嫁鬼夫”。这种情况,一般女方不得再嫁他人,要终身为“鬼夫”守节。
由于古代女子地位低下,在古代比较常见的是“鬼娶鬼”或者“嫁鬼夫”。现代社会比较常见的也只有“迁葬”中的第二种类型,即并不相识的两个去世男女,合葬一处,以成夫妻之名。另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蛮俗》记载,南方地区还有一种特殊的冥婚风俗,俗称为“迎茅娘”。如有男子未娶妻而死者,家人为之束扎茅草,成女子模样,然后在郊外,敲锣打鼓,将“茅娘”迎接回来,并与男子合葬。这是用茅草人代替真实的亡女,具有象征意味。
二、冥婚的仪式
冥婚同正常的结婚相似,也要举行一整套婚礼仪式。冥婚的双方,至少有一方已经作古,所谓的婚姻,除了合葬一处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夫妻之实,也只为了有夫妻之名。所以为了彰显夫妻之名的婚礼仪式就显得尤其重要,甚至要比正常的婚礼举办得还要正式和热闹。
冥婚主要是为了求得生者的心理安慰,毫无疑问,冥婚的婚礼仪式肯定会以活人婚礼为模仿和借鉴对象。宋人郭彖在《睽本去》中载:“晋俗,男女年当婚娶,未婚而死者,命媒互求之,谓之‘鬼媒’,鬼亲后的两家来往如姻娅。”可见冥婚的婚礼仪式和正常婚礼仪式相似,但因为它的独特性,缺少仪式主角,也一定会与正常婚礼有所不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乡土作家王鲁彦有一篇文学地位显著的短篇小说《菊英的出嫁》,这篇小说主题就是写冥婚的。该小说的前半部分详细描写了菊英的母亲为八岁就因病去世的菊英筹办与举行冥婚婚礼的全过程。先是找媒人说合,看了照片,订下婚约,男方送来聘金,选了吉期,接下来就是预备嫁妆。菊英的母亲辛苦做工,省吃俭用,为菊英丰厚的嫁妆:
金簪二枚,银簪珠簪各一枚。金银发钗各二枚。挖耳,金的二个,银的一个。金的,银的和钻石的耳环各两副。金戒指四枚,又钻石的二枚。手镯三对。金的倒有二对。自内至外,四季衣服粗穿的俱备三套四套,细穿的各二套。凡丝罗缎如纺绸等衣服皆在粗穿之列。棉被八条,湖绉的占了四条。毯子四条,外国绒的占了两条。十字布乌贼枕六对,两面都挑出山水人物。大床一张,衣橱二个,方桌及琴桌各一个。椅,凳,茶几及各种木器,都用花梨木和其他上等的硬木做成,或雕刻,或嵌镶,都非常细致,全件漆上淡黄,金黄和淡红等各种颜色。玻璃的橱头箱中的银器光彩夺目。大小的蜡烛台六副,最大的每只重十二斤。其余日用的各种小件没有一件不精致,新奇,值钱。在种种不能详说(就是菊英的娘也不能一一记得清楚)的东西之外,还随去了良田十亩,每亩约计价一百二十元。
从作者不胜其烦罗列出的嫁妆清单,我们可以看出,和活人的婚礼没有二致,包括金银首饰、精美服饰、生活用品、日常家具、桌椅板凳、各种摆件等等,甚至还有琴桌、良田等,让人觉得比一般的婚礼还要奢华。当你第一次看这个小说的时候,看到这里,你不会觉得这个婚礼不正常。你会觉得作者就是在白描一场盛大的喜庆的结婚仪式。
可直写到吉期一到,婚礼开始,才会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直到“送嫂”、“纸童”、“纸婢”、“纸马”、“纸轿、“纸桌”、“纸椅”、“纸箱”、“纸屋”等名词出现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不是寻常的婚礼,恍然大悟,如梦方醒,震惊异常,原来是一场冥婚:
最先走过的是两个送嫂[注:专于婚丧时服侍女客,及平日与妇人绞面毛,其丈夫多为吹手兼轿夫,或管庙祠。此处系用为至男家报喜及服侍新娘子之用。]。他们的背上各斜披着一幅大红绫子,送嫂约过去有半里远近,队伍就到了。为首的是两盏红字的大灯笼。灯笼后八面旗子,八个吹手。随后便是一长排精制的,逼真的,各色纸童,纸婢,纸马,纸轿,纸桌,纸椅,纸箱,纸屋,以及许多纸做的器具。后面一项鼓阁[注:一种轿子形式,内置乐器数种,以一人司之,与娇后数人之乐相和。]两杠纸铺陈,两杠真铺陈。铺陈后一顶香亭,香亭后才是菊英的轿子。这轿子与平常花轿不同,不是红色,却是青色,四围结着彩。轿后十几个人抬着一口十分沉重的棺材,这就是菊英的灵柩。棺材在一套呆大的格子架中,架上盖着红色的绒毯,四面结着彩,后面跟送着两个坐轿的,和许多预备在中途折回的,步行的孩子。
送亲队伍、大红绫子、陪送嫁妆、花轿等,都是民间正常婚礼的元素。但冥婚仪式又加入了,“各色纸童,纸婢,纸马,纸轿,纸桌,纸椅,纸箱,纸屋,以及许多纸做的器具”,“轿后十几个人抬着一口十分沉重的棺材,这就是菊英的灵柩”,这些葬礼和亡灵祭祀礼仪的元素,就这样,红事与白事就在这种情况下糅合到了一起,阴阳完成了沟通,造成一种和谐的假象,显得十分别扭。
南宋词人康与之在《昨梦录》中曾有一段对冥婚婚礼记录比较详细:
北俗,男女年当嫁娶,未婚而死者,两家命媒互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细帖,各以父母命,祷而卜之。得卜,即制冥衣。男冠带、女裙帔等毕备,媒者就男墓,备酒果,祭以合婚。设二座相并,各立小幡长尺余者于座后。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动。奠毕,祝请男女相就,若合卺焉。其相喜者,则二幡微动,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为动,且合也。又有虑男女年幼,或未间教训,男即取先生已死者,书其姓名生时以荐之,使受教,女即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之属。既已,成婚。则或梦新妇谒翁姑,婿谒外舅也。不如是,则男女或作祟,见秽恶之迹,谓之男祥女祥鬼。两家亦薄以币帛酬“鬼媒”。“鬼媒”每岁察乡里男女之死者,而议资以养生焉。
除需要新郎新娘参与之外的仪式,几乎与正常婚礼仪式相同。唯合卺代之以小幡,通过小幡的动静判断冥婚双方的喜恶。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死去的男女如果没有受过教育,还要给他找已死的先生当老师,女性还需要纸保姆、纸使婢,可谓比生者考虑得还要周全。当时甚至有人以做“鬼媒”为生,可见冥婚流俗之盛。
古时女子如果未嫁早殇,是不允许进入自家祖茔的,真可谓死无葬身之地。已故女子的父母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找一个男人与其冥婚,这样这个女子才能成为另一家世系成员并受到这个世系的后代的祭祀。除了利用“鬼媒人”牵线搭桥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已故女子的父母把装着写有女子名字和生辰八家的纸装进一个布包里,然后扔在路边,如果路过的男人捡起布包,那么命中注定他就必须娶这个已故女子。如果幸运,这个男人有子孙,这意味着这个女子会被默认为这个男人的妻子,而这个男人的子孙今后必须担负起祭祀她的职责。
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记载:“山西石州风俗,凡男子未娶而死,其父母俟乡人有女死,必求以配之。议婚、定礼、纳币,率如生者,葬日亦复宴会亲戚。女死,父母欲为赘婿,礼亦如之。”“议婚、定礼、纳币”是我国传统正常婚姻制度中的常见程序。
清徐珂编纂《清稗类钞·婚姻类》中记载《山西冥婚俗》一则云:
有所谓冥婚者,凡男女未婚嫁而夭者,为之择配。且此男不必已聘此女,此女不必已字此男,固皆死后相配者耳。男家具饼食,女家备奁具。娶日,纸紮男女各一,置之彩舆,由男家迎归,行结婚礼。此事富家多行之,盖男家贪女家之奁赠也。此风以山右为盛,凡男女纳采后,若有夭殇,则行冥婚之礼,女死,归于壻茔;男死而女改字者,别觅殇女结为婚姻,陬吉合葬,冥衣、楮镪,备极经营,若婚嫁然。且有因争冥婚而兴讼者。
这两则记载虽极简略,但也可观其大略。通过“率如生者”、“备极经营”等语,亦知与寻常婚嫁一般。
有关近代“娶鬼妻”的冥婚仪式,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陆汉斌在《浙江月刊》上发表的《浙江偏远地区的冬至趣谈》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浙江安吉、孝丰二县边境的林边、洋沟和连坑、烙城等几个乡镇的居民,年届十六岁以下的姑娘不幸夭折时,她父母要替她请媒人找一个“冥婚夫”,找到冥婚夫之后,才能收敛。且死者的冥婚夫就是她双亲的正式女婿了,所以也要有一番选择;惟愿意应征做她冥婚夫的,大都是贫穷子弟,因弟兄多,恐日后没钱结婚。所以选择冥婚夫,也只能挑品行较好的青年人,谈不上“门当户对”了。冥婚夫寻妥之后,由媒人带他到女家时,他就具有“杖期生”[旧时,妻子去世,丈夫持丧棒祭奠,称为“杖期生”。]的身份,但不穿丧服。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他冥婚妻的灵位,并把冥婚妻的眉毛、手指甲前下,用红纸包一小包放在灵位前“香火碗”里,然后给她“开光”,道士们用纸捻成一条约铅笔大小的纸捻,俗称“纸捻芯”。一面念念有词,一面将纸捻醮了油,占起火给她冥婚夫,冥婚夫持此火在她的尸体上由头照到脚,由脚照到头,及第二次由头照到脚后,即将残余的火光丢入她香火碗里,便开始举行“冥婚”仪式;入殓之后,要把冥婚妻的灵位移到他自己家里来,请道士“择上家堂”(把她香火碗里那一包眉毛、指甲移到他祖先牌前一个大香炉里,俗称“公婆炉”之后,她就有他元配的地位,祖先牌上也有她的姓名,她就可以享受他子孙们的供奉、祭祀,并不是“无主孤魂了)。
三、冥婚的历史
关于冥婚的历史,非常久远,而且在正史、野史、小说、笔记等古代典籍中的相关记载都相当丰富。
根据甲骨文记载,早在夏商时期,已经有为已故妇人冥婚的,比如武丁之妃妇好,在其死后就又充当了上帝或成唐、大甲、祖乙、小乙等先王的“冥妇”,以进一步加强赖政治婚姻维系的商王族与异姓家族的血亲纽带。(参考宋镇豪著《夏商社会生活史》)可见上古时期,冥婚作为一种很重要的维系家族兴旺与统治的手段,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普遍认可和运用。
《楚辞》中有多篇描写人神之恋、神神之恋的,班固、朱熹等在评价楚辞时,也表达了对冥婚的态度。如朱熹云:“楚人之词,……语冥婚而越礼。”在楚辞中“语冥婚”都是“越礼”行为。班固对屈原持批评态度,说屈辞“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如上文所引,《周礼》也是禁止冥婚的。虽然《周礼》明文禁止“迁葬”与“嫁殇”,且主流话语体系中冥婚一直作为“越礼”行为,但是这种冥婚风俗在之后的历史图景中仍是延绵不绝,在历代社会生活中流传相当广泛。
据北宋著名金石家洪适《隶释》所载,汉朝《相府小史夏堪碑》云:“娉会谢氏,并灵合柩。”其中“娉会”就是“娶会”,在汉朝所谓“娶会”就是冥婚。根据碑文可以推测,传主死后,与一已故谢氏女子冥婚,谢氏迁葬与其合柩。
据《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载:“原女早亡,时太祖爱子仓舒亦没,太祖欲求合葬。原辞曰:‘合葬,非礼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哉。’太祖乃止。”仓舒就是魏太祖曹操最爱的儿子曹冲。曹操想让自己的爱子与邴原的亡女冥婚,然而邴原不愿意,就用《周礼》来反驳曹操,并用巧妙的语言劝止了曹操,所以曹操未能如愿。但在《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中又载,邓哀王冲字仓舒,“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则流涕,为娉甄氏亡女与之合葬”。可知曹操虽然被邴原婉言谢绝,但并没有放弃他的想法,明知道不合礼仪,最终还是实现了为曹冲完成冥婚的意愿,与甄氏亡女合葬。
《资治通鉴·魏纪四·明帝太和五年》载,魏明帝“爱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谥平原懿公主,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之置后,袭爵”。魏明帝曹睿之女与甄后从孙合葬这一案例是比较典型的冥婚,明确记载不仅加官进爵,而且给他们过继了后代以承袭爵位。
北朝时亦有冥婚的记载。《北史·穆崇传》载:“正国子平城,早卒。孝文时,始平公主薨于宫,追赠平城驸马都尉,与公主冥婚。”此处明确提到了冥婚。
东汉末年的经学家郑玄也明确表示过冥婚“亦乱人伦者也”,可见和《周礼》态度一致。但是从以上所列举事例,可知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冥婚风俗是很盛的。大多是为自己的过早夭折的爱子、爱女寻找已亡人合葬或婚配,皆属于“迁葬”之属。而且可以看出,要求冥婚的,都是统治阶级和贵族,可见当时冥婚虽然不被古礼认可,在社会上对冥婚有一定的抗拒力量,但在礼崩乐坏的年代,皇家是不太在意古礼的,为了满足自己心理上的慰藉,常常更愿意遵从感情意愿和当代流俗。
至唐代,有关冥婚史例的记载更是多不胜数,既有皇亲国戚,又有士农工商,几乎覆盖了整个社会各个阶层。
据《旧唐书·懿德太子重润传》载:唐中宗李旦长子李重润,因与其妹永泰郡主、婿魏王武延基等窃议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何得恣入皇宫,而得罪武则天被杖杀,年仅十九岁。李旦继位后,追谥为懿德太子,陪葬乾陵。“(中宗)为娉国子监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李重润墓位于乾陵东南隅约两公里处的黄土台地上,墓地四周原有围墙已毁,惟四角残存夯土堆。陵园地面陈设与特恩“号墓为陵”和以太子身份埋葬的记载相吻合。1971年7月至1972年2月,由陕西省博物馆和乾县文教局组织发掘。出土椁内残存两幅人体骨骼,经专家鉴定,在男骨盆上有一条明显的骨髓线,断定其年龄不超过二十岁,与文献记载李重润卒年仅十九岁和与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合葬相吻合。
据《旧唐书·崔无诐传》载:“崔无诐……父从礼,中宗韦庶人之舅,景龙中……萧至忠才位素高,甚承恩顾,敕亡先女冥婚韦庶人亡弟。无诐婚至忠女。”又《新唐书·萧至忠传》:“韦后尝为其弟间与至忠殇女冥婚。”中书令萧至忠世代官宦,韦皇后专权时,其亡女与韦皇后亡弟韦洵冥婚合葬。韦皇后覆灭后,萧至忠又挖开坟墓,把女儿的灵柩从韦洵墓中移走,另行安葬。冥婚原来也是可以离婚的,萧志忠前后的所作所为受到时人很大的非议和讥讽。
据《旧唐书·棣王琰传》载:“代宗立,追念琰死非其罪,乃追谥为承天皇帝,以兴信公主亡女张为恭顺皇后,冥婚焉。”建宁郡王李琰是唐肃宗李亨第三子,在安史之乱时曾辅佐肃宗抗击叛军有功,后来却因为被张良娣、李辅国诬陷而被肃宗赐死。代宗李豫继位以后,追念弟弟之死并不是因为有罪过,就在大历三年(769)下诏追谥李琰为承天皇帝,与兴信公主亡女张氏举行冥婚,追谥张氏为恭顺皇后,二人墓迁移合葬于顺陵。
以上所举事例皆是皇帝与朝臣之间屡屡实行冥婚,可知当时冥婚比以前更盛。另外在《唐代墓志汇编》中收入多篇墓志,都提到冥婚,可以看出在民间冥婚流俗也非常兴盛,试举几例如下:
张楚,贞观十九年(645)死,年20,显庆六年(661)“冥婚马氏”。
贾元叡,显庆五年(660)死,年17,“娉卫氏女为暝婚”合葬。
尚书都事故息颜子,显庆五年(660)死,年16,与“文林郎刘毅故第二女结为冥婚”。
张氏,垂拱元年(685)死,年21,次年与永淳二年(683)年20死的陈冲“冥婚合葬”。
清庙台斋郎王豫,延载元年(694)死,年28,“冥婚梁吴郡王孙邢州司兵萧府君之第四女”。
淮阳郡王韦洞,如意元年(692)死,年16,因是韦皇后弟,唐中宗制令“冥婚太子家令清河崔道猷亡第四女为妃而会葬”,并赙赠“物□千段,米粟五百石,衣等九袭”,“赐东园秘器,葬日给班剑州(四十)人,羽葆鼓吹仪仗送至墓所。往还长由调卒,将作穿土”,极为隆重。
李瑑,天宝四载(745)死,年27,其父母“娶同县刘氏为夫人”,合葬。
另外,《广异记》、《太平广记》、《鉴诫录》等当时小说集中,也多有记载冥婚故事。事虽怪异,不足为信,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冥婚在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可作佐证。
唐人认为,冥婚是“古之遗礼”,古人已有冥婚,今行之符合礼仪。同时认为“父母哀其魂孤,为结幽契”,冥婚能使这些年幼的亡人,在另一个世界里“幽途琴瑟”和谐,同穴而安。有的甚至认为,这“等秦娥之奔月,□同萧史之□仙,岂谓共归于蒿里”。总之,唐人对冥婚的认可度很高。比如据《新五代史·刘岳传》和《新唐书·郑餘庆传》所载,由于唐代冥婚风俗盛行,身居宰辅的郑餘庆,奉诏详定朝廷典制,他广泛收集当时士庶之家有关吉凶礼仪的书籍资料,加上参考平常的家中礼仪,写成了《书仪》两卷,其中就把冥婚列入典制,与寻常婚礼并列,且当时并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可知当时冥婚不仅是约定俗成,而且有人把其写入典制,给予了官方认可。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并不是没有反对冥婚的声音。如据唐代墓志,李卅三娘,元和三年(808)死,年17,祔葬外兄之墓,其家人认为:“若神而见知,幽魂有托,生为秦晋,没也岂殊,何必卢充冥婚然?”李三十三娘死后,并没有冥婚,而是和自己的兄长合葬。后来后唐明宗李嗣源读到郑餘庆的《书仪》,认为婚礼是吉礼,怎么能用在死人身上呢?唐明宗就诏令刘岳等通晓古今的有识之士按照古礼修订《书仪》等书,把冥婚从礼仪中删除。可见对于冥婚的态度,无论在江湖还是庙堂,都还是有争议的。
尽管五代之后,官方并不认可冥婚,但由于受此前的传统风俗影响,宋元以后,社会上冥婚之风更加盛行。宋代有关冥婚记载不多,但在元以后变本加厉起来。
在元代,冥婚制在蒙古人中也流行起来。《马可·波罗游记》中有一段话,正是描写了蒙古人中流行的冥婚风俗:
彼等尚有另一风习,设有女未嫁而死,而他人亦有子未娶而死者,两家父母大行婚仪,举行冥婚。婚约立后焚之,谓其子女在彼世获知其已婚配。已而两家父母互称姻戚,与子女在生时婚姻者无别。彼此互赠礼物,写于纸上焚之。谓死者在彼世获有诸物。
在《元史·列女传》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奇怪的事:“杨氏,东平须城人。夫郭三,从军襄阳,杨氏留事舅姑,以孝闻。至元六年,夫死戍所,母欲夺嫁之,杨氏号痛自誓,乃已。久之,夫骨还,舅曰:‘新妇年少,终必他适,可令吾子鳏处地下耶!’将求里人亡女骨合瘗之。杨氏闻,益悲,不食五日,自经死,遂与夫共葬焉。”此事记录在《列女传》中,显然是统治阶级要作为典型表彰杨氏的“贞洁”。但是其中奇怪的是,郭三明明有妻子,其父母还要为他求亡女冥婚。这无异于用封建礼教逼迫杨氏自杀,与其子殉葬。做鬼也不能一时没有妻子,可谓极端之至。
至明清时期,理学兴盛,封建统治者大肆宣扬矜表妇女节烈,致使社会对妇女贞节十分看重,对妇女造成许多伤害。以至于妇女未嫁而未婚夫死了,也要过门守节,即“嫁鬼夫”,或者自杀殉夫,然后就是男女双方家庭合葬冥婚,以至于明清两代有关这类冥婚的例子数不胜数,成为了惯例。
《明史·太祖诸子传》载,“(秦王樉之孙志均)宣德元年薨,妃张氏,未婚,入宫守服。”按照《礼记》记载,“曾子问曰:‘女未庙见而死,则如之何?’孔子曰:‘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女子嫁入男家,如果没有参拜家庙就死了,可以认为没有结为夫妇,女子要归葬自己的家族。可是明清时期,女子一旦许配与人,无论男子死活,注定就要为此人守节。
在《明史·烈女传》中,妇女自杀殉夫冥婚合葬的记载更多,如“孙氏,瓯宁人,幼解经史,字吴廷桂。廷桂死,孙欲奔丧,家人止不得,……(孙氏)届期缢死。”“项贞女,秀水人,国子生道亨女,字吴江周应祁。……周应祁病瘵,……(女)夜伺诸婢熟睡,独起以素丝约发,衣内外悉易以缟而紉其下裳。……遂自缢。两家父母从其志,竟合葬焉。”此类史载,数不胜数。
明清时期各种笔记、小说中记载的冥婚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如清叶廷琯《吹网录》记:“今西北诸省尚沿此风(指冥婚)。余姊婿席恺,官山西太原尉,女殇已葬,邑绅杨氏子亦殇,遣媒求婚于席,移女榇归,与子同穴,两家称姻媾焉。”
如《清稗类钞·婚姻类》中记载《顾秉藻冥婚华亭》一则:
顾秉藻幼而慧,父母皆奇爱之。咸丰辛酉,粤寇扰江苏,与诸昆弟奉其母避于沪,得疾而卒。临终,牵母衣,请以仲兄子礼枢为嗣,母泣而许之。无何,母亦卒。及乱定,还里,诸昆弟将如母命,而以秉藻未娶,不得有嗣。适金山钱氏有女,未许嫁而死,与秉藻年相若也。遂媒合之,仿迎娶之礼,迎其枢归,合葬于秉藻之墓。
明杨慎《丹铅录》云:“今民间犹有行(冥婚)焉而无禁也。”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盫随笔》云:“今俗男女已聘未婚而死者,女或抱主成亲,男或迎柩归葬。”可见,明清时期冥婚风俗在民间达到了巅峰,固然与唐朝的兴盛类似,有很多“鬼娶鬼”类型的冥婚,这是传统冥婚风俗的遗存和发展,而更多的是妇女为未婚夫殉死合葬,或者“嫁鬼夫”守活寡的类型,这是封建道德发展到了极端,对人的束缚更加严酷的结果。
近现代以来,并没有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民主与科学等思想的传播,社会上的冥婚风俗而有所遏止。如1934年,有人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冥婚》中说:“结阴亲:无论男女,到了成年时期,没有结婚就死去的人,家里因着孤男孤女不入祖坟的习俗所限,又不忍把他们埋在地边独受凄凉,又因为他们没有结过婚,家里总觉得对不住他们,要想着给死人继子立后,接续香火,这才有‘结阴亲’之说。”可见当时人们的想法,与几千年历史上的想法毫无二致。
上文提到的现代文学作品《菊英的出嫁》,是王鲁彦《柚子》集中的一篇佳作,是一篇真实描写“冥婚”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开始写菊英母亲为十八岁的女儿找到了婆家,两边家长按照严格讲究的地方性婚嫁习俗,有条不紊地开展,直到后来冥婚元素出现才让人省悟,原来新娘新郎皆是去世了的人,菊英已经去世了十年,读到此有种动人心魄之感。作者用忠实且细密的场面和人物描写,展示了浙东农村特异的冥婚习俗,具有现实意义的民俗学价值,折射了民国时期的冥婚流俗风貌。本篇小说虽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作品,但作者并没有在文字中明确表示出对冥婚流俗的批判,只是写出了一个大反差,让读者惊心动魄的同时,感觉到荒唐。
其实在清代小说集《醉醒石》中,也写到一个叫菊英的女子的故事。《醉醒石》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成书当在清代,但所书故事多发生在明代。《醉醒石》第四回《秉松筠烈女流芳图丽质痴儿受祸》,女主角姓程名菊英,也是浙江人,也是商人之女,被其父许配给同里秀才之子张国珍。正要为他们举办婚礼,却出现一个徐姓大户要求高价聘娶菊英,菊英之父因看重张国珍的品行,以不是卖女儿为由断然拒绝。徐家就仗势欺人,反诬程家赖婚私聘。菊英无奈,自杀身亡,程家差人报丧于张家。“张家父子,感她义气,都来送殓。张国珍也扶棺痛哭,如丧妻子一般,服了齐衰,在棺前行夫妻之礼。择日举殡,把棺材抬上张家祖坟。”这篇小说成书于明清时期,毫不意外的还是通过故事赞颂贞洁烈女,宣扬封建道德,与《菊英的出嫁》相对比,就会发现,王鲁彦借用“菊英”这个名字,既借鉴了这个小说的题材,又起到了一个反讽的作用。
近现代,甚至当代的例子也很多,试举几例。根据李敖在《蒋介石评传》中的研究,蒋介石曾有一弟弟,名叫蒋周传,四岁而亡。蒋母就找一早夭的王氏女子与之相配,即为结冥婚,后又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过继给蒋周传。
张鸣在《大荒纪事》一书中有一篇《九年一班的枪击事件》短文,讲到他的中学同学名叫张强,在一次意外枪击事件中被同学的枪意外打死,就埋在了学校旁边的山头上。有一年,一个女孩子上山砍柴从张强的坟前经过,突然倒地死了。人们都说,是张强把她招去了。于是,两家就结了亲,还正经办了喜酒,把俩人合葬了。如果此事属实,按时间推断,此冥婚事件当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阎连科在小说《风雅颂》后记中写到一件事:“我大伯的第六个孩子,在二十几年前当兵远赴新疆之后,在部队上因故结束了他不到二十岁的生命。依着我老家的习俗,父母健在,早亡的子女不能进入祖坟。这样,就给我的这个未婚的叔伯弟弟找了同村一个溺水死亡的姑娘,冥婚合葬在了我老家的村头。二十几年后,大伯的病逝,才算可以把我这个弟弟一并送入祖坟。因为我的叔伯弟弟当初冥婚时,没有举行过“婚礼”仪式;因了这次出殡,要给他们补办一个冥婚的仪式。也就在出殡这天,我家乡寒风凛冽,大雪飘飘,世界上一片皑白。然而,我叔伯弟弟和他“妻子”的灵棚里,主葬主婚的人,给那对小棺材上铺了大红的布匹,贴下了喜庆的冥婚对联。就在那天早上出殡的过程中,在我们上百个孝子披麻戴孝、顶着风雪、三拜九叩的行礼过程中,我的一个妹妹过来对我悄声地说,后边我弟弟的灵棚里和棺材上,落满许多红红黄黄的蝴蝶。”此事阎连科在《我与父辈》等作品中多次提及,时间发生在二零零四年。
四、应该杜绝冥婚陋俗
虽然当代冥婚风俗依然昌盛,但在我的家乡却从未听说过这种风俗。我知道冥婚,还是因为读到《菊英的出嫁》这篇小说,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震撼,除了带有悬疑性质的写作手法给我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还有就是我当时非常诧异于世间还有这种诡异的风俗习惯。
近来网络上泛起对冥婚讨论的风波,起因是一件刑事案件。2019年发生在山东的一起女子被虐待致死案,近日开庭审理,经记者采访得知,该已故女子已经被其家人冥配他人,还声称是按照本地风俗。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对此义愤填膺,认为女子生时被人虐待,死后又遭冥配。由此又引出多起有关冥婚的新闻,如河北康菲菲的坟墓深夜被人盗挖,康菲菲的尸骨及陪葬的“三金”下落不明。经公安侦查,发现盗取康菲菲尸骨及陪葬“三金”的人,是康菲菲的亲生父母。康菲菲的尸骨被取走后,又被以8万元的价格卖给别人配了阴亲。
又近日,在广西“艺起舞”高校街舞联赛中,广西财经学院的作品《殙》讲述了一名女子被父亲卖去配冥婚,在出嫁当天被活活勒死的故事,猛烈批判了冥婚陋俗。据舞社成员透露,该作品获得比赛亚军。这个消息在网络上引起极大反响,也激发了网友对冥婚风俗的讨论。
从以上冥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冥婚风俗起源很早,而且至今绵延不断,在三国和唐异常兴盛,自元明清直到近现代达到了巅峰。冥婚风俗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给生者带来心理上的安慰,或者维持政治上的利益和联系,或者契合传统传宗接代的陈规。但是,冥婚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多,除了是宣扬愚昧迷信之外,还有可能对生者造成财产甚至生命的损害,特别是元明清时期的冥婚,与唐以前的有所不同,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封建礼教的影响,贞节观念的鼓励,而逼迫或诱导妇女殉夫或者“嫁鬼夫”,这已经超出风俗的范畴,经常发生逼死活人的人间惨剧。近代以来,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风俗宣传了近百年,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俗披着传统文化的外衣,沉渣泛起,大行其道。
如果从地域来看,在历史上,冥婚风俗在北方与江浙地区最为盛行,特别是山西与浙江。上文所列举的史例可资为证。同时从民国时期编撰的《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四编“冥婚之习惯”里的两段,也可以得到旁证:
“娶鬼妻”(河南河北等处习惯),豫西河北等处,凡子未婚而故,往往择别姓字而殇之女,结为冥婚。俗谓之“娶鬼妻”,又曰“配骨”,以结婚后往往合葬也。
“冥配”(浙江平湖县习惯),平湖县,上、中、下三等社会,凡子弟未婚夭亡,类多择一门户相当、年龄相若之亡女,为之定婚,迎接木主过门,礼节如生人嫁娶,名曰“冥配”。盖以不如是,则灵魂将无所依归,不能入祠祭祀,且不能立后,一经冥配,即取得被继承人之资格,得为之立后也。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相关判决书,以关键字“冥婚”可搜索出74份判决,以关键字“阴婚”可搜索出183份判决,详情如下图(检索日期2020年12月19日)。根据地域及法院分类,可以看出,此类案件发生最多的四个省,分别是山西、陕西、河北(含北京)、河南,都是北方省份,当下与历史相符合。冥婚风俗甚盛的浙江,虽然该类案件时有发生,但与北方相比已经改观不少,可能原因是浙江经济发展比较发达,冥婚之类陋俗受到冲击。

中国裁判文书网“冥婚”搜索结果

中国裁判文书网“阴婚”搜索结果
近些年来,某些头脑里装满陈旧观念的人,假借政府宣扬传统文化的东风,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招牌,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比如前几年到处兴起的读《弟子规》运动,处处弥漫着邪教的味道,还美其名是宣传传统美德。看看《弟子规》的内容,这种书早应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如果秦始皇焚的是这类书,一点都不要觉得可惜。社会主义文化的退潮,封建迷信文化就回潮了,这是这四十多年的特点。
物质决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映社会存在。从以上几个案例可以看出,虽然今天和古代,同样是打着冥婚的旗号,但目的却有些非常微妙的不同。古人为子女实行冥婚,为的是符合封建伦理道德或者获得心灵上的慰藉,而如今的所谓冥婚,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金钱利益的驱使。当下的冥婚,不再单单是封建迷信下的痈疽,而且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肿瘤。所以当下社会竟然还存在冥婚这种陋俗,是封建迷信的回潮与资本主义的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时值当下,更应该彻底杜绝冥婚陋俗。
如何彻底杜绝冥婚陋俗,一个是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法律,《刑法》、《民法典》中的法律条文并不足以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二是要彻底改变人民的观念,不要再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幌子宣扬封建迷信,要把科学观念、法律观念深入人心。人民群众中的“四旧”要破除,“破四旧”要重提。很多人可能会误会。但是我要说的是,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中的“旧”不是指时间上的概念,不是指老思想,老文化,老风俗,老习惯,而是与现代性意义的“新”——新文化、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相对的概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伴随着“破四旧”,“兴四新”,一定要把传统文化与封建糟粕区分开来。
2020年12月18日于三言阁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