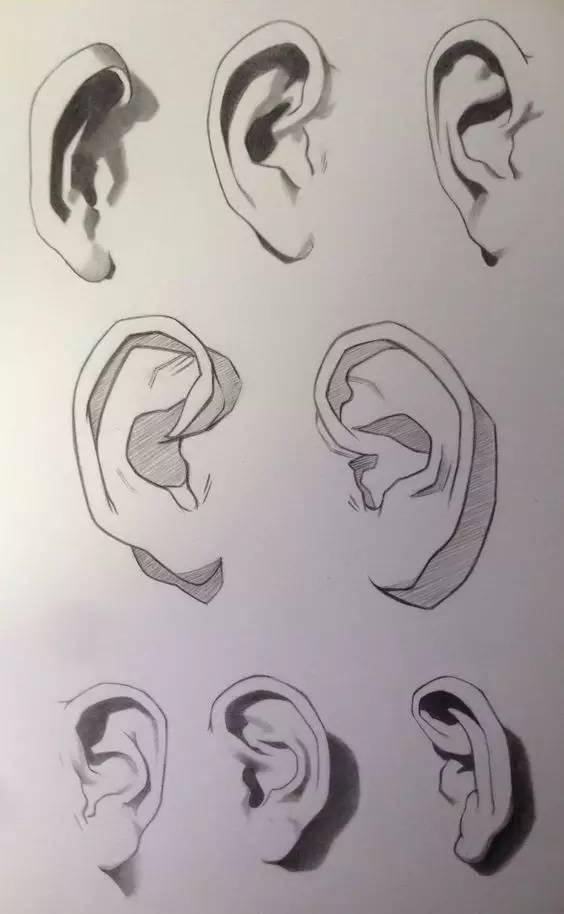淳安话和杭州话(移民佬淳安方言是移民流动的根)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方言是文化的一种,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过程,是文化的活化石。方言的土壤在民间,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方言所代表的,是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曾经听宁波朋友跟我讲过,说外地人听宁波人说话像唱歌,一开口就“哆啦咪发嗦啦西”的,后来与宁波人接触多了,还真有点那个意思。其实,不只是各地方言有各自的特点,其说话的语气也是各具特色。

方言的内涵不止只是乡音,也是一本书,一本流传千百年的百科全书。它丰富的内涵,涵盖于日常生活与生产的方方面面,有谚语、有歇后语,有俏皮话,有幽默,有褒有贬,丰富多彩。根据教育部的文献介绍,汉语方言通常分为十大方言,即:官话方言、晋方言、吴方言、徽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平话土话。

淳安与古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一衣带水、唇齿相依,两地的文化相融贯通,两地的贸易往来自古繁华。古狮城、古贺城曾是众多徽商的谋生之地,从安徽屯溪到汾口镇龙山街的徽龙古道,曾有多少两地商贾的梦想和汗水。如此这般,两地便有了共同的认知、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区域文化。可以从安徽省黄山学院文学院戴元枝教授所著的《明清徽州杂字研究》一书中找到了一条路,一条老家方言所曾经走过的路。

书中的很多描述,对我们年轻一辈似乎已经无感,但对更上一辈特别是爷爷那一辈的人来说,曾经是那样地熟悉,就如同与一位老邻居在聊家常,他所娓娓道来的,都是我们曾经的日常所见,是那样地亲切。譬如说:“农业耙耖,窖桶窖勺,砌磡填路,扁擔柱棒,牛轭犁头,砍斫担拕,作坊作马,刀鞘刀把,谷扠谷扒,杖杆折尺,打箍破蔑,犜牛阉猪,粥饭裹粽,索面点心”等等。书中所称的那些物件,就与老家的方言同出一辙,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但戴元枝教授所作的却是《明清徽州杂字研究》,我们难道不能从中悟出点什么吗?不过,这仅仅只是家乡方言寻根的一条路而已。

语言随着人的迁徙而迁徙,如今遍布江西省的淳安乡音,是因为50年前新安江水库建设的那一次移民,那一次有29万多人口外迁的大移民,最远的移到了新疆石河子,从此,淳安乡音便飘荡在了祖国最西部的那片大地。同理,我们如今的语言体系,除了徽文化的影响,移民的因素也不可小觑。譬如说,淳安余氏的发源地在长江以北,过江后在镇江生活了多年,后一路南迁,来到了原遂安萝蔓塘。因一场大火,余氏居住了125年的故乡又被毁于一旦,遂四散开去。而余氏的这个迁徙过程,前后延续了两千余年,这期间的语言不可能没有变化,一个“鱼”字发音的变化来印证这个问题是确实存在的。

鱼(yú),与姓氏余同一个音。但在老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却没人念鱼yú,而念女nǚ字的第二声nǘ。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教育的普及,年轻人文化水平的提高,方言也逐渐地向普通话转化,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很少有把鱼yú说成nǘ了。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因为,历史总是向前的,方言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就如那陈年的佳酿,越陈越香。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