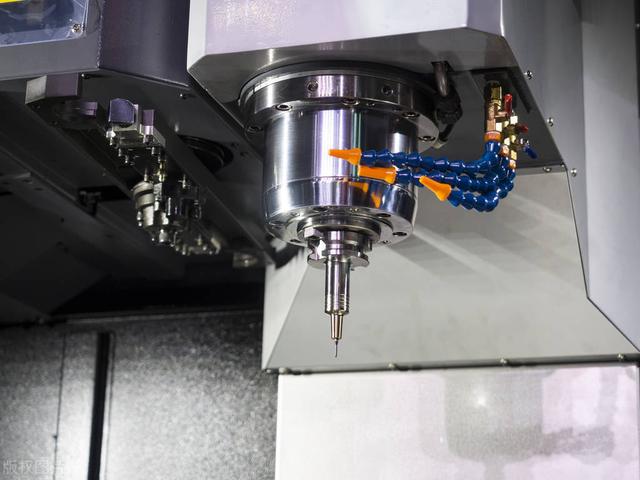弘一法师和李叔同(李叔同请叫我弘一)
文/孙希彬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唱起这首《送别》时,就想起它的词作者李叔同。
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 1880年生于天津的一个富商之家,1942年圆寂于福建泉州。生年跨越晚清和民国两个时代。作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李叔同才华横溢,学贯中西,集诗词书画、音乐、戏剧、篆刻、美术、文学于一身,39岁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却到杭州虎跑寺出家当了和尚,法号弘一。从此,那个年轻时风流倜傥,才惊四座的翩翩浊世佳公子就成了弘一大师。
原来只知道李叔同是《送别》的歌词作者,后来才知道,李叔同是个高僧,是个传奇。当年,李叔同颇有些杜牧的风范,“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亦正是他的写照。由于出身富贵人家,他可谓少不更事,与一帮诗人文友吟风弄月,游山玩水,混迹于烟花艺馆之地,留下几多风流韵事。但是成家立业之后的李叔同心境为之一变,忽然大彻大悟,厌倦红尘,遂有出尘之念。这个念头是如此固执和强烈,以致于亲朋好友劝不动,娇妻爱子留不住,终于割断情丝,遁入空门。在他剃度那一天,他的妻子以及曾经深爱的红颜知己一齐跪在寺外,进行"哭谏"。可惜此时的李叔同早已是四大皆空,向佛的慧根萌发,红尘色相于他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任谁也拦不住他。传1918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李叔同正式皈依佛门。剃度几个星期后,他的妻子——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杭州灵隐寺,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劝说丈夫切莫弃她出家。这一年,是两人相识后的第11年。然而李叔同决心已定,连寺门都没有让妻子和孩子进,妻子无奈离去。 他的妻子知道已挽不回丈夫的心,便要与他见最后一面。当时是清晨,薄雾中的西湖两舟相向,李叔同的日本妻子喊:“叔同——” 李叔同说:“请叫我弘一”。妻子:“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李叔同:“爱,就是慈悲。” 妻子悲伤地责问道:“你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李叔同无语,默然离去。”说实话,每读此,总有“高山仰止”之敬意,亦有司马迁所说的那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觉。
弘一法师虽以持律闻名,但笃志念佛。晚年时神采气力渐衰,自知将要往生,因而尽力弘法,时常劝人听时钟念佛,依照时钟滴答滴答的声响,设想为阿弥陀佛四字。若是念六字佛号者,则以第一个滴为“南无”,答为“阿弥”,第二个滴为“陀”,答为“佛”。他的听时钟念佛,不失为一个摄心念佛妙法。

公元一九四二年春天,弘一大师前往灵瑞山讲经。不久之后,住在温陵养老院,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为大众讲经,并向院中的老人讲说净土法要。二十三日示现些微疾病,拒绝医药及探问,只是专一念佛。二十七日绝食,只饮水。二十八日写遗嘱,交代妙莲法师负责后事。九月一日下午,在一张纸上写著“悲欣交集” ,交给妙莲,并嘱咐注意:如在助念时,见我流泪,并非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是悲喜交集所感。说完话,仍默念佛号。四日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地往生了。时年六十三岁。荼毗后获舍利子一千八百粒,舍利块有六百块。

弘一大师在佛24年,恪守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一生光明磊落,潇洒飘逸,道德文章,高山仰止,赢得了当时以及后世无数政要名流的敬仰。尽管如此,弘一法师却说自己:一事无成身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其赠好友夏丏尊偈语曰: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佛教泰斗赵朴初赞弘一诗云: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照天心。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弘一大德,山高水长......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