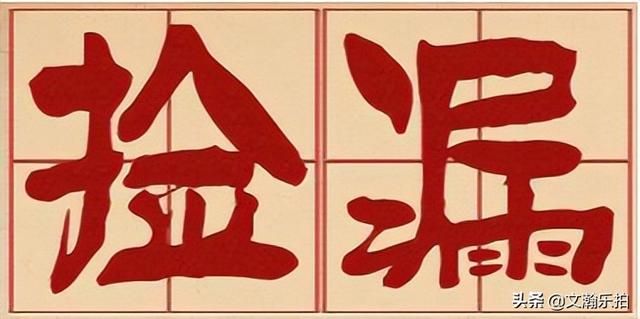千年沧桑的容颜(镜子的背影岁月的千秋)
早年走进博物馆看铜镜的时候,心头一直有一个问题:这镜子上有这么多图案,还怎么映照观众们俊朗姣好的面庞呢?彼时的我大概深中格林兄弟和唐太宗的毒,以为镜子是且仅是如实映出真相的存在。直到后来小伙伴一语惊醒梦中人:博物馆哪会给你看铜镜锈蚀斑斑的正面——早就照不出人了,展示的都是镜子的背面!!
或许背负唐太宗的三镜理论太过沉重,或许白雪公主遭受的迫害让魔镜们良心不安,在时光的浸润中,那“刚直不阿”的铜镜终究老去,终于不必再为“上价值”和“得罪人”而烦恼,得以转身华丽。而我们眼中花团锦簇的“背面”,或许才是铜镜自我的“正面”——这大概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铜镜展叫做“镜里千秋”而非“镜鉴千秋”的原因吧。
汉镜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艺术的高峰期。这一高峰期的出现,颇值得玩味:众所周知,从夏商周到秦汉,青铜器艺术整体上是在走下坡路,特别是青铜容器,由原本的华贵精美转变为简单朴素,但一些特殊的器类,如灯、炉、镜等,却精品迭出,个中原因不易索解。放胆猜测:或许是当时人们把从青铜器上腾出来的艺术精力,一股脑地投注在了这些器类的营造上,使得它们大放异彩吧。

草叶纹镜 摄影/丁雨

星云纹镜 摄影/丁雨

山字镜 摄影/丁雨
战国秦汉时期铜镜种类众多,草叶纹镜、星云纹镜、山字镜、规矩纹镜都是极为流行的代表性镜类。尽管主体纹饰有所差别,但以四神、五灵和铭文为饰,却是一时之风。在诸多镜种中,规矩纹镜是经常令人不解的一款。这番不解,来源于其特殊的名字。其他铜镜皆是以最具标志性的纹饰命名,如草叶、星云、山字,命名由来,一目了然。规矩纹镜实质也是如此,只是“规矩”在现代语境中,更多是以“法度”“标准”的概念出现,让人忘记了其原本来自于画圆和画方的工具:圆规与曲尺。所谓“规矩纹”,指的其实是镜背常见的如字母“T”“V”“L”一般的图案。也正是因为这些图案,早先海外学者便直截了当地称之为TVL纹镜。这种方便操作的叫法当然不符合我国的古今语境。1942年,梁上椿在《岩窟藏镜》中指出,日本学者梅原末治最早根据TVL的形态,提出此类纹饰可称为“方格规矩”。规矩镜一名遂流传开来。

西汉“中国大宁”博局纹铜镜
图片来自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
“规矩”之名的竞争力,当然不止汉字之于字母的天然优势。规矩方圆,与铜镜上各类图案配合,如纵深推演,恰能形成一套符合两汉时人的宇宙观。只是这番演绎的立论根基是来自于推测,毕竟不甚牢靠。解铃还须系铃人,铜镜留下的问题,只有铜镜自己能够解答。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在国家博物馆所藏新莽时期的规矩纹镜上发现一首诗,中有“刻娄博局去不羊,家常大富宜君王”之句。其中“去不羊”,为“去不祥”,即去除不祥之意,此句之意,翻译成白话,便是刻上博局纹去除不祥(事物、预兆)。此诗现世,无异于规矩纹镜自报家门:我其实叫博局纹镜。
如今我们对“博局”一词的含义已不熟悉,但在秦汉时期,博戏却是十分流行的游戏,有学者认为它是现代象棋的前身。而博局相当于博戏中所用的棋盘。展览中特意用展板展出了浙江地区出土的木博局棋盘,“T”“V”“L”一个也没有少,且其图案的核心布局与博局纹镜丝丝入扣。由此,名物相符,真相大白。
博局走出棋盘,走上铜镜,当是因为其本身的含义在时人眼中获得了升华。在“刻娄博局去不羊”这一铭刻中,便可知道其应有去恶辟邪的功效。实际上,学者们对于博局纹含义的探讨已历百年,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看法认为,“T”“L”两“字母”代表东南西北四方,“V”代表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维,博局的方形棋盘和铜镜的圆形,构成了天圆地方的结构,而铜镜法天象地,由此或许也便有了沟通天人的功能。不然为何镜上铭文中,皆是寄托希冀之语呢?
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长沙出土的鎏金规矩纹镜,一向被公认为是此款镜中的极品,为此次镇展之宝。此镜四神皆备、云气缭绕,纹饰规整精致,色泽光润,外观夺目,尤显特殊的是其外缘的一圈铭文,如做简单句读,大体如下:“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元吉,有纪纲。”此镜纹饰铭文虽然精美,但与当时铜镜铭文套路并无不同。唯“中国”二字,所指范围恐较“宅兹中国”所指已有扩大,而更显示出两汉之交时人们对国家认同的变化。天下太平,子孙安康,种种祈愿,尽在一镜之中。汉人重镜,大抵如斯。
唐镜
唐代是铜镜艺术的又一高峰,尤以盛唐时期最为辉煌。如此盛况,可能和唐代的皇帝有关。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此言因魏征逝世而发。魏征为其重臣,以镜为喻,把“正衣冠”与“知兴替”“明得失”等相提并论,可知“以铜为镜正衣冠”在唐太宗的日常生活中应当也是相当有分量的事情。唐太宗理论先行,其用镜如何,却不得而知,反不如他重孙子唐玄宗用的镜子出名。在唐玄宗过生日的安排中,有一项惯例,是要王公贵戚与自己互赠铜镜。皇帝千秋万岁,生日称千秋节,铜镜便也称“千秋镜”。这些千秋镜一般为当时的铸镜中心扬州所造。制造亦有讲究,须得在扬子江心熔炼六七十道,放得成品,由此又得名“江心镜”“百炼镜”,镜背一般有千秋字样,图案包括盘龙、月宫、衔长绶的鸾鸟等,以盘龙为多。以等级论,此镜应属唐代规格档次最高的铜镜,但平心而论,以镜背装饰来看,还是特种工艺镜更胜一筹。

唐-高士宴乐纹嵌螺钿纹镜
图片来自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
唐代是镜子装饰自己的黄金时代,装饰镜背的高级工艺很多,包括金背、银背、鎏金、螺钿、金银平脱等等。这些特种工艺术语听起来很复杂,但总结起来都是一回事儿:就是给镜背“化妆”,想方设法往上加点料,比如金背、银背,相当于给镜背戴个金银面具;螺钿、宝钿,就是把蚌片和宝石想办法粘到镜背上去;金银平脱稍显复杂,其实也就是把金银箔片贴到镜背,然后刷漆数层,再打磨掉金银片上的漆,把黄白之色显露出来,与深沉漆色形成对比,使之富于色彩张力。虽然听起来并不复杂,工艺、纹饰以排列组合方法略加调配,足以让小小一面铜镜熠熠生辉。国博此次展览的螺钿镜与金银平脱镜足以见其一斑,但若论特种工艺镜的收藏,仍是以日本正仓院所藏最为精彩,特别是有一件黄金琉璃花瓣镜,海内罕见。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认为唐代有此工艺。此件莹润华贵之镜,或可被视为唐镜美学和艺术的巅峰之作。

唐-羽人花鸟金银平脱铜镜
图片来自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
唐镜精美,故而其用途不止鉴容正衣,亦为高档车辆和建筑装饰所必备。唐代一些宫殿为凸显装修效果,所用铜镜可达数千。如果仅是为了室内的光线处理,铜镜背面似不应当如此复杂。唐代大多数铜镜镜背存有装饰,故而在室内装饰中,究竟是利用镜面还是镜背,实际尚未可知。但至少如金银平脱镜、黄金琉璃镜这些特种工艺镜,唐人应当是舍不得让镜背“面壁思过”的吧。

唐-正仓院藏黄金琉璃花瓣镜
图片来自正仓院官方网站
展览行至隋唐,便匆匆转移话题至铜镜的工艺制作与文化交流,实是因为自宋代开始,铜镜艺术便已乏善可陈。两宋时期虽为中国工艺美术发展的高峰时段,无奈时人兴趣不在铜镜,所留遗物熔炼不精、画面粗疏。当然,也不能说宋人对铜镜毫无想法,但估计当时工艺美术界的精英并未参与铜镜艺术的创新。

宋镜 摄影/丁雨
镜背虽辉煌不再,但人们对镜子奇妙的特性仍兴趣不减。厅堂之上的“明镜高悬”匾额、诸多明清神怪小说中照妖镜、阴阳镜等一系列神奇镜子的发明和想象,寄予了人们勘破真相、镇压邪恶的希望,也蕴含着思想史视野中铜镜灵魂的升华。不过,沧海桑田之后,那些幸存下来的镜子们,却只愿为我们留下款款的背影,或许是因为,当日明镜高悬,已阅尽世间风景;如今揽鉴自现,愿留众生气象万千。
文|丁雨
编辑|史祎
本文刊登于2021年2月26日《北京青年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