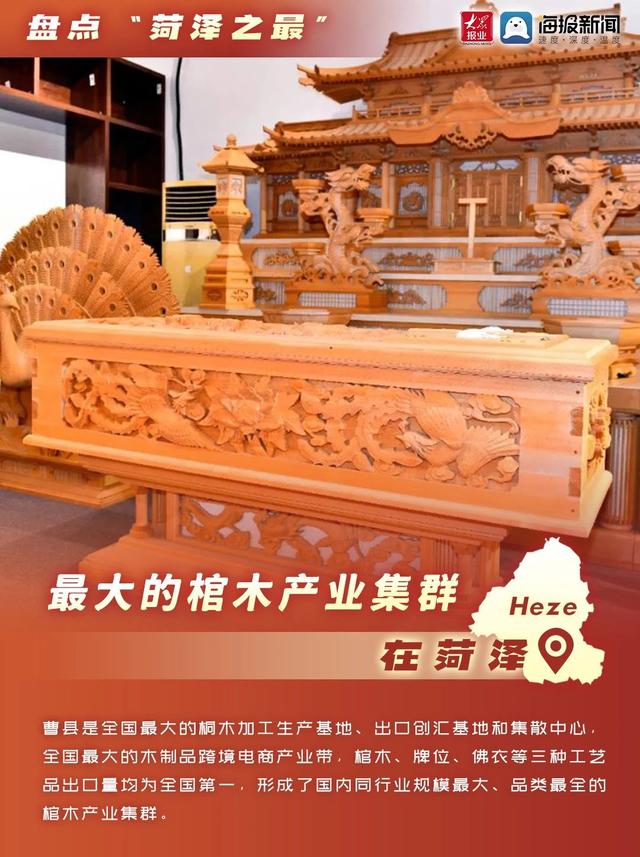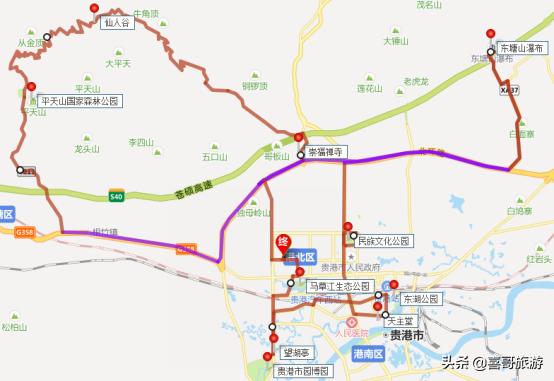南宋抗金队伍的领导(感戴报德与循吏象征)
转自“史学集刊”微信公众号原载《史学集刊》2021年第6期,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南宋抗金队伍的领导?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南宋抗金队伍的领导
转自“史学集刊”微信公众号。
原载《史学集刊》2021年第6期。
感戴报德与循吏象征:宋代生祠的盛行与地方社会
韩冠群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宋初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朝廷不再将颁授碑祠作为笼络地方或政绩奖励的手段,对生祠放松了管制。这使得修建生祠的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地方,为其盛行创造了条件。生祠因兼具为官员祈福祈寿与颂扬美名的功能,从而成为民众偏爱的报答方式。作为循吏传统的重要象征,建祠立碑对于提高官员声望、塑造循吏身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官员道德实践得到认可的标志,故受到推崇。同时,地方士民借此评价官员的施政效果,把各种善政措施固定化,以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宋代生祠的盛行。
关键词:宋代;生祠;循吏;地方社会
建生祠、立德政碑以颂扬官员德政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项悠久传统。自汉代以降,延绵不绝。但在不同时期,民众采取的方式却有所不同。唐代时,从官方到民间更多地采用树德政碑的方式。金元时期最为盛行建立去思碑。明清时期,建生祠和立德政碑都被民众采用,不过德政碑似乎更流行。在宋代,建生祠的方式最普遍。由于帝制时期的普通民众大都文化水平较低,很少留下反映他们生活实情的文字记录,他们成为历史研究中“沉默的多数”。而建生祠、立德政碑等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反映了民众的情感和利益诉求,从而为我们探求其情感世界和生存状态等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同时,建祠立碑也和国家制度法规、地方官员的实际作为、地方士人的角色密切相关。因此,这一活动也成为考察国家权力与基层士民互动关系的一扇窗口。
略检宋人的传记史籍、文集、方志、金石志等就可发现,立生祠的事例比比皆是,却很少立德政碑。[1]宋代不仅所立生祠数量多,而且参与者也很广泛。除了普通民众,很多官员、士人也参与生祠兴建与记文的撰写。那么,为何宋代官民会更多地选择立生祠而不是树德政碑?生祠对于他们具有怎样的意义?如何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情感和利益诉求?目前学界对唐宋时期的生祠研究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2]也有学者回应这一问题。如刘馨珺指出:唐代民众树立德政碑对于官员考课升迁有着重要意义,而在宋代,两者的关系是脱离的。“民间若要感谢有善政的官员,以简单的‘绘像’亦可表达类似生祠的祷祝,还具有替官员祈福的积极意义,于是宋代以后的生祠事例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3]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宋代史料中也有很多生祠祈福的事例,不过这只是从民众感戴官员的情感诉求出发的考察。在此之外,当有其他层次的原因。还有研究者从民众面临的现实困境来解释生祠较多的现象,如战乱频仍、水旱灾害多发、赋税负担重等。[4]但这些只是触发士民感戴官员的外部因素,并不必然导致德政碑的减少与生祠的兴盛。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众多表达感戴的方式中,为何生祠受到宋代吏民的空前青睐,而不是德政碑或其他方式。可见,由于学者的考察视角基本上局限于两个朝代内部,并没有动态地考察由唐至宋碑祠修建的演变过程,也就未能厘清两个朝代生祠立碑的内在差异。本文拟从唐代朝廷颁授碑祠的初衷及其变化入手,探讨生祠立碑在唐宋时代的内在差异,并对宋代生祠兴盛的现象做出解释,以展现地方社会的丰富面相。
一、中唐至宋初的碑祠颁授及其终结
唐代建立之初,承袭魏晋以来国家管制吏民立私碑的规定,明令禁止长吏擅立德政碑或者遣人申请立碑。[5]而此时并未见到律文中对修建生祠的管制。直到开元末年成书的《唐六典》才有相关规定。该书“礼部郎中员外郎”条载:
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立碑;七品已上立碣;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凡石人、石兽之类,三品已上用六,五品已上用四。(凡德政碑及生祠,皆取政绩可称,州为申省,省司勘覆定,奏闻,乃立焉。)[6]
学者对该条史料引用较多,但是似乎忽略了该规定的长时段背景和具体语境。正如杨俊峰所指出,《唐六典》是在规定官吏死后建立碑碣的制度后,才补充规定了官吏生前立碑的制度。这表明唐廷管制德政碑、生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恰当、公允地赐予官吏荣耀。[7]朝廷将原本具有民间属性的生祠纳入官僚体制,使之成为荣耀和奖励官员的一种手段,所以才详细规定碑祠的申建流程。揆之于情理,以生祠来赐予官员荣耀应当也有一定的程序,不过从目前史料来看,此前的生祠修建的确未见申请、批准的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朝廷将生祠作为褒奖手段的时间是晚于德政碑的。此后吏民为官员建生祠均需向州县申请,州县上奏尚书省,经考功司勘验,朝廷批准后方可建立。其流程与德政碑并无二致。其中,离任请碑、政绩优异是申请碑祠的条件,而吏部考功司的勘验核查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正是考功司的勘验保证了申请者的政绩真实可信,也保证了碑祠不会被滥授。如郑浣担任考功员外郎时,“刺史有驱迫人吏上言政绩,请刊石纪政者”,郑浣探访勘验,得其实情,拒绝授碑。[8]可见,朝廷将碑祠的颁授权收归中央,其初衷在于既保证建祠立碑活动真实地反映官员的善政以荣耀官员,又切实地回应民众对良吏的感戴怀思。
安史之乱后,道一级的观察使或节度使开始介入生祠的申请流程。[9]其中诸道观察使发挥着文书呈请与监察考核的双重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碑祠都如此,前述通过州县官的申请程序仍然保留。大和四年(830)高陵李士清等人为刘县令申请遗爱碑可为例证。[10]此后,随着中央控制力的下降和地方独立性的增强,碑祠所具有的奖励、荣耀官员的意义发生了变化。由于碑祠是由朝廷颁授,以皇帝名义敕建,故代表着崇高的荣誉,一些对抗朝廷的强藩遂将敕建碑祠作为神化自我、强化自身统治的工具。他们或通过监军上表请求,或由吏民诣阙请求碑祠,同时节帅不离任,从而彻底破坏了这一请碑条件。[11]比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德政碑是由“缁黄耋耆诣阙陈乞,请颂德褒政,列于金石”。[12]田承嗣还曾向朝廷请建生祠,但未获批准。直到德宗贞元年间,其子田绪主政时,才获准建立。按照唐制,田承嗣官至节度使,死后复赠太傅,其完全具备立家庙的资格。而田绪却宁愿在其父死后追立生祠,也不立家庙,这清晰地反映出敕立生祠对于藩镇维系统治的重要意义。大约在贞元二年至元和四年(786-809),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同时建有生祠和德政碑。宪宗平定淮西后,裴度改其生祠为紫极宫,其德政碑也被磨灭重刻,由韩愈改写为著名的《平淮西碑》。[13]原来朝廷为笼络吴少诚而敕建的德政碑重刻为《平淮西碑》,表明淮西地区重新归于中央统治。而紫极宫作为供奉李唐祖先老子的官方道观,改建吴少诚生祠为紫极宫的政治宣示意义不言而喻。景福元年(892),义胜军节度使董昌“准敕”,[14]“建生祠于越州,制度悉如禹庙,命民间祷赛者,无得之禹庙,皆之生祠”,[15]董昌还自言:“有飨者,我必醉。”[16]足见这些跋扈强藩充分利用敕建碑祠的形式,以自我造神,强化统治。朝廷为了笼络地方势力,常常批准建立,并任命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为他们撰写碑文。
吏民诣阙为藩镇或地方官请求碑祠的做法在五代时更多。马殷、韩逊、钱镠皆曾派人诣阙请建碑祠,都得到朱温的同意,并命人撰文立碑。[17]其背后都有着借助朝廷威名,援碑祠以自立的政治目的。而随着中央控制力的下降,民众为地方官请建碑祠,也绕过了道一级机构的文书呈请与监察考核流程,直接诣阙请求。如后梁的赵昶平定盗寇,劝课农桑,“陈、许将吏耆老录其功,诣阙以闻,天子嘉之,命文臣撰德政碑植于通衢,以旌其功”。[18]后周的白延遇显德元年(954)改任兖州防御使。“在兖二年,为政有闻,人甚安之,州民数百诣阙,乞立德政碑以颂其美”。[1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并非节度使的州县官似乎更加看重德政碑的价值,而不是生祠。这应当与德政碑形制高大,通常立于通衢大道,便于民众瞻仰有关。
在北宋建立之初,统治尚不稳固之时,延续前代的为节帅、观察使、防御使等颁授碑祠、命高官撰写碑文的做法应当是比较现实的选择。故在太祖朝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事例,如建雄军节度使杨廷璋在宋初加检校太尉,“吏民诣阙,请立碑颂功德,太祖命卢多逊撰文赐之”。[20]先后担任防御使和观察使的李汉超在齐州十七年,“为政简易,吏民信爱,尝诣阙请立碑颂德,诏太子率更令徐铉为之文”。[21]曾任殿前都指挥使的尹崇珂在宋初为淄州刺史,“有善政,民诣阙请刻石颂德,太祖命殿中侍御史李穆撰文赐之”。[22]随着宋廷强化中央集权措施的展开,朝廷在审核、批准和颁授碑祠事务中重新占据主动。除了颁布很多禁止吏民诣阙举留、请碑的法令外,更为关键的是,宋朝重建并强化了中唐时期道一级机构在举留请碑过程中的职能,后来逐渐固定为转运司等监司拥有此权。
太祖建隆元年(960)十月下诏:“诸道长贰有异政,众举留请立碑者,委参军验实以闻。”[23]规定诸道官员的善政须经过地方录事参军检验核实后上奏中央,不能经由吏民诣阙。建隆四年(963)颁布的《宋刑统》重申了《唐律疏议》中禁止长吏在任立碑的规定,若在任官员擅自立碑或者遣人申请立碑将受到严厉处罚。《宋刑统》实则是恢复了安史乱之前,官员必须离任才可请碑的原则。[24]乾德四年(966)六月颁布的诏书云:
国家以官得其人,治有异等,生民受赐,许列状以借留,政绩可嘉,听其事而称纪。近者吏民等奔走道路,直诣阙庭,既妨夺于民时,判离于职次。自今应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知州、通判、幕职州县官等,有政治居最,为众所推,愿纪丰碑,或乞留本任,并不得直诣阙上言,只仰具理状于不干系官吏处陈状,仍委即时以闻,当与详酌处分。[25]
朝廷首先申明允许吏民列状举留、建碑,但因为举留妨碍农业生产等原因,不得诣阙上言,必须经过“不干系官吏处陈状”才能奏闻。随着诸道(路)监司的陆续设立,这里的“不干系官吏”逐渐固定为监司官。景德元年(1004)六月的诏书曰:“自今百姓僧道,更不得辄诣阙庭,及经邻部举留官吏,如实有善政,候转运使到州即得举陈,仍委本使察访能否以闻。”[26]即民众举留陈状必须在转运使巡历到该州之时,而不得诣阙或经过邻近州县向转运使举陈。或可推测,在此诏令颁布之前转运使已经负有这一职能了。
转运使始置于乾德年间,“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是太祖收藩镇财权的一大措施。同时,转运使也负有监察之责,“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27]可见,朝廷把考察地方官吏的权限赋予转运使,由转运使来呈请举留官员的文书是符合制度规定的。景德元年以后,禁止民众诣阙举留、建祠立碑的诏令很少,或表明最晚至真宗景德以后已经建立起完善的举留陈状制度,诣阙举留或请碑行为都被压制在监司层级。大约在庆历年间,提刑司官员也承担了这一职责。[28]
乾德四年的诏令还提示我们,朝廷是将举留、请碑的做法一起约束的,则吏民请碑也同样需经由转运使、提刑官等监司官转奏朝廷。庆元年间,朝廷再次重申:“诸在任官,虽有政迹,诸军辄举留,及余人非遇察访监司所至而举留者,各杖一百。建祠立碑者,罪亦如之。”[29]可见,两宋对于官员必须离任才可举留、请碑的规定是一贯的。依据以上诏令,宋代吏民为官员立碑的申请流程大致是:官员离任—百姓向监司申请—监司上奏朝廷—朝廷“详酌处分”。虽然比唐代前期逐级申请、勘验、批准的流程略为简省,但对立碑的条件审查之严格则较为一致。
与朝廷对官员立碑的详细规定相比,我们没有看到宋廷颁布单独针对生祠的法令。前述庆元年间的敕令是仅有的提及生祠的记载,不过这也是附在官员举留的规定之后。宋代法律对立碑规定的严格细密与立生祠规定的粗疏,或许正好反映了朝廷对两种活动的实际态度。这在宋代众多的建祠立碑史料中也可得到支持。宋真宗朝以后的立碑活动被批准者极少,几乎完全禁止。如景德元年,吴元扆知定州考满,“定州民诣阙贡马,乞留知州吴元扆,并求立德政碑”。朝廷的做法是“命还其马,赐元扆,诏褒之”,[30]并未批准立碑。天禧元年(1017),曹玮因为抗击吐蕃有功,“秦州僧道百姓等以部署曹玮功状请立碑颂”。朝廷也只是下诏褒奖,拒绝批准立碑。[31]最典型的当是蔡襄的例子。嘉祐初年,蔡襄任泉州知州,因有惠政于民,“既去,闽人相率诣州,请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许谢,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32]这里透露出,真宗朝以后的请碑制度虽然存在,但实际上官府不再允许树立德政碑。民众将其善政“刻于石”只是树立私刻之碑,并非是由朝廷批准和颁授的德政碑。
相比于立碑之难,宋人立生祠则容易得多,而且我们极少看到完整的申请流程的记载。在笔者翻阅的大量史料中,只偶有提及民众向当地官司或监司申请而获批准的记载,并未见监司上奏朝廷的记录。如林安宅于绍兴十二年(1142)任新昌知县,有“改建学宫,置田养士,更修县治、坊郭、门巷、祠庙”等善政。他离任后,士民感其恩德,欲建生祠,即向县官“请祠于学”。[33]申请之后,士民即获准立生祠于县学。又如,程师孟的生祠是目前仅见的民众上请转运使的例子。元丰二年(1079)越州知州程师孟离任,“郡之衣冠、缁黄、耆艾之士若干人,乞留于部使者,三为之上,不报。因相与泣曰:‘公去矣,其像虽存于三老堂,然吾人之心未厌也。闻公尝帅洪、福、广三郡,三郡皆有生祠,岂越独无有?今宝林院者,公之所兴建也。若即其地为堂,立公之像,如三郡故事,以慰吾人之思,不亦可乎?’众曰:‘然。’于是又以状白使者,请立公之祠堂焉”。[34]这里的“部使者”“使者”均指监司官。据此,则士民为知州程师孟建立生祠需向监司官申请。下文就径直言:“今祠堂成有日矣,谋为记,宜莫如孙公者。”越州吏民打算请求孙觉为生祠堂撰写记文。这里未见监司官向朝廷申奏、朝廷对其政绩勘验等程序。《宋史·程师孟传》也记载:“(程师孟)发隐擿伏如神,得豪恶不逞跌宕者必痛惩艾之……洪、福、广、越为立生祠。”[35]则越州的生祠确然建立无疑。若联系到宋代监司权力之大,即使是死刑的详复权也已完全下放给提刑司行使,[36]则朝廷将立生祠的处理权下放给监司,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表明,相对于德政碑,宋廷对立生祠的管制要松弛得多。
那么,为何在宋真宗朝以后,朝廷放松了立生祠的管制而对于立德政碑依然严格呢?这一方面是北宋强化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德政碑和生祠的功能差异有关。随着宋太祖、太宗时期一系列的收回藩镇兵权财权、罢藩镇领支郡、命文官知州等集权和削藩措施,彻底剥夺了原来手握地方实权的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等存在的基础,使这些官职最终成为代表尊贵地位和优厚俸禄的虚衔,中央重新确立了对地方的完全掌控。与此相应的是,朝廷已无必要将颁授碑祠作为笼络地方的手段。德政碑和生祠都回归其作为政绩奖励方式的性质。但是由于德政碑在中唐五代以来更多的是作为地方藩镇和官员跋扈强权的象征而存在,正如仇鹿鸣指出,中晚唐河北地区的巨型碑志成为藩镇彰显权力合法性及形塑地方认同的工具。[37]而吸取了晚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中央卑弱教训的宋代统治者极其在意德政碑的这一历史影响。虽然宋初以来中央权威逐步重建,但是在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国家战略下,任何可能削弱中央权威的行为都需要高度警惕。故在宋真宗朝以后,德政碑基本不再批准颁授。
虽然生祠也曾在晚唐五代的地方割据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多是附属于德政碑而建立的。其单独发生作用的场合并不多。一旦碑祠不再由朝廷颁授,生祠也就失去了敕建的光环,基本回归悠久的先贤祭祀传统,其实际意义需要重新建构。生祠对于中央的威胁也大大减小。同时,朝廷还可以对生祠加以引导利用,允许给地方良吏建生祠,以树立一些榜样,使其他官员能够见贤思齐,这对于地方吏治与教化也不无裨益。总之,随着北宋初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调整,无论是作为中央笼络地方手段还是政绩奖励的碑祠颁授活动都走向了终结。申请德政碑的制度虽存,实际上已被禁止。而对于生祠,朝廷则放松管制,成为一种地方士民向监司、地方官申请或私自建立的纪念活动。宋代的德政碑之少与生祠之多,或许可以从此得到解释。[38]
二、宋真宗朝以降生祠的价值建构及其盛行
生祠管制的松弛,使得修建生祠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地方,成为一种地方事务。这为宋代生祠的盛行创造了条件。宋代士民也修建了少量的去思碑、遗爱碑、政绩碑等,不过绝大多数为生祠。[39]依据参与者数量多少和采取的方式,生祠可分为个人式的画像祠与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的画像(塑像)生祠。这两种形式并不相互排斥,很多时候是并存的。对于个人而言,由于画像的方式对地点(通常是家中)、成本要求不高,只需绘制官员画像即可进行祭祀,所以这一方式使用得相当广泛。如史籍中所记载的“比屋绘其象”“绘公像于家”等。民众集体为了表达对官员的感恩报德之情,会专门为其建立或另辟一室为祠堂,在祠堂内绘像或塑像,通常还有士人撰写生祠记文以树碑记事,便具备了表达民情民意的特质,形成了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的画像(塑像)生祠。[40]如韩琦任职地方时,“所历诸大镇皆有遗爱,人皆画像事之,独魏人于生祠为塑像,岁时瞻奠”。[41]文彦博晚年退居洛阳时,士民立其塑像于资胜院,“冠剑伟然,都人事之甚肃”,并邀请司马光撰写记文。[42]本文侧重探讨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的生祠。那么,在朝廷不再颁授碑祠的背景下,褪去了皇权光环的生祠何以能够比去思碑等更获得官民的青睐?随着朝廷管制的放松,建生祠难免出现官员邀誉、民众滥建的情况,这也引起了很多士人的批评。不过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无论建祠者是发自真心地怀思感戴,还是为了私利的谄媚之举,为何他们都认为立生祠是有价值的呢?换言之,不论每个人的动机如何,生祠这一“形式”本身所具有的、可以传达的价值是当时人所公认的。官民对此价值的认同和追求是促使其盛行的重要动力。以下我们将从地方民众和官员的角度分开论述。
(一)祈福与颂扬:地方民众建祠的追求
对民众来说,生祠的基本功能在于表达对良吏的怀思、感戴和报德。如张茂良所记:“桂人德公(指:赵崇模)之久,结恋不释,即无量寿佛宇西偏肖像建祠,寓其去思。”[43]吕南公所记:“官今去,我不能借而留之,盍图像以慰永远之思乎?”[44]相较于更加士大夫化的立碑记事,画像或塑像是普通民众所采用的最直接便利的一种形式,很适合表达怀念、去思的意义。如郑樵记述百姓的想法:“其意谓君(指:丘铎)之闻望名字,必书青史,君之行事,勒在民之心膂,口口承传,无有纪极。惟君之面,老壮幸及知,后来者无由识,作此祠所以识君之眉宇也。”[45]在表达怀思之上,就是对官员的报德。如范仲淹所说:“生祠,民报德也。”[46]不过树立去思碑也有报德的意义,生祠报德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呢?
一是体现在生祠具有为官员祈福祈寿的功能。生祠采用画像或塑像的方式,固然承自汉代以来“图形立庙”祭祀先贤的悠久传统,也很可能受到唐代寺观常常设立真堂(影堂)以供奉高僧大德、有功于寺观者或者祖先模式的影响。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批僧人和当地上层人士的邈真赞,其目的就是供家属、子孙、门人弟子祭奠瞻仰。[47]若联系到很多祠堂就设立在寺观中,则生祠借用这一形式也就不难理解了。画像或塑像的长处在于以直观的图像拉近了官员与民众的距离,便于民众在多种场合、时间进行奉祀、祷祝。所谓“吾何以永报公之德于无穷也?无亦绘而祠之,晨香夕灯,祝公千岁,而后尽于吾心”。[48]沈遘在杭州深受爱戴,民众“相与于山之巅,作为室堂,物色仪象,以揭示瞻仰,日颂公寿”。[49]有的生祠直接称为“寿祠”,祝词中也有“祝以眉寿,毋忘公恩”等语,其祈福祈寿的意义更加凸显。
二是体现在颂扬官员的美名以报德。扬名于天下以垂之久远是当时各个阶层所共享的价值追求。时人认为对官员的报德就是让他们的美名和功绩广泛传播、世代流传。民众的口碑流传固然重要,但随着时间流逝会逐渐淡化,如何使之固定化,成为一种留得住的记忆呢?刻石立碑是重要的方法。[50]士民通常会在绘像、塑像的同时,请人撰写生祠记文,镌刻入石,树立生祠碑,利用石碑的坚固性,使得良吏的名字“永垂不朽”。如绍定四年(1231)秋,广西经略安抚使赵崇模离任,当地人在无量寿佛寺为其肖像建祠,同时“犹以为未足,乃相与诵述善政,刻之水月洞石崖”,以达到“此石永存,德名不朽”的效果。[51]隆德府民众为感恩知府韩昭,一方面绘像生祠于佛寺,同时“谨采治绩之尤者刻诸石,俾子孙揄扬歌颂,兹无愧于桐乡矣”。[52]洛阳士民邀请司马光为文彦博生祠撰写记文,目的也是“书其事,著于石,以传告无穷”。[53]士民也期望利用撰写者的声望使得官员美名超出一时一地的范围,传播更广。所以他们通常会邀请一些知名的文人士大夫来撰写记文,为此不辞辛苦,多方联络。司马光、陆游、魏了翁、真德秀、程珌等都被人通过同乡、同年或友人等关系而获邀撰写。可见,较之于单纯的去思碑,生祠兼具了画像祠祈福祈寿与碑石纪功扬名两种功能,既满足了民众怀思、感戴善政官员的情感诉求,又能够充分发挥石碑的恒久性特征,记载官员德政,颂扬官员美名。其功能的互补性和全面性应是士民偏好选择生祠,以报答官员的重要原因。
那么,宋代官员是如何看待生祠立碑带给他们的美名呢?这一美名的意义何在?
(二)循吏的重要象征:对官员的意义
首先,民众为其建祠立碑意味着百姓对官员治理的认可,而在帝制时代的官僚文化中,对官员治理的认可通常会和循吏传统联系在一起。士大夫认为生祠应当准确地表达民众对官员的感戴怀思而不应当是阿谀滥建。周子岩就批评道:“生祠之建,为令尹政教美也。乡校议政,其善固宜祠,况善教乎?俗薄伪胜,无问贤否,率立之祠……信如是,祠奚益?”[54]那么如何保证官员的治理政绩与民众绘像建祠的做法是“名实相副”呢?他们认为“士心”“公论”是最值得信赖的。只有经过“士心”“公论”的评判,生祠才是名副其实,官员才是真正的贤达。而这种贤达就是循吏。如姚勉所言:“夫为政,以得人心为本,然而得吏心易,得军心难;得军心易,得民心难;得民心易,得士心难。得吏心者最下,吏可为奸耳。得军民心者次之,谓犹可以惠致。士心镜善恶,口衔臧否,不可威怵利诱,众论所归谓之公。是至难得者士心。君之生立祠也,士率民为之,信贤已。其贤何?若无可纪而实可纪,如古循吏也。”[55]在姚勉看来,士心不同于吏人、军人和民众之心,士人不可“威怵利诱”,因为是众论所归,所以士人议论就代表着公论。因此得之最难。陈知县的生祠是经过了士人的认可,由士人带领民众所立,故证明陈知县是真正的“贤”。这种“贤”就像是古代的循吏。如此一般论证,就把被立生祠的官员和循吏等同起来。也就是说,生祠成为循吏的重要象征。又如陈居仁也曾在多地为官,“历典数郡,率乘旱歉匮乏,公悉心措画,责成其下,人乐宣力,政事日修,财用自足,宽严适中,号称循吏”。周必大还将“所至皆立生祠”作为循吏的标志记下来。[56]
在士大夫撰写的生祠记文中,这些德政官员基本上遵循孔孟所议论的“先富后教”的理政次序。[57]士大夫经常将他们比作遵循“先富后教”的汉代循吏文翁、龚遂、黄霸、卓茂等。绍定年间,蓝山知县赵汝瞻的施政便具有代表性。黄梦清记载:
下车之初,首谒先圣,慨学校之废缺;涤龟之始,咨讽利病,叹民生之孔艰。若曰:吾不先有以纾其力,则救死不赡,奚暇礼义?由是条昔日横科之目,闻于台府,一切蠲而汰之;必不得罢者,则蠲俸以代偿。民力稍苏矣,而爱民之心犹未已也。虑溪峒之有以寇吾民之积也,则置总辖以训齐之,虑屠牛之有以妨吾民之耕也,则严法令以禁戢之。岁比小歉,则务劝分,而家以给足……而公之意犹以为富而不教,民犹昏昏也,乃询谋于邑人士,大治学宫之役。自大成殿、两庑、棂星门、明伦堂,下至庖湢,或饰旧,或增新,秩然有序,焕然有章……而公之意则以为,士固不可无教,而尤不可无养,于是请开田六十七亩于郡,复括逃绝产百二十五亩,及市官估之业一百十九亩有奇以益之。民不困累,而知生之乐;士无苟营,而惟道之谋。其有造于兹土,大矣远矣![58]
从蠲免横征的赋税,到保证农业生产、劝分赈济,都属于富民的措施。之后的修缮学宫,是为教士之举;增加学宫经费,则是养士之举。这些措施完全符合“先富后教”的次序。所以黄梦清在文末赞扬赵汝瞻为“循吏”,并认为其有可能名留青史。这样的形象不只是赵汝瞻一人。沈遘、[59]葛洪、[60]吴机、[61]赵汝廪[62]等都被塑造成“先富后教”的循吏形象。
其次,我们需要考虑循吏的美名对于官员自身有怎样的意义。最现实的意义是有可能得到府州长官或监司的举荐而升任。如昌国知县葛洪因为有听讼明辨曲直,制止胥吏奸欺,规范赋税,修缮学宫等善政,“两受郡侯荐墨……列台状其政于朝”。[63]不过对于监司官而言,分辨生祠究竟是出于民众的真心感戴而建立,还是受到驱迫而建立,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故监司官对这些做法的虚伪性较为警惕,他们往往会依据官员的考课而举荐官员,不仅仅只关注被立生祠一事。
虽然生祠对于官员仕途升迁的直接助益有限,但借助于生祠碑文的记载和传播,官员的政绩有可能超越一时一地的范围,传播得更广。这有助于官员提高个人声望,建立更加广阔的人际网络。对身处官多缺少、升迁难度较大的宋朝官员来说,仍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如赵尚宽在唐州任职五年,政绩卓著,民众为其立生祠。王安石、苏轼分别作《新田诗》《新渠诗》赠送给他。王安石特别指出:“循吏之无称于世久矣,予闻赵君如此,故为作诗。”[64]之后赵尚宽声望大增,顺利迁转,或许与此不无关系。
此外,生祠对于官员的循吏身份塑造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宋代士人的传记书写中,立生祠通常会作为褒扬官员政绩的重要方面而被郑重地写入神道碑、墓志铭和行状中,构成其身后的荣耀。如舒亶为罗适撰写的墓志铭道:“所至称治,去则人思之,多为立生祠,而论者以谓有古循吏之风。”[65]苏辙为欧阳修撰写的神道碑言:“公前后历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宽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扬之人,至为立生祠。”[66]楼钥所撰赵善誉墓志铭也载:“去邑五年,人相与立生祠于县治,邑宰陆侃之记可考也。”[67]而这一“历史书写”也可能进入本朝国史甚至正史,固定为士人的后世形象。如苏轼、胡宿、韩琦等人《宋史》本传中“立生祠”的记载都来源于其本人的行状或墓志铭。
当然,循吏身份塑造的最高境界则是进入本朝国史或正史《循吏传》。不少生祠记文都会提到:“引考条列,传信其后,以待史氏之捃摭。”[68]黄梦清撰写的记文就言:“三代而下,直道亦自在人,异时必有龙门兰台,大书循良,以诏来叶,岂直泐之贞珉而已哉。”[69]揭示出从生祠留名到青史留名的追求。宋朝的国史《循吏传》今已不可见,但是《宋史·循吏传》主要取材于宋朝的国史《循吏传》。[70]我们以《宋史·循吏传》为例,也可见生祠立碑对于正史记载的影响。如张纶在江淮发运副使任上的德政记载,如治理盐场、修漕河堤、筑捍海堰等,全部来源于范仲淹为其撰写的《泰州张侯祠堂颂》。《宋史·循吏传》中对程师孟施政风格的概括直接源自秦观为其所撰写的生祠记文。其他被列入《循吏传》的官员中,至少两人的传记将民众立生祠视为其循吏身份的重要事件来记载。如赵尚宽“留于唐凡五年,民像以祠”。[71]高赋根除衢州巫蛊之患,招募流民,继续增加唐州的田地、户口,“两州为生立祠”。[72]由于元人修纂《宋史》过于仓促,缺漏之处很多,列入《循吏传》的十二人都是北宋人,南宋竟无一例。但是仅此四例已可见生祠立碑对于官员循吏身份塑造的重要意义。
自汉代以降,循吏的美名都是士大夫的价值追求,不过在宋代独特的政治环境中,循吏这一美名则更为重要和迫切。宋代的士大夫真正成为政治主体,他们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积极谋求在朝则美政,在乡则美俗的社会实践。忠厚循谨、积极推行教化的官员成为朝廷树立的典范。受此政风影响,士大夫特别重视循吏的美名。而经过他们的阐释,生祠成为循吏的重要象征。建祠立碑对于提高官员声望、塑造循吏身份形象具有重要价值。官民对这一价值的认同和追求推动了宋代生祠的兴盛。
三、地方士民的利益诉求与生祠的修建
除了官民对生祠内在价值的认同和追求外,我们还需思考的是,这种地方士民广泛参与、祭祀对象主要是州县官、生祠碑文也是由地方官或者士人撰写的颂扬活动,对于具体的某个“地方”有着怎样的意义?地方豪横奉承官员以谋取私利固然是个别生祠建立的原因,[73]但除此之外,地方士民是否也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感戴报答(奉承)官员之外,他们有可能主动运用生祠立碑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首先,生祠立碑成为地方士民评价官员施政效果的载体。与唐代不同,宋代官员的考课很大程度上系之于监司。而监司对于官员的考课评价与地方士民对官员的评价有时候并不一致。当这两者严重不一致之时,就会发生冲突。民众的做法就是举留,举留不成功则建祠立碑,以表达不同于官方的态度和评价。这在南宋绍兴年间,衡州士民为知府向子忞建祠立碑上体现得很明显。
绍兴五年(1135),向子忞知衡州。他赴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蠹害衡州的湖南提刑司的属官逮捕治罪,之后派人籴米于丰稔之州,救济大量饥民。但是他的做法得罪了提刑官。所以荆湖南路的监司官一起向朝廷劾奏其“以酷刑失民心”,向子忞很快被罢免。次年正月,向子忞被授宫观官,“士民相与群聚击鼓于提刑司,愿举留,鼓为之裂。提刑惶惧,夜半登舟出巡以避之”。[74]不仅如此,衡州士民还“犯雨雪泣涕属道而送,其能远者,众资之,使谒诸朝”。但是民众的力量毕竟微弱,朝廷“久而未报”,民众就在城北青草寺绘像建祠,“岁时合笳吹鼓舞其下,以祈侯寿考而思其来也”。[75]可知,士民以为向子忞建生祠的方式表达对朝廷处置的不满,有抗议朝廷不公之意。直到四年后,在胡寅等人的呼吁下,御史官员上章论奏,朝廷下旨改正,任命向子忞为荆湖北路提点刑狱,此事才算得到了相对公正的处理。士民遂邀请胡寅撰写碑记文,立于生祠旁,“并刻御史章于碑阴,至今存焉。皆公出后所立,非有使之者”。[76]这里的“非有使之者”当是指向子忞的生祠是民众私自树立的,并非出于他人的驱迫或奉承所为。民众在向子忞复职后才立碑,记录下了民众抗争朝廷不公的全过程,颇有“纪念碑”的意味。虽然此事的很多细节已不清楚,我们仍可以看出,民众通过建祠立碑的形式以表达对地方政治的意见,也蕴含着对官员施政做出不同于朝廷的“地方”评价的意义。
士民不仅建祠立碑以彰显良吏的善政,有时也把恶吏的恶政写在碑记之上,使得善者永远被人怀念感恩,恶者永远被人唾弃。通过这种褒善贬恶的方式劝诫后世的官员。姚勉就说他撰写生祠记文采用了《春秋》笔法,虽然没有明确记录有恶政的临江县令的姓名,“读是记者,必皆知其为某。使某人得此记读之,亦将颒然赧而雨然汗也”。他认为建立陈侯的生祠“不独可以劝戒天下吏,又可以为此令劝戒矣”。[77]
因为建祠立碑有着如此重要的褒善贬恶的道德评价意义,为了维护其权威性,立碑的时间就成为关键问题。如果选择官员在任时立碑,不仅有违法律规定,也可能成为地方官和豪民相互勾结,共谋私利的行为,从而损害了建祠立碑的“公议”功能,丧失其道德评价的意义。所以最好的时机是在官员离任之后。这样可以避开以上干扰,尽量反映地方士民的真实评价。[78]
其次,士民通过建祠立碑的形式把各种善政措施固定化,以维护自身利益。地方士民一方面感戴良吏的惠政,另一方面也会因良吏的离任而遗憾。他们忧虑良吏的善政会因为官员去任而改变。吕午就记下了徽州民众的忧虑:“既有私忧过计者,叹曰:‘公政声洋洋,行归天朝,岂容久私其惠于吾镇?使来者能继贤躅,幸甚,否则未保其往也。’”[79]地方士民之所以有建祠树碑、撰写记文的强烈愿望,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将官员的善政措施形之文字,刻于碑石,使之成为既定的规范,对后任者施加某种约束。尽管其实际效果或许并不显著,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的确是民众热衷建祠立碑的重要原因。如淳熙十二年(1185),资政殿大学士李公奏请削减义乌县每年上供的酒税额,并蠲免数年来逋欠的酒税。民众感恩戴德,为其立生祠。县尉赵师日在写给陈亮的信中说:“公之盛德在民为甚深……师日在邑僚之底而获于大惠,不勒其事于石,乌保异时之额不增,非所以相我公之惠于无穷也。愿属笔于吾子,以谂来者。”[80]开禧年间,在殿中侍御史叶时的奏请下,朝廷蠲免了华亭县四个乡的部分酒税及逋欠税额,民众为其立生祠于县学。华亭县宰汪立中在邀请楼钥撰写记文的信中陈述了必须立碑的原因:“天假之幸,有此际会,且蒙俯察其来已久,非今日之罪,略其前日不得已之过,而禁其将来,可谓曲当矣……立中深恐后人不知其详,愿书而登之石。”[81]宾阳父老不远千里来到桂林,邀请秦祥发为广西经略赵师恕撰写生碑记。他们说道:“吾邦之人,比遭前守之虐,俱不聊生。今兹获遂生理,大帅赵公之赐也。请识之,归镵于石,以示不忘,且为后来贪毒者戒。”[82]足见建祠树碑对当地民众具有的现实意义。所以,一旦发生后任官员改变惠政措施的行为,就会引发对前任良吏的怀念,极易形成诉求共识和舆论氛围。
总之,宋代生祠的总体价值在于形成了一个地方官民、各方势力都能参与其中,且都能各取所愿的持久性的利益获取、道德实践模式。这一模式的确立让本来仅仅服务于死后不朽、宣扬德行的载体(祠堂),变成服务于当下各种情感与道德需求、利益诉求的新传统,让更多的人觉得“有利可图”,有必要积极参与其中。故生祠立碑的模式,在之后的历史时期也得到延续。
结 语
宋代的碑祠修建活动可分成两个阶段来认识。北宋建立之初,继承中唐以来的传统,采取朝廷颁授、高官撰文的模式。而随着太祖、太宗两朝一系列集权和削藩措施的实施,中央的掌控得到恢复和强化,原来握有地方实权的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等官职成为虚衔。与之相伴的是,由朝廷颁授碑祠以笼络地方的做法走向终结。真宗景德之后,申请德政碑的制度虽然保留,但实际上不再批准。同时,朝廷放松了对生祠的管制。这一改变使得生祠修建的主动权转移到地方,使之成为一种地方事务,从而为生祠的盛行提供了条件。
在可供民众选择的表达感戴的方式中,生祠因其兼具为官员祈福祈寿与颂扬美名的功能而受到民众的偏爱。对于官员来说,被立生祠成为循吏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在当世士大夫群体中提高个人声望,建立广泛的人际网络,还是对于官员循吏身份塑造,建祠立碑都是其道德实践得到认可的标志,最终固化为一种永久性荣耀,故受到其推崇。官民对于生祠内在价值的认同与追求是促使其兴盛的重要动力。地方士民也期望通过生祠修建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使之成为评价官员施政的载体。他们把善政措施以镌刻立碑的形式固定化,以维护自身利益。地方士民对这一形式的主动运用也推动了生祠立碑的扩展。相对于庞大的国家机器而言,生祠立碑作为表达民情民意的一种方式,其效果是因地、因时而异的,但仍然让我们看到了统一国家之下的地方社会的面相。
作者简介:韩冠群,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史。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宋代江南地区先贤祠研究”(2019ELS013)的阶段性成果。
[1]宋人所建生祠的具体数量已不可考,笔者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检索“生祠”“立祠”“画像”“绘像”等词汇,宋代的数量就多达几百例,远多于刘馨珺所搜集的唐代114例建祠立碑。而在唐代这114例建祠立碑中,立碑占多数,生祠比较少。再比较唐宋留存的生碑记文数量也可知宋代生祠远多于唐代。本文搜集到宋代生碑记文共有77篇,其中题为“生祠”记文的有71篇,标题为“德政碑”“遗爱碑”“去思碑”的记文共有6篇(这6篇的标题有可能是后人所改),生祠记文占据绝对优势。刘馨珺收集到唐代生碑记文共30篇,其中题为“生祠”记文的只有2篇。这固然与留存至今的宋代文献比唐代多有关系,但是仍然反映了宋代立生祠的普遍性。唐代数据,参见刘馨珺:《从唐代“生祠立碑”论地方信息法制化》,《法制史研究》第15期,2009年。本文搜集的宋代生碑记文目录参考了刘馨珺的“目前所见宋代生祠立碑文简表”,并做了增删。参见刘馨珺:《“唐律”与宋代法文化》,嘉义大学2010年版,第166-171页。
[2]日本学者长部和雄早在1945年发表《支那生祠小考》(《东洋史研究》第9卷第4号),简要讨论了生祠的起源、发展、虚伪性等问题。此后直到2004年,生祠问题才被再次关注。雷闻从唐代地方祠祀分层的角度考察了生祠的概况、立祠程序、祭祀功能等问题(《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和城隍神为中心》,《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刘馨珺从考课的角度分别对唐宋两代的生祠立碑制度及内容做了研究。唐代部分见其《从唐代“生祠立碑”论地方信息法制化》(《法制史研究》第15期,2009年),宋代部分见其《“唐律”与宋代法文化》一书,第85-96、136-171页。仇鹿鸣将德政碑视为“王朝理想政治秩序的象征”,重点分析其在唐后期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运作中的角色,这对于生祠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111页。增订后收入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4-173页)。李怡梅对南宋东南地区生祠的概况、修建原因、申请程序、场所、参与者及所反映的社会特征等做了论述。唯其关注时段为南宋,并未对生祠兴盛的制度背景、价值建构、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深入探讨(《南宋东南地区生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9年)。
[3]刘馨珺:《从唐代“生祠立碑”论地方信息法制化》,《法制史研究》第15期,2009年。
[4]李怡梅:《南宋东南地区生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9年,第20-33页。
[5]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一一《职制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7页。
[6] (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四,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0页。
[7]杨俊峰:《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以国家和南方祀神之风互动为焦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8]《旧唐书》卷一五八《郑余庆传附子浣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67页。
[9]雷闻:《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和城隍神为中心》,《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0]碑文载:“大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刘君之德,诣县请金石刻之。县令以状申于府,府以状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谨桉天宝诏书,凡以政绩将立碑者,其具所纪之文上尚书考功。有司考其词宜有纪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诏曰:可。”参见《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二《高陵县令刘君遗爱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页。
[11]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第161页。
[12]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四四《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32页。
[13] (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第2册,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2页。
[14] (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三《唐敕建董昌生祠题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15]《资治通鉴》卷二五九,乾宁元年十二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460页。
[16]《新唐书》卷二二五下《董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467页。
[17] (宋)王钦若等编,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八二○,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9547页。
[18]《旧五代史》卷一四《赵犨传附昶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6页。
[19]《旧五代史》卷一二四《白延遇传》,第1634页。
[20]《宋史》卷二五五《杨廷璋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904页。
[2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一月庚午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85页。
[22]《宋史》卷二五九《尹崇珂传》,第9001页。
[23]《宋史》卷一《太祖本纪》,第7页。
[24] (宋)窦仪等撰:《宋刑统》卷一一《职制律·长吏立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196页。
[25]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八《禁纪碑留任不得诣阙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0页。
[26]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六月丙辰条,第1238页。
[27]《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第3964页。
[28]《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七载:庆历六年十二月四日,“臣僚上言:益州路州县,乞今后诸色人不得远诣转运、提刑司举留官员,候逐司巡历到处陈状。从之。”参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98页。
[29] (宋)谢深甫编:《庆元条法事类》卷八○《杂门·职制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25页。
[30]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三月乙酉条,第1232页。
[3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天禧元年六月癸巳条,第2071页。
[32]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三五《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21页。
[33] (明)田琯修:万历《新昌县志》卷九《名宦》,廖鹭芬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4年。
[34] (宋)秦观:《淮海集笺注》后集卷六《越州请立程给事祠堂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4页。按:这篇文字的篇名似乎有误。从文意来看,秦观所写的明明是代孙觉为程师孟生祠堂撰写的生祠记文初稿,而不是上请的状。
[35]《宋史》卷四二六《程师孟传》,第12705页。
[36]郭东旭、陈玉忠:《宋代刑事复审制度考评》,《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37]仇鹿鸣:《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38]刘馨珺认为宋代的碑祠仍需向朝廷申请方可建立,并未认识到生祠管制的松弛。故她只是从民众祈福的角度来解释生祠的兴盛,似乎尚有不足。参见刘馨珺:《“唐律”与宋代法文化》,第92页。
[39]这里使用“去思碑”“遗爱碑”之名,而不用“德政碑”,是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德政碑必须得到朝廷批准方可建立,而这种碑在宋初以后即消失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宋廷放松生祠的管制,是否会出现地方官效仿晚唐五代的跋扈节帅,利用生祠神化自我、强化地方统治的情况?这种情况实际上不可能发生。首先,宋代民众所建的生祠只是民众私建或者向地方官申请,并不具备朝廷颁授、皇帝敕立的荣耀,也不具备神化的潜质。最根本原因在于北宋初之后的中央集权已经彻底铲除藩镇割据存在的基础,官员均为流官,须严格遵守任满即替制度。官员离任后方才建祠,也没有强化地方统治的可能。
[40]需指出的是,生祠修建后所立的碑不是德政碑,而是生祠碑。考虑到朝廷严禁吏民建立德政碑,故生祠立碑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德政碑的部分功能吸收了进去。
[41] (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中集卷四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450册第581页。
[42] (宋)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5页。
[43] (宋)张茂良:《广西经略显谟赵公德政之颂》,(清)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卷一二,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44] (宋)吕南公:《灌园集》卷一六《庐陵徐俊和画像赞并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3册第156页。
[45] (宋)郑樵:《邑令尹丘君铎生祠记》,弘治《兴化府志》卷二九《礼纪十五》,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75页。
[46] (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卷八《泰州张侯祠堂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47]郑炳林:《敦煌写本邈真赞所见真堂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宋)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一七《益国赵公生祠记》,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87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219页。
[49] (宋)陈舜俞:《都官集》卷八《杭州知府沈公生祠堂德政记》,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13册,第140页。
[50]如秦祥发记载桂林父老的想法:“公之德识于人心者,固自不可泯,而识于坚珉者,抑亦不可缺。无其事则为诞,有其实不为谀。虽大书特书,不以为过。”参见(宋)秦祥发:《广西经略安抚焕章赵郎中德政碑》,(清)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卷一二,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4册,第290页。
[51] (宋)张茂良:《广西经略显谟赵公德政之颂》,(清)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卷一二,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4册,第289页。
[52] (宋)吴景修:《隆德府知府韩公生祠记》,弘治《潞州志》卷七,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53] (宋)司马光撰,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六《竚瞻堂记》,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08页。
[54]周子岩:《贤尹张公生祠记》,宗源瀚等修:同治《湖州府志》卷五二《金石略七》,《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四号》,成文出版社1966年版,第982页。
[55] (宋)姚勉著,曹诣珍、陈伟文校点:《姚勉集》卷三三《新昌陈知县生祠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75页。
[56] (宋)周必大著,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卷六四《平园续稿·神道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950页。
[57]于柔在《耿侍郎生祠记》就写道:“儒者之政,要在行其所学,行之固有大小,而讲学之序未尝不一。冉求以政事名孔门,盖有得于适卫问答数语,故富而后教,其序则然。”参见徐士瀛等修:民国《新登县志》卷七,《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影印本,1993年,第47册第112页。余英时对循吏的特点有深入探讨,参见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129-216页。
[58] (宋)黄梦清:《知县赵汝瞻德政生祠碑》,嘉靖《衡州府志》卷八《艺文》,廖鹭芬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59] (宋)沈绅:《越帅沈公生祠堂记》,邹志方点校:《会稽掇英总集》卷一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
[60] (宋)楼镛:《葛洪生祠记》,(元)冯福京修、(元)郭荐纂:《大德昌国州图志》卷六,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第6097页。
[61] (宋)丁宗魏:《吴知州生祠记》,隆庆《仪真县志》卷一四《艺文考》,廖鹭芬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62] (宋)韩伯巽:《社仓祠记》,万历《重庆府志》卷七八,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46册,第185页。
[63] (宋)楼镛:《葛洪生祠记》,(元)冯福京修、(元)郭荐纂:《大德昌国州图志》卷六,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第6098页。
[64] (宋)王安石著,秦克、巩军标点:《王安石全集》卷三六《新田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65] (宋)舒亶:《舒懒堂诗文存》卷三《宋故上护军致政罗公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6册第621页。
[66] (宋)苏辙:《栾城后集》卷二三《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2页。
[67] (宋)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一○八《朝奉郎主管云台观赵公墓志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0页。
[68] (宋)陈舜俞:《都官集》卷八《杭州知府沈公生祠堂德政记》,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13册,第140页。
[69] (宋)黄梦清:《知县赵汝瞻德政生祠碑》,嘉靖《衡州府志》卷八《艺文》,廖鹭芬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70]燕永成:《〈宋史·循吏传〉探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71]《宋史》卷四二六《赵尚宽传》,第12702页。
[72]《宋史》卷四二六《高赋传》,第12703页。
[73]南宋官员判词中就指出,举留之人就是“平日之把持道者也”,他们“取悦知县为干预公事之地”。可知,这些举留官员的人本来就是当地的豪横,在当地有很大影响力,他们借举留官员来取悦知县,以便进一步干预当地事务。参见(明)张四维辑:《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二《官吏门·举留生祠立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1页。
[74] (宋)王庭珪:《卢溪先生文集》卷四七《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阁向公行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34册,第731页。
[75] (宋)胡寅:《斐然集》卷二○《前知衡州向公生祠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18页。
[76] (宋)王庭珪:《卢溪先生文集》卷四七《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阁向公行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34册,第731页。
[77] (宋)姚勉著,曹诣珍、陈伟文校点:《姚勉集》卷三六《临江陈侯生祠记》,第404页。
[78]如姚勉《高安洪侯生祠记》指出:“有仕于此者,捐帑藏为继富之政,以媚豪民,豪民亦或为之祠以媚。去未几,而祠即废,上下之交媚者胥伪也:今是祠也,不作于侯在高安之日,而作于去高安一年之后,欢然攻成,不戒以孚,夫岂有所媚而为之哉,是可以言遗爱矣……去思也。”参见(宋)姚勉著,曹诣珍、陈伟文校点:《姚勉集》卷三三《高安洪侯生祠记》,第374页。
[79] (宋)吕午:《竹坡类稿》卷二《徽守刘寺丞生祠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9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页。
[80] (宋)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卷二五《义乌县减酒额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7页。
[81] (宋)楼钥:《华亭县南四乡记》,(元)徐硕撰:《至元嘉禾志》卷二一《碑碣》,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4569页。
[82] (宋)秦祥发:《广西经略安抚焕章赵郎中德政碑》,(清)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卷一二,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4册,第290页。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