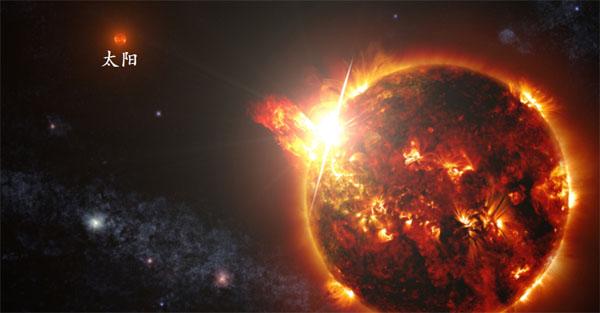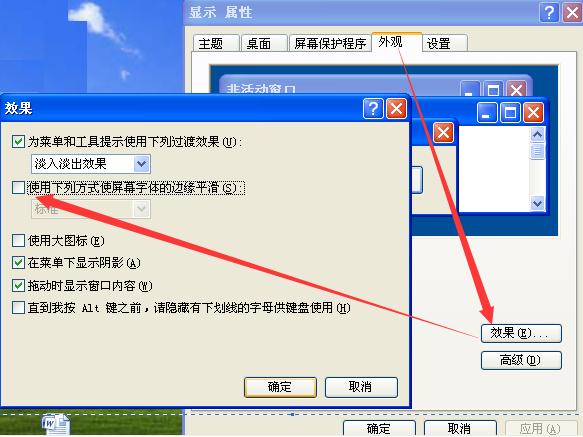太行山山下的农民(在希望的田野上)
文/高金业

我的老家在胶东的海边,离海也就四五里路,村子周围是庄稼地,没有山,要去山里,需要向南,得走很远的路。老家人多地少,40年前,煤炭是计划供应的,又没有山柴可用,对于平原地里的庄户人家来说,烧柴是一件挺要紧的事情。
是的,人要吃饭,做饭需要柴禾,热猪食、鸡食也要柴禾,就连冬日里取暖,也是需要的。人不吃饭没力气干活,猪和鸡冬天里总吃凉食要拉肚子,不长肉,闹不好还会死掉。
人要挣工分挣口粮,鸡要下蛋,猪要卖钱。那时的农民,有着自个的盘算,走路有使不坏的腿,路远不要紧,多费些腿力就是。穿衣也不打紧,大人孩子倒腾着改改,凑合着冻不坏就成。吃食不行,要做熟,生东西吃多了容易生病。
麦子熟了,别处是割麦子,老家那儿是拔麦子。麦根是很好的烧柴,落在地里可惜了。拔麦子是个苦活,一天下来手都握不死。麦子上了场,铡掉麦根,脱了粒,分出麦秸和麦糠。选洁净的麦秸卖给造纸厂,剩下的麦秸、麦根和麦糠就分给了社员,作为柴禾。
“分草了!下工后拿走啊!”等堆好了堆,看看差不多,保管便用破锣嗓子招呼着。于是场院热闹起来,用小车的,用扁担的,吆喝着、咋呼着,将一堆堆分好了的麦秸麦根捆好,运回家里。“让让啊,让让!碰着了!”一路上,只见草捆不见人的手推车慢慢向各家挪动着,好似爬行着的大草虫。老人们孩子们跟在车子后面,不时地拾着掉下来的桔草。
各家都有自己的草园,把麦秸麦根分开垛了。麦秸垛是圆的,远远看去如同一个个的蘑菇。
每逢此时,草堆得差不多了,父亲就用个梯子,爬到草垛上面,一边用脚踩实,一边让我用木杈往上扔麦秸。接过草,父亲一层层摞好、压实,围成圆形,上面堆成帽子,以利雨水淌下。见父亲高高站在草垛上,汗水在太阳的灸烤下湿透了白褂子,便有些心疼,想让他下来,我上去替他一会,但父亲不肯。我明白,他是不放心,怕我垛不好草,草垛倒了要重新再垛。还有,庄户人家的脸面没处放,许多的脸面里,草垛也是一个。

父亲垛的草垛好看且结实,拿草时无论怎么抽,草垛都不会倒。小时候,经常会与伙伴们一起,在草垛上掏个洞,躲在里边玩。
麦草发暄,最不搁烧,常常地一篓子草做不熟一顿饭。但它烧的灰多,用来做圈肥非常好。
农家主妇们喜欢的还是秋庄稼。
像麦子一样,玉米熟了,人们也不用镰刀,用小镢头将把整棵的玉米从地里刨出来,去掉土,再用铡刀将根用铡掉,一部分玉米杆留下来供生产队的牲口吃,剩下来的,连同玉米根一起,分给各家各户。玉米根结实搁烧,谁都喜欢要。还有玉米棒,剥掉粒,剩下的玉米芯也是好烧柴。
仅靠队上分的柴禾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拾柴禾便成了孩子们一件经常要做的事情。我和姐姐们自然也不例外。
有言道:南跑北奔,不如拾草攒粪。秋收过后,麦子种上,农活少了。我们背上篓子,拿上绳子,开始拾草。
天高气爽,空气里泛着清新,秋虫鸣叫着,旷阔的田野里飘着泥土的味道。
守在路边的地头上,那里有生产队马车往回拉玉米秸。玉米收割后,一捆一捆的玉米杆先是被扛到了地头,簇在一处。麦子种好后,劳力们有了空,才开始往场院上运它们。路不平,马车晃动,就有散落下的秸子,三三两两,立刻被我们拾起来,捆在一起。

还会有一些遗落的玉米根,被犁翻起,在麦田里或隐或现裸露。用抓钩将其钩出来,把土打净。这活计有些费力气,玉米根上的土不容易去掉,刚从土里刨出来又有些湿,装满一篓子背回去便显得吃力。
很快的,玉米根也被人们拾得差不多了。
秋风刮起,天气变凉,草也枯了。沟里、道旁、河滩上,有草的地方就有孩子。用铁耙,铁耙齿不容易断。很快地,篓子便会搂满。这种草也不耐烧,但可以当柴火引子。
霜降过后,树叶黄了,经过霜打的树叶被风一吹,纷纷扬扬飘落下来。公路上杨树叶最多,天不亮,赶紧起来,去公路上占地场,抢那夜里落下的叶子,或扫或搂或捡。有小孩子用长长的粗铁丝做成通条,磨上尖,去串地上的叶子,一捅串上一个,再一捅又一个,不一会通条上就串满了树叶,黄黄的,像一只巨大的黄豆虫。篓子里的叶子带着露水,踩结实了,显得有些沉,背回家,倒出来亮晒。大队的果园里,有果树叶子,苹果、梨、桃子,落下后,现着不同的颜色和形状。园子里不让人进,得偷偷去。瞅个空子钻进去,选那树坑边和低洼处,被风旋到一起的叶子,赶紧往口袋里胡拉几下,然后快速撤退。
那几日,院子里、草园里,到处堆积着我和姐姐拾回来的树叶,在秋风和艳阳下散发着特有的苦涩味道。秋干气燥,不用几日,树叶卷起,很快地干了。果树叶子可以喂猪,粉碎了,放缸里发酵好,作为猪的粗饲料。杨树叶多数人家用来做饭,也有用来喂猪的,但味道太苦,猪不愿吃。
时间不长,各家草园变魔术似地很快堆起了各式草垛,望着这一堆堆的烧柴,忙了一年的人们这才觉得心里有了底。
胶冬的冬天来得早,过了小雪,北风一刮,水面就有了冰碴。潮湿的海风开始吼叫,扑向阻挡它去路的一切。连阴几天,雪便肆无忌惮飘扬起来,鸟儿归了巢,路上少有行人。窗户上有了冰花,地渐渐冻得邦硬。农活没法干,猫冬开始了。
猫冬也要柴火,忙惯了的妇女们,白天做女红编小辫织渔网,家里要伸得出手。夜里睡觉钻被窝,炕上没点暖和气也不行。灶间做饭的火通过炕道,余烟顺房顶的烟囱冒出,土炕上会留下一丝热气。数九寒天,仅凭这点热量是不够的,还要烧炕,在炕洞里填上些麦糠,麦糠是阴火,熄得慢。老家人称之为盎炕,此称呼缘何而来,未细考。
不定时地,会做上一锅兑了菜的玉米饼子,锅底里煮上地瓜,篦子上蒸了饼子,放一大碗瓜唧咸菜,一碗小咸鱼。屋子里暖意融融,一家人逮着甜甜的地瓜,嚼着香香的饼子,就着咸鱼瓜唧咸菜,消磨着冬日里难得的空闲时光。
大雪封门,出不去门,家家围坐在热炕头,俗语曰“三九四九合家死虬”。忙针线活的,说古论今的,打扑克下棋的,各显其能。烧柴这时派上了用场,灶膛内生火,锅里烧上水,把那烧酒热了。炕洞里加些柴,人们就挤在一个炕上。炕上小桌摆一个火盆,火盆里木炭或玉米棒烧得红红的。女人们边拉着家常说东家道西家,边忙着手里的活计。喜欢酒的男人们,坐在热炕头上,弄一两个小菜,喝上几杯地瓜干兑来的老白干,晕乎乎炕头一歪,扎扎实实睡一个好觉。
那时侯没有煤与电,烧柴完全拜土地所赐。所有的植物,除了能吃的和能用的,其余皆送入灶膛。那灶膛和炕洞如同贪婪的巨兽,放肆地吞噬着成堆的柴禾。
炕席下垫上了厚厚的麦草,既暖和又防潮。人们的嘎鞑鞋毡靴中也放了麦草。麦草随处可见,碎了就换,实用得很。
转眼阴历年就到,家家户户开始忙年。这时候烧柴用得最多,大煮锅要用硬火,把一段段的树枝架起来放到锅底,让它慢慢阴着烧,小火,锅里的猪下货和鸡才能煮得透烂,打出的肉冻才能琥珀般又硬又亮。大饽饽每个掉不下一斤面,面要合得硬,揉好的大饽饽放炕上醒好,即刻装锅。这时候要用大火,玉米棒玉米根可劲往灶里填,风匣“呱嗒呱嗒”拉个不停,锅里的热气就从锅边往外哧哧地冒。不一会儿,甜甜的馒头香味就溢满了屋子。那几日,炕头上热得烫人,晚上睡下谁也不愿意往炕头上躺。
随着天气的变暖,草垛的个头也逐渐地变小,大蘑菇逐渐变成了小蘑菇,终于有一天草垛不见了。它们都变成了草木灰,成为新庄稼的肥料。
在这些肥料的滋养下,又有新的庄稼长出来,接着就有新的柴禾堆到了空出来的草园里。
年复一年,土地、庄稼、柴禾,就这样周而复始地给予和索取,人们的生存便有了保障。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蘑菇状的草垛不见了。没有人去坡里搂草,割棉槐条子。地里街上,很是干净,已难得见到散落的草木了。土地早已流转给那些专业大户,种植收割、田间管理,都是机械化、自动化,那些先前被人们当做宝贝的麦秸玉米杆,人们懒得往家里收拾,收割机连收带割,直接将秸杆粉碎地里,当做了肥料。
各家各户,做饭取暖,先用的煤,后来为了环保,煤都很少用,直接用了煤气、电器。家家安了土暖气,冬天既可烧水,又可取暖洗澡,干净清洁,温度适宜,省却了冬日里盎炕的诸多麻烦。也有人家,用上了沼气,安上了太阳能,不但做饭有了不花钱的气,平日里都用上了热水,就连照明也都捎带了。
据说,太阳能、沼气以及暖气的安装,包括农村厕所的改建,政府都要补助,农民们出一点钱,就可以享受优惠。
而今回老家,已经很少见到各家烟囱里冒着的黑烟了,那些大锅灶旁呱唧呱唧拉着的风匣,早已成为了古董,被收藏家收藏起来,作为纪念了。还有陪伴着我长大的拾柴禾的棉槐条筐篓,也早已不知了去向。
路边的树叶再多,沟边的草再高,也没有人去理睬,兀自孤傲地炫耀在那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共同富裕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乡村要绿色发展。各级加大了金融支持力度,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眼下的农村,正一步步走向城乡一体的道路。
这的确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必再像先前那样下死力气劳作,再不必为做饭取暖去搜罗植物的根茎。逝去的不会再来,时代总在进步着向前。
我们依恋着曾经的劳作,不舍得抛弃那些曾经付出过巨大代价的过往,因为那也是一种人生的历练及其美好。
在忆及往去了岁月的同时,人们更容易关注当下,是的,人行走路上,眼自然是向前望的。然而,好日子是人们一点点、一步步,迈着坚实的脚步实现的。为了那些曾经的不易,也为了那些不易不会再来,因此要学会珍惜。
珍惜那些为着生活的艰辛,也珍惜那些为着生活的烧柴。

作者简介: 高金业,笔名碧古轩主人。山东龙口人。1973年入伍,在空军部队工作30余年,后转业山东省直机关工作。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曾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特写、诗歌等各种文学作品数百篇。中、短篇小说集《真情》被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品被收入《飞向极顶》、《绽放的军花》、《军魂》、《胶东亲情散文选》、《母亲的力量》、《庚子战疫》等书中。长篇纪实文学《北方之鹰》刊于《时代文学》,被青岛出版社出版,并被“齐鲁晚报”连载,该作品获山东省纪念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征文一等奖。出版有《胶东散文十二家高金业卷》。作品曾多次获文学期刊及文学网站征文奖。
壹点号碧古轩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