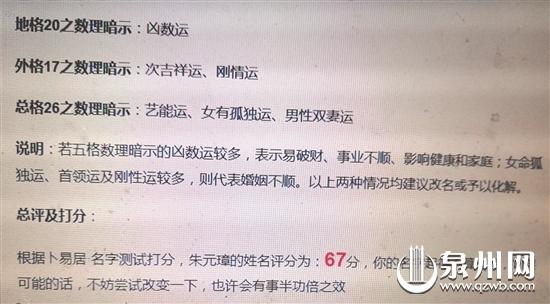《鲁迅之死》(从鲁迅之死开始谈起)

“
任何的批判,都比繁琐细致的研究来得容易,也不必每天到图书馆弄得两袖灰尘。
——程光炜
从“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到“改良改良,越改越凉”,“鲁郭茅巴老曹”对于大多数的中国青年而言都耳熟能详。然而,他们的形象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一步步塑造出来的呢?程光炜先生的新作《文化的转轨》给我们了一份答案。
文学分期
“鲁郭茅巴老曹”这一经典作家序列在当代中国的建构过程,显然是一个好的故事,但这样一个故事从何讲起、如何开头?程光炜的选择可谓慧眼独具。他选取的起点是1930年代中期“鲁迅之死”。笔者认为,程光炜借此提出的,是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另一种分期尝试,即从“鲁迅之死”,围绕着刊物、大学、知识分子展开的“现代文学”已经结束了,而从郭沫若回国到就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并很快作为“鲁迅的继承者”成为“文化界的领袖”,“当代文学”已经开始。

“势”与“人”
程光炜未并简单地把这些学者作为拷问的对象,而是对他们的处境进行了耐心的分析。这种处理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文学史编纂史研究者提出的文学史写作中的“势大于人”的论断。由于当代政治与文化的复杂关联,这样的判断确有其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分析了“势”之后“人”就可以被忽视了。姑且不论“人”对“势”的能动,即便是在“势”覆盖了“人”的地方,也应考察“人”在“势”中的反应。这样不仅可以经由“人”更细致地看清“势”,还能看到在“势”的作用下“人”已经的和可能的作为。

另一个鲁迅故事
“鲁迅的塑造”是笔者印象很深的一章,每个小节读下来都有“柳暗花明”之感。以“故居”“纪念馆”中的鲁迅这一节为例,作者从许广平布置北京鲁迅故居起笔,将故居再而纪念馆再而博物馆的过程一一道来。当读到鲁迅生前居住过的普通四合院——作者专门在脚注里提到鲁迅的卧室兼书房是一间8.4平方米的斗室,最终成为“一座具有先进的防水、防火、防盗和恒温等设施的现代建筑”时,顿然有了想重温鲁迅任一篇杂文的冲动。

不过,程光炜对表面化的冷嘲并没有多少兴致,而是极有耐心地“将笔墨转向远在南方的上海”,然后又“禁不住要去被上海人说成‘乡下’的浙江绍兴游历一番”,并最终落脚于广州中山大学的鲁迅纪念馆。这么一番纪念馆之旅走下来,作者要提醒读者的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鲁迅的故事已经结束,1950年代的另一个鲁迅故事正在开始。但它们之间绝不是相互断裂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接轨的关系。”这是作者对于不断被翻盖和装修的“鲁迅”这座建筑物的观感,也是对于仍然在延伸的当代(文学)史的内行诊断。

关怀体察
论述得比较辛苦的是“郭沫若之路”一章,因为研究对象与当代政治社会史的深度纠缠。有意思的是,程光炜这次既不打算如“新启蒙”思潮那样对郭沫若简单批判一番,也不愿意像持有另外文学史观的学者那样专注于做翻案文章。在程光炜看来,这两类方式都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文学史研究中常见的符号化、断裂式和“六经注我”等问题盖因于此。其结果往往是文学史家仅仅在在研究中暴露了自己身处的历史位置,而研究对象的本应有的历史感却没有显现出来。程光炜属意的研究态度是尽量“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境遇”做到“关怀体察”。我对这里的“关怀体察”的理解是:一方面要尽量贴着研究对象的现实处境理解其所作所为,另一方面又借用长时段的眼光去确认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位置。

“五四”和“当代”
比如对于郭沫若在“当代”的写作和做派,程光炜认为这与郭本人的“五四式的自我人格的设计方案”、爱国主义、个性解放和文化英雄情结并不矛盾,并且,前者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后者在包括单位制度在内的当代社会体系中的扭曲实现。这一判断让程光炜的研究一下子和两种比较常见的文学史观区分开来。一种文学史观是“新启蒙文学史观”,它的主要观点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和“当代”的政治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另一种是所谓的“新左翼文学史观”,它认为“当代”实际上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自然发展的结果。程光炜让读者看到了另外一种解读历史的可能:“五四”和“当代”当然有着深刻的联系,但“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在当时有着解放的意义;这些思想在“当代”经历了社会语境的巨大转换,它们的背后“潜伏着1950年代之后社会道德和精神生活的深刻危机”,不应该把这笔糊涂账尽数推给五四,而是要正视在1950年代-1970年代到底是哪些力量、用怎样的方式塑造出了这样一个郭沫若。

壮烈的一页
这些复杂的辨析让人头痛,好在作者并没有被这些观念上的论争所拘囿,他的“关怀体察”有着更为宽阔的视域:茅盾与现实政治的微妙平衡中,他身上的吴越文化所起到的作用;老舍对新政权的认同、所受的礼遇在他身上激起的“士为知己者死”的集体无意识,和进而“焉有不为现实而宣传的道理”;巴金的创作水平在1940年代就已开始滑坡的事实,以及曹禺修改《雷雨》时的自保心态和他身上的繁漪幽灵。这里面让人感觉最到位是对老舍的分析。程光炜认为,作为平民子弟的老舍,“他的实践来自于原来阶层的教养”,为人处事上既懂得知恩图报又绵里藏针:“当他在生活中一帆风顺时,社会权力对其创作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一旦遭受挫折,这种生活状态就会全线崩溃”。写到这里,程光炜不禁感叹:“轻轻掩上文学史的书页,那里壮烈的一页确实让人无法平静”。

(篇幅所限,原文有删减)
(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编辑 王薇 供稿 张雅秋】
好 书 推 荐
长按图中二维码可进行识别关注
点击本文最下方“阅读原文”,
直接在北大社官方微店下单吧!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