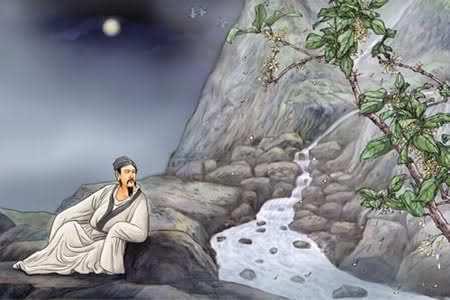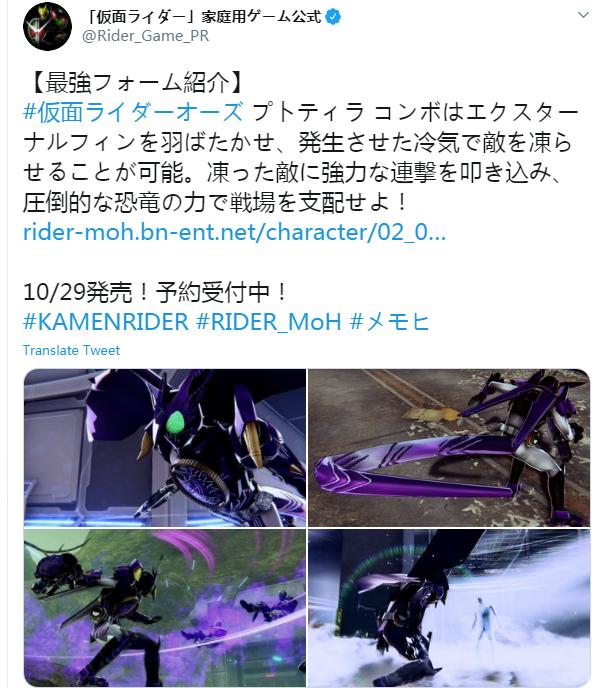器官移植前的准备工作(器官移植从谈移)

去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姚女士陪患有肝糖原累积症的儿子昊昊等待接受费用相对较低的亲体肝脏移植手术,即用姚女士的一部分肝脏替代昊昊的全部肝脏。
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袁全
望着眼前的长寿面,62岁的刘芳(化名)心想这也许是人生最后一个生日了。2015年年初,她查出肝脏有肿瘤,医生建议马上做肝移植手术。她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却没有等到合适的肝源。
没想到生日的第二天,医院通知“肝源到了。”她当晚8点被推进北京佑安医院的手术室,8个小时后,一个来自42岁男性的肝脏开始在她体内工作。术后两年多的时间,她的各项肝功能指标保持正常。
刘芳把器官移植视为一次“重生”。
据官方数据,2015年中国器官移植手术达到10058例,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16年超过15000例。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大多历经求医问药,举债筹钱,垂死挣扎,才使生命得以延续。他们感慨医学技术的神奇,感谢命运的眷顾。尽管重生之后,生活依旧艰难,但他们仍称自己是“最幸运的人”。
从谈“移”色变到“救命机会”
我国的器官移植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较其他国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1972年,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了全国首例活体肾移植,受者存活一年以上。此后随着肾移植经验的积累,肝脏、心脏、肺脏、小肠以及胰腺等器官移植相继开展。
然而,器官移植真正大规模进入公众视野要等到2000年以后。2004年,演员傅彪接受肝移植手术。36岁的何欢(化名)也在当年查出肝硬化晚期。她以经营小买卖为生,很少体检,结果乙肝“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了肝炎、肝硬化,最后成了肝癌。有医生建议她马上做移植手术,但她选择保守治疗,因为对器官移植完全不了解,“害怕最后人财两空”。
医生刘源从2003年开始便在北京佑安医院做肝移植手术。他说那时病房里都是谈“移”色变。“不仅病人有顾虑,有些内科医生都不是很懂。”
在何欢印象中,医院里做移植的大多是“老外”,她几乎找不到可以交流的病友。而傅彪历经2次移植手术也仅延续1年生命的例子,更印证了坊间流传,“做也是死,不做也是死”。
此后一年,何欢又经历一次肿瘤破裂大出血,“血喷如柱”。这是十分危险的征兆,她险些丧命。但“挺过来”之后她还是犹豫,直到又在病床上熬过了一年,医生对她说,“这回你可过不去了。”
辗转其他医院,所有的医嘱都是建议移植,何欢这才下定决心。“这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她和家人简单算了一下医药费,便草草把一套北京二环边上90平方米的房子卖了80万元人民币。按现在行情,那套房的价格可达1000万元。“顾不得那么多了,”何欢说。她手术前交了35万,而术后几年的用药都要自费,每年少则上万,多则十几万。她同病房的一位病人就因为“钱的问题”,最终放弃了移植。
手术前,何欢高烧不退,医生们也紧张,劝她慎重,“肝源还会有。”但这次是她自己等不了。“太难受了,腹水,腿肿,整天在床上动弹不得。”何欢回忆道,“我和大夫说,即使手术失败了我也不会讹您。”
当晚7点她被推进手术室,那天是6月26日。11年来,何欢恢复得很好,她说这得益于自己的新肝是来自一位19岁的生命。
为更多人不因“移”致贫而努力
2015年,中国宣布废除死囚器官使用,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渠道。然而,中国现阶段器官供需比是1比30,短缺严重,很多人在等待中死去。
让人恐惧的还有经济负担。坊间将器官移植称作是“富贵病”。很多患者因为凑不出几十万元的手术费而放弃移植。
根据2007年颁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医疗机构向接受人收取的费用包括摘取和植入器官的手术费,保存和运送器官的费用,以及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药费、检验费、医用耗材费。器官移植的手术费用不断攀升,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少则六、七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且不在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这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
即便能勉强支付手术费用,移植后的药费也是一笔巨款,且很多药品需要终身服用。
赵军(化名)11年前进行了肝移植手术。他根据术后必须服用的药品和检查算了一笔账,发现一般人在术后第一年每个月就要支付1万3千元左右,一年的药费就要12万元,此后随着病情稳定,逐年递减,但至少也要4、5万元。
2007年以前,大部分药品还未纳入医保,都需要患者自费。2007年后,北京市医保也只解决每年2万元的治疗费用。
何欢看到太多人为省钱,选择减药或停药,结果导致病情加重,需要再次移植,或者死亡。
2007年以前,北京市对于器官、组织移植的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只包括肾脏、角膜、皮肤、血管、骨和骨髓。
从2008年开始,何欢和数十位移植病友呼吁让肝移植术后抗排异、抗病毒治疗费用纳入医保。由乙肝病毒致病的移植患者需要终身服用抗病毒药物,且不减量,一般术后第一年单治疗费用就需要大约4、5万元。移植患者每年不计其数地向卫计委、劳动保障局医保中心等政府部门递交诉求。
何欢认为要求合情合理。“器官移植挽救了我们的生命,但生活的压力接踵而至。有些家庭手术时的费用还未还清,每个月几千元的药费比家庭的总收入还要多。很多人因病致贫,没有一点生活质量。”
“接待人员对我们态度很好,因为他说他的朋友也做过移植手术,知道用药艰难。”何欢说。
努力没有白费。2010年9月和2011年7月,肝移植抗排异、抗病毒治疗相继纳入北京医保“特种病”报销范围。
尽管如此,移植患者需要自付的药费每月还是有上千元。“这对于我们每月只有三千多元退休金的家庭来说,是笔巨额支出,”刘芳说。她因为移植手术,身上还背着50万元的借款,至今还不知如何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建议将器官移植的手术费也纳入大病统筹。
现在,何欢和其他移植患者还在努力呼吁将“乙肝免疫球蛋白针剂”纳入到医保。“不注射就会导致乙肝复发。”何欢说,一针“乙肝免疫球蛋白针剂”的费用是648元,一般的患者平均每个月要注射2至4次,一个月就是两千多元的开销。
从2010年开始,何欢不断地向政府部门、医药公司写信申请,她已记不清申请了多少次。“听说上海、广西的朋友们已经成功,我们也不会放弃。”
同病相依,“过来人”传递希望
器官移植技术的研究曾多次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认为是“医学手术皇冠”。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初期,手术只有主任级别的大夫才可操刀。
目前,全国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仅有169家,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只有几百人。黄洁夫表示,制约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一大因素是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够。特别是心、肺移植的医疗人才短缺,造成很多器官浪费。他建议未来5年,使有资质的医院增加到300家,并加强对器官移植医生的培养。
医院移植人才的短缺,也让患者对器官移植更加陌生和恐惧,特别是对术后生命的未知。如果说器官移植手术要依靠大夫的医术,那么术后的存活就是自己掌控。毫不夸张地讲,一粒药片上哪怕增、减一毫克,都关乎生命的质量和长度。但“主刀大夫只管手术”,“内科大夫又不太懂用药”,患者得到的答复往往是“情况不好了再说”。最后,可以信赖的就是病友。大家同病相怜,相互依偎。
2004年4月,36岁的雷宇(化名)通过自学,建立起一个器官移植的网站。他起初只是为了分享自己移植后重获新生的经历。他在单位体检时查出肝癌,被医生判了死刑,“生命只有2、3个月”。“手术成功后,我很兴奋,特别想告诉其他人,被称为‘癌中之王’的肝癌并不可怕。”
没想到网络让他结识了病友。大家开始陆续在他的网站分享自己的故事,以及搜罗到的康复资料。雷宇说,十几年前,关于器官移植的报道少,对于即将接受移植的患者来说,内心恐惧,孤独。“过来人”的“现身说法”,往往比医生相劝还要管用。
他将网站命名为“中国器官移植网”,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篇名叫“肝癌可以被治愈”的帖子,点击量过8万,里边涵盖了许多接受移植病人的故事和照片。
网站的交流日益丰富,名声也逐渐响亮,雷宇和其他病友又陆续创办了杂志和微信公众号。有的人愿意把自己的病例,化验单分享出来,供大家分析、参考;有的病友本身就是大夫,网上“坐诊”,答疑解惑;还有的人“久病成医”,收获上百拥趸,帮病友寻医问药。
网站上还有人“晒”出行游记,登高爬远,自驾千里,挑战极限。大家享受生命的眷顾,也展现对生活的信心。这个人数并不庞大的特殊群体,也展现着人性的光辉和黯淡。有人妻离家散,也有人找到了知心伴侣。有人因不舍钱财,撒手人寰;也有人因同学情深,靠捐款渡过难关。
钟岳(化名)18岁带女友从湖北来京打拼,两个年轻人不敢把他的病情告诉父母,只能一边工作挣钱,一边治病就医,自食其力。最后他们花了7年时间,靠辛苦创业支付起几十万元的手术费。爱人始终不离不弃,让钟岳心念感激。
高玉东(化名)舍己救人,把盼了几个月才盼来的器官源,让给了一个病情更加危重的女孩,结果他又多等了4个月才做上手术。他不仅为此多支付了7万多元的医药费,还冒着随时都可能大出血的危险。那4个月“每天度日如年,心惊胆战”,但他无怨无悔。
对于大多数接受器官移植的人,重生后的心愿就是感恩。他们渴望得到关怀,也希望回报社会。他们大多数已申请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我愿意把完好的器官,乃至遗体捐献出来,哪怕不能救人,也愿意为医疗事业的研究做贡献。”何欢说。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