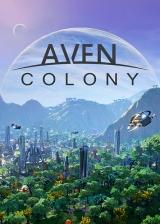相声中鲜为人知的禁忌(再来谈谈相声中的)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了相声本门应该是五门功课,再加上一个小门,算是5 1门功课,这可能与我们通常听到的不大一样,因为在相声演员中总是强调相声的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这是因为第五门——“杂”在新中国相声的演出中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运用的熟练了,毕竟相声作为一门艺术品类,已经不再是旧社会那种难登大雅之堂,不入艺术之林的“玩意儿”了,而是成了文艺工作者,甚至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了,一个个出来自带光环,也都是以“老师”相称了相比起以前的撂地相声来,可谓是一步登天,鱼跃龙门了,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相声中鲜为人知的禁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相声中鲜为人知的禁忌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了相声本门应该是五门功课,再加上一个小门,算是5 1门功课,这可能与我们通常听到的不大一样,因为在相声演员中总是强调相声的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这是因为第五门——“杂”在新中国相声的演出中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运用的熟练了,毕竟相声作为一门艺术品类,已经不再是旧社会那种难登大雅之堂,不入艺术之林的“玩意儿”了,而是成了文艺工作者,甚至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了,一个个出来自带光环,也都是以“老师”相称了。相比起以前的撂地相声来,可谓是一步登天,鱼跃龙门了。
说起撂地来,所包含的种类就太多了,戏法、剑、丹、豆、环、火帘、罩子、抱花子、倒包子等。还有的带有驯狗、羊、猴、鼠等一类的小动物。并结合“卖口”进行演出活动。“卖口”在“撂地”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撂地”艺人的一项基本功。“撂地”艺人一边“使活”,一边“使口”。“使口”时既要熟记程式性的解说词,还要根据节目的演出实况和场上观众的情绪、身份、反映等情况即兴编讲。讲起来既要一段接一段流畅自然,又要入情入理,合辙押韵。“撂地的”少则一、二人,多则三、五人,其道具轻便,行动灵活,演出地点大都在茶馆、酒肆、路旁、村头,活动范围主要在乡镇和集市庙会。演员在平地上演出,另有人向观众租赁桌、凳,供观众坐席。撂地”卖艺按场地分可以分为三等:上等的设有遮凉布棚和板凳;中等的只有一圈板凳;下等的什么设施都没有。又称:“明地儿”。不过呢,在这里还有一些区别,那就是北京相声和天津相声的区别。
北京相声虽然也有在“新世界”、“城南游艺园”,包括天桥等地撂地演出的演员,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主要是应堂会,去到宅门里表演;而在天津则基本都是撂地演出,顶好的也就是园子里,绝少有堂会演出。且天津的观众相比起北京的观众来说,对相声的热情更高,更认真,更明白。
我们现在总结相声的表演一般分为四个部分,由“垫话儿”——即兴地开场白;“瓢把儿”——转入正文的过渡性引子;“正活儿”——正文;“底”——掀起高潮后的结尾四部分组成。但在当年却很少是按照这种表演形式的,往往他们先在地上画个大圆圈,这也叫做“锅”。两位相声演员站在里面,不一会工夫就会有很多小孩子把场子围了起来看热闹。站在里面的两位演员面带笑脸,不时地挥手向过路的行人打招呼让他们过来,有的人不知怎么回事就站了过来。或者有的演员(尤其是单口演员),一边撒字,一边唱着太平歌词,为什么要唱太平歌词呢,其实就是因为太平歌词简单,你在一心二用的时候,可能记不清楚词,容易唱丢了,而太平歌词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基本不需要过脑子。这种边撒字边唱的,是不用打板的。只有在演出中间加演的时候才手持玉子,进行独唱,抑或是两个人对口唱,现在很难再看见这种对口唱的了。
时间不长,撂地的场子就打好了,能站在这里的人大多数为穷人,那时的相声没有固定的剧本,基本全是临场发挥,这也叫现挂。他们在演出中逗哏的演员两眼不时地盯着路过的行人,尤其看到大姑娘小媳妇及穿戴好一些的行人,就成了他们的讽刺的笑料。这些人看到说相声的人拿他们找乐,赶紧面带羞涩,红着脸,快走几步,离开这里。有一些文人和买卖家的大老板遇到这种情况赶紧掏出几分钱扔到场子里转身离开这里。他们如不这样做,逗哏演员就会在他们身上找到笑料,说出奚落的话语,闹得路过的行人十分尴尬,围圈看相声的人们顺着演员所指方向,看那行人尴尬的样子大笑。大笑之后两位演员开始敛钱,他们手中拿着托盘面带笑容点头哈腰向围观的人要着小钱,给钱的人大都是成年人给上一二分钱。一天下来他们的收入很低,块八毛钱回家买些玉米面、棒子面,养家糊口。而这种,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控场的能力就叫作“杂”。
你就算“说学逗唱”俱佳,如果没有本事来招揽观众来看,只是一味地去表演,那是赚不到钱的,赚不到钱的话,身上的能耐再好也没用。所以那时候的演员在学习了基本表演手法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学习“杂”。最简单地说,这是你能否吃上饭的本事。在这点上,不单是相声演员,即连数来宝、快板书、山东快书,乃至兜售大力丸的等等这些都要学习这个。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包袱”不同,著名相声艺术家马季在谈及相声的基本概念时指出:“(相声)就是通过组织一系列特有的‘包袱’来使人发笑的艺术,这里所指的包袱是语言艺术的包袱,这里所指的语言是包袱艺术的语言……语言、包袱儿、笑声,可说是相声艺术的三大要素,并且缺一不可。” 在他列举的三要素中,语言、笑声是其它一些喜剧艺术也具有的,只有包袱才是相声艺术特有的。包袱在相声艺术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包袱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是我们研究相声艺术的关键。
“包袱”一词是个形象化的比喻词,它实际上指的是相声中喜剧性矛盾酝酿、发展的一个过程。所谓的“三翻四抖”,则是相声包袱常采用的结构。其中“三翻”是指对矛盾假象反复进行渲染和强调;“四抖”是指在三翻之后揭露矛盾的真相。喜剧矛盾的特征是“用另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因此在喜剧矛盾中,各种假象就特别多。假象其实也是一种现象,它的特点是能够提水与其本质相反(或相离背)的表象,然而,假象又是以其特有的方式极为深刻地反映着本质。因此,真实的喜剧矛盾具有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的特点。比如马三立说的《逗你玩》,前面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这个贼怎么跟小虎做游戏,怎么教他念自己的名字,经过这么多的铺垫,三番四抖,最后贼来了,把小虎妈晾在外面的被单偷走了,达到让观众开怀大笑的效果。而笑料就是非常简单地通过语言动作即时达到让观众发笑的目的,比如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一个男服务生把蛋糕扣到客人头上,这是属于浅层次的幽默手法。
但其实我们说,这个“包袱”也并不是相声所独有的,比如说评书,也是要适时地抖响一些“包袱儿”,评书因情节多惊险曲折、险象环生,为了使观众精神上不至于过度紧张疲倦,但是不可能一直让听众处于紧张的环境下,也要适时抖一点“包袱”,以加强诙谐幽默感。这是评书表演调节书场气氛的一种重要手法,运用得当,效果会十分强烈。评书抖“包袱儿”的手法约有四种:一、从书中所塑造的滑稽人物身上找“包袱儿”,如《兴唐传》中的混世魔王程咬金、《施公案》中的小脑袋瓜赵璧;二、古事今说,在说书现场抓现哏。素有“评书大王”之称的清末艺人双厚坪就擅长即兴逗笑,观众由此称赞他“于叙述古人之中,暗地讥讽时事,不露芒角,令人心旷神怡”;三、以夸张、误会、错觉、巧合、双关语、谐音等手法抖“包袱儿”,讲究铺平垫稳、前呼后应;四、以状形、状物、方言抖“包袱儿”,这类笑料有的与故事主题结合得很紧密,如《刀劈胡汉三》中说到潘冬子举起利刀砍胡汉三时,“别说是胡汉三的脑袋,就是这猪头也碎啦!”(状形)而有的则纯粹属于活跃气氛的插科打诨。
而“杂”代表的则是一种演出的技巧,控台的能力,随手抓哏的本事。要知道我们现在听相声,电视机前就不用说了,那个你要是不喜欢可以换台,但是坐在剧场里就不一样了,你要守规矩,要文明,各种的条条框框管着你,就算你不喜欢听,也很少会有抬腿走人的,毕竟票价不菲,可惜了的。但是以前不一样啊,不管是明地儿,还是剧场中,听众们要是不喜欢,那可就是直接闹场啊,严重的可能你还要挨打,在那种地方,只除了例如像一些京剧的名角们,比如金少山等之外,就算你在台上有个“担待”,观众还能见谅,可是相声演员可到不了那个层次,你要是说不好,观众们可不惯着你,一次两次下来,你可就买不起“嚼谷儿”了。
那么“杂”的本事究竟在哪里呢?首先说,你的基本功需要扎实,有的“卖”,才能让人认可,即像数来宝的一样,能随时随地的抓哏,编出词来,虽然不需要合辙押韵,那起码是让人听了有韵味,有 “嚼头”,站在那里可以回味一下;其次是眼快,现场的环境,南来北往的都是些什么人,那些人可以是被你抓入哏的,那些人是面皮薄的,搁不住几句玩笑的,那只有破财免灾了,要是眼神不济,抓了个你惹不起的主,那可就惨了,不单挨骂挨打,可能这地界以后你都进不来了;再次是脑瓜子灵活,嘴头子得利索,眼到嘴到,就能吸引人,一个敞笑过后,起码能收上几个钱儿来,这才是本事。以前讲,“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现在说起这个词来,算是个贬义词,可在那年月,打把式卖艺靠的不是你真有多大的本事,您想想,这些人不是一时走窄了,像评书中所说的,那些落了难的公子王孙,走到那里,困住了,手头上一时不便,没奈何只得靠着手里的玩意,换几个钱使唤,还往往碰上什么事,这可是经年累月在这个地界耍学变练的,见天的油锤贯顶,胸口碎大石,搁了谁也受不了啊。所以所谓卖艺,卖的就是这套江湖口,英雄词,让大家听高兴了,再耍练两下,看高兴了,这才能有钱赚;最后就是“荤素不忌”,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荤段子了,譬如我们重新检出来的《探清水河》里面的四更天,现在很多地方直接将四更天给删略过去了,至于“四更鼓里忙,二人上牙床”,这个是二人转里面的,其实您想想,这在当时也是四处传唱的一首小曲,也不可能想《金瓶梅》中那样细致的描写,顶到天就是类似《盘丝洞》表现的类型差不多,放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是下流了,如果放在今天,根本不算什么,一到夏天,女孩子们穿着比起那个时代来,可“黄色”的多了。何况,正如郭德纲所说的,那些个荤段子大都是让你琢磨一下的,也就是用的隐语比较多,例如咱们现在在写文章的时候,往往会有这样的字句,“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懂得”,心知肚明也就是了,毕竟语言艺术不可能像文字那样可以肆无忌惮的。那么在“杂”学中,还有的就是与观众的互动,利用观众的互动,调动观众的情绪,既要将观众安抚住,又要巧妙地利用观众的互动,延续自己所说的内容,同时又得让观众满意。面对观众的质问和搅合,你不可能直接就在台上和观众互怼,在现在的剧场中有可能,以前的年月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观众是衣食父母,没人给钱,你能耐再大,本事再好,都没用啊,所以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展现一个演员的真正本领的时候了。那时候的徒弟和师傅学什么,就是学的这个本领,像现在,你说你会多少段相声,你会多少曲子,那都是后话,你不能压住场,观众不会静下心来看你表演的。这里还需要的就是“扣子”,那个时候要钱都是说到一半的时候,下去要钱,这就需要你既能将观众吸引过来,又得能让观众留下来,同时还得让观众有继续听下去的欲望,这就需要的是“扣子”,评书里有“明扣”、“暗扣”等等,相声不行啊,观众不可能等你那么长时间去解“暗扣”,故此相声基本都是“明扣”,例如《关公战秦琼》:(这里说明一下,这个段子是前辈艺术家张杰尧创作的,后来传给王世臣先生,但是那个版本实在找不到了,只好用侯宝林先生改编的,原作里面是张宗昌,不是韩复榘。这段相声的成形应于三十年代左右,据说当年小蘑菇常宝堃曾在天津演出过。)
甲: “老太爷!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那好啊,请您点戏吧!”
乙: 对。
甲: “我问问你,是关公的本事大?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乙: 那谁知道啊?
甲: “那……他们俩人没比过。”
乙: 是啊。
甲: “今天让他们比比!”
乙: 啊?比比?
甲: “来个关公战秦琼!”
乙: 这可真新鲜啦!
说到这里的时候,就该下去要钱了,这就属于“明扣”,观众听到这里也会产生疑问,怎么比?不是一个朝代的啊,就是利用观众的这种心里,下去要钱,才能有人愿意给钱。
虽然在进行相声总结的时候,将这个“杂”给删除掉了,但其实就在我们现今相声重新回到小剧场演出的时候,这个“杂”中的很多理论还是需要尊重的。德云社一再强调观众是相声演员的“衣食父母”,这是正确的。在商品经济时代,相声早已不再是电视舞台的宠儿了,一旦重新回到民间的时候,那就需要普通老百姓的认可,才能继承并发扬光大。“说学逗唱”是相声的四种最基本的艺术手段,而“杂”才是真正可以将这些艺术手段明明白白地呈现给观众的表现手法。相声要想真正长久走下去,这个“杂”是永远不能丢掉的!一个真正的相声演员只有真正继承了这五门功课,并能真正实际运用到演出上面,才能被称为大师!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