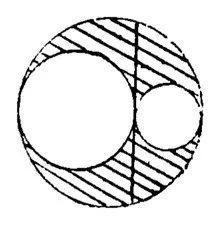捧哏巨匠朱鹤松遇到对手(赵佩如艺海拾零话)

赵佩如
在对口相声里逗、捧同样重要,决不是逗的重,捧的轻。捧逗有捧逗的技巧,一个包袱响了是俩人的力量。让我说衡量捧逗的作用不能从话多话少上看,怎么说呢?有时候越是话少,越是“肩膀”;短一句包袱就响不了。在传统对口相声里捧哏的作用非常明显,决不是单口可以随便改对口;对口随便改单口,一改那句头满不合托啦!
比如我演的《揭瓦》内容是讽刺旧社会一个小市民欺软怕硬、假充光棍。他揭了房上的瓦,房东找他来,他还打了对方,惹恼了房东的儿子们,气冲冲地拿着家伙找他打架来了,他一害怕,这儿有两句台词是:
甲:……我们院里有块大石头,一百多斤,平常我哪儿弄得动呀,那天也是急劲,一伸手给举起来了。我举起石头一想,我砸死一个够本,砸死两个赚一个,托着石头往门道跑,一撒手,当的一声……
乙:砸死几个?
甲:我把门顶上了!
乙:对!顶上门怕人进来。
这里捧哏的只有这么两句话,可是在甲叙述经过时他也得帮助做戏,除了集中精神地听甲述说外,到“当的一声”这儿他得带点紧张语气问:“砸死几个?”甲回答:“我把门顶上了!”到这儿包袱就响了,听众知道甲是虚张声势,于是觉得可笑。但这类包袱后边捧哏的却不能立即“刨”甲,如果说一句:“真泄气!”那对底下的情节倒有损失了,所以我体会要一本正经地说:“对!顶上门怕人进来。”这样对内容发展会有好处。再如:
甲:我跳后墙跑,我打后墙往下一出溜……
乙:跑啦?(有意地支,起垫的作用)
甲:后边蹲着四个哪!
乙:把您的后路卡了。
看,这简短的对话够多么紧凑、生动,可是捧哏的要不用这两句吃紧的台词,还是一般地询问或顺口搭音,那不仅给逗哏的添了麻烦,也大大地泄了劲:
甲:我跳后墙跑,我打后墙往下一出溜……
乙:怎么样?
甲:还怎么样哪,我要跑没跑了!
乙:怎么没跑了哪?
甲:后边蹲着四个哪!
乙:好嘛!
甲:他们把我的后路卡了!
乙:是啊!
这一来,多出了好几句,还没有原来那四句交代的清楚。
在相声《论捧逗》里曾说:“逗哏的是拨船的,捧哏的是掌舵的。”这种形容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拨船、掌舵是一个劲头儿,甲乙演相声,不“合托”包袱就响不了。俩人高矮音,大小劲得配合好了,比如到翻包袱的时候捧哏的调门应该比逗哏的高一点,如果使到那儿声音一低那就把肉埋到饭里了。不只是发音方面要讲究高低、轻重、急徐,表情、动作俩人得密切结合,要不怎么叫“相”“声”哪!还有的时候根据内容需要打捧哏的这边出包袱,那逗哏的就得全神贯注地给他“量”著。像《灯谜》前边一人说一则“智力测验”轮到捧哏的说:“一个西瓜我切五大块十小块。”甲琢磨了一下说:
甲:我知道,你是先划印儿,划好了印儿,叭,一刀切开了,就是五大块,十小块。
乙:你拿什么划印儿?
甲:拿刀。
乙:划一个印儿呢?
甲:拉一刀。
乙:划两个印儿?
甲:两刀啊!
乙:那你得划多少刀啊!我这西瓜上就切一刀,要切它个五大块十小块。
甲:那我不知道是怎么切的啦!(前边甲的猜测,与乙的对话,都是为了铺垫得更清楚些,到乙又加重语气重复了“一刀切五大块十小块”,于是甲提出不知,好把“肩膀”给乙,让他说明真相)
乙:你不知道啊,我买一个西瓜,搁桌上一刀切两半,没留神掉地下一半。
甲:那怎么五大块十小块呢?(有动作辅助,伸出左手,手心朝观众,又把二指和中指叠在一起晃了一下,做着五和十的姿势)
乙:对啊,我是捂大块去拾小块。(左手按在桌子上,微哈腰右手向下)
这里甲乙的动作、语气要配合一致,包袱儿非常大。给我捧哏的李寿增先生这个包袱使得很好,前边“五”、“十”垫得不露痕迹,后边使用动作干净利落,让人明确地感到“五”是捂住了,“拾”是拣的意思。这虽是个语言上的谐音包袱,离开动作就不易收到强烈效果。
一个好的捧哏演员他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有正面烘托,有侧面渲染,有辅助甲明垫,有辅助甲暗垫,有代表观众提出质问的时候,也有现挂包袱增强效果的时候。特别是有经验的捧哏演员应随时辅佐甲的表演,万一他临时忘了词,捧哏的也要不露声色地提醒他。过去我们出艺时都是老师给捧哏,出现了漏洞及时弥补,观众一点也听不出来,所以说有个好的捧哏演员会使逗哏的说得舒服、省力。
我个人喜爱捧哏,在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在我体会捧哏演员容易犯一个毛病:“学舌”,这不好,捧哏的除了有时候重复逗哏的一些极为必要的台词外,最忌讳那种衬话音的重复,正如《论捧逗》中形容的那位不称职的捧哏演员,逗哏的说:“昨天我到您家啦!”他说:“噢,到家啦!”逗哏的说:“啪啪一打门。”捧的说:“打门不咧!”这就是“学舌”。当然在这个段子里是通过比方说明捧哏重要性的,可是在我们演出相声时,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有一次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二位同志使《杂学》,捧哏的光是重复逗哏的话。甲说:“我去了!”他说:“喔,去了。”这样的话一多,人家听着就不舒服。改成“您多昝去的?”或是“干嘛去了?”也比这么“学舌”强。有的《杂学》逗哏的学几口唱倒是满够味儿,可是从整个段子来说却不是相声哏,捧哏的作用不好发挥,尽往里塞话倒给甲“挡”了,这一来,捧哏的话又少,作用又不大,这样发展下去对相声就有损失了。所以我建议《杂学》这类活也应该根据相声结构特点安排好“包袱”,不然捧哏的往那儿一站也僵得慌。侯宝林、郭启儒同志使的《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在这方面做得就不错,那里边捧哏的每句话都是“腿”,他把这话递过来,逗唱的很快地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段落,比自己“转”省事多了,还显著那么自然。
咱们捧哏演员在台上要盯住逗哏的,随着他的叙述表示各种不同的感情,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有夸耀赞美的,也有冷嘲热讽的;有的是用语言,有的是用神气。在台上要紧的是别给逗哏的“散神”,他正拿话“铺”呢,他得让观众集中精神听他说;不该捧哏演员说话时,只能用表情辅助,相声是用语言说故事嘛,人家对主要台词没听清,到地方怎么笑呀!怎么叫“散神”呢?我看首先是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演出,老以为:这没什么,或者在场上心不在焉,东张西望,这都容易“散神”。还有就是别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带到台上,有的同志在台上总拿手绢擦眼睛,要不就无目的地动,有这么两下,听众的精神就走的。不该笑的时候笑也不好,总起来说,捧哏的在场上处处得想法“拢神”才好呢。还有,捧哏的在台上不能盖着逗哏的,台词是这样,调门也是这样。前边咱们谈过,捧哏的有捧哏的话,在调门上,除了翻包袱时稍高外,平时总要比逗哏的低一点。有的同志逗惯了哏,再让他捧哏时,您看吧,话特别多,声调上也渲染得过重,结果怎么听怎么像俩逗哏的。捧哏既能完成任务又不喧宾夺主最理想,也最吃功夫。除了提高表演技巧、艺术修养,要紧的得提高思想水平,在政治、文化学习上要多努力。
我跟常宝堃烈士合作过十五年,他的艺术造诣很高,可是为人非常谦虚,他尊重捧哏演员,倚重捧哏演员,所以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他对我说:“有的活看谁逗着相宜就谁逗。”我们合作那些年像《福寿全》、《拉洋片》、《耍猴》、《醋点灯》、《坟头子》这些活都是我逗,他捧得也好,一丝不苟,尤其是《福寿全》这块活他捧得最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艺术上好学不倦,演出之前我们总是在一块儿仔细“对活”,直到台词、口锋、神气完全“合托”了为止,下场后就根据演出效果总结经验,发现了毛病立时研究修改。时间紧的时候,我们就在赶场的路上对词,谁琢磨出了新包袱就赶快报告对方,能用的就再研究使法。我们合演的近百个段子,他会我的词,我也会他的词,所以表演起来熟练自如,得心应手。在生活上我们互相尊重、彼此关心。每逢剧场、电台约我们演出时、他总是认真地跟我商量,问我怎样做好。我觉得宝堃烈士对待捧哏的态度、做法是值得相声演员们学习的。
(赵佩茹口述,仲文整理。台北相声迷丑伦彰扫校。)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