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国土面积和人口(土默特文史资料)

土默特地区,一般是指明长城以北,达尔汉、茂明安、四子部落三旗以南,察哈尔西四旗以西,黄河及察汗敖包以东的广大地区,即习称的归绥、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包头、武川七县、归绥、包头二市所辖范围。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恰好处于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频繁接触的地带。史料表明,随着历代封建王朝与北方民族力量的消长,生息、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民族群体也随之变化。总而言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本境有时虽为单一的民族据有(如秦末汉初的匈奴),但更多的时候是以某一民族为主体,各民族杂处为主要形式生息劳作,隋、唐、辽、金、元、明、清各代均是如此。本文拟就土默特地区历代的人口状况,特别是明代以来的人口状况作一些探讨。由于资料及能力所限,这种探讨只能是粗浅的,疏漏、谬误在所难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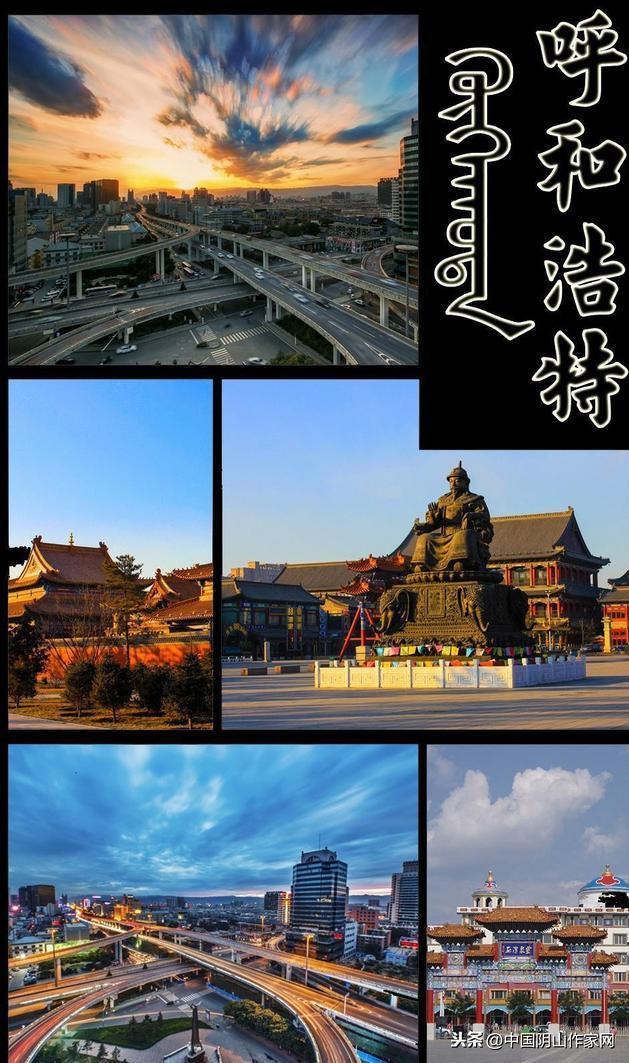
总之,北魏时期居于本境的鲜卑、汉、敕勒及“诸种杂人”当有数十万之多。
突厥 北魏末年,经“孝昌之乱”,拓跋氏在土默特地区的“州郡属县废徙已久”,到高氏北齐政权时,其建置更“渺不可究”,因而人口状况亦不清楚。当时惟柔然强盛,525年,阿那(瓖?)率柔然十万骑协助北魏镇压了六镇军民起义,柔然自此雄踞阴山以北,间亦南下至救敕勒川。六世纪中叶,突厥崛起,击灭柔然政权,势力达于本境。木杆汗时,曾“与西魏师入侵东魏,至太原”。到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东突厥沙钵略“控弦之士四十万”,于585年投附隋王朝。隋文帝令其寄居白道川(即今之土默川)。589年,东突厥突利可汗被都蓝可汗击败,率众附隋,隋封之为启民可汗,筑大利城(在今清水河县境)以居之。600年,隋又为之筑金河城(在今和林格尔县境)。时启民可汗“人民羊马,遍满山谷”⑩。
隋末,“值天下大乱”,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强盛,“中国人奔之者众”,“控弦百万”。固而始毕可汗“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⑾。到颉利和可汗时,突厥不断由本境振兵南下,攻略雁门、朔州等地。武德八年(625)七月,颉利曾率兵十万进至太原一带,全歼唐将张公瑾所部。当时,突厥在本境的人口数,史无确载,《旧唐书·突厥传》说:武德三年(620),处罗可汗立隋齐王杨楝之子“政道为隋王”,“中国人在虏庭者,悉隶于政道……居于定襄城(在今呼和浩特南),有徒一万”,据此可知,突厥部属居本境者,起码应数倍于此。
贞观四年(630),颉利可汗在白道岭(在呼和浩特北)被唐将李靖、李勣击败,不久被俘,“遂灭其国”。从此,东突厥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唐王朝于是“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⑿。关于居于本境的突厥部众,据载,默啜于万岁通天元年(696),曾向唐王朝索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主要在本地区),兼请农器、种子。唐朝“遂尽驱六州降户数千落,并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事以与之”。据此推测,居于本境的突厥降户及部众当有数万人。
天宝(742—755年)以后,留居本境的突厥人役属于回鹘。回鹘在本境出现,约当八世纪中。如至德间(756一757年),唐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曾与回鹘葛勒可汗会于呼延谷(即今之昆都伦沟);宝应元年(762),回鹘“北收单于府兵、仓库”,封其酋长“胡禄都督(为)金河王”。武宗初年(842年左右),回鹘“入云,朔,剽横水”,“转侧天德、振武间”,次年,其首领“嗢没斯率三部及特勤、大酋二千骑诣振武降”,“列舍云、朔间处其家”⒀。但回鹘在本境多属游动,不像突厥那样长期定居。
晚唐时期,居住于本境的还有沙陀人。元和三年(808),沙陀尽忠之弟“葛勒阿波率残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府都督”。大和中(853年左右),“委(沙陀朱邪)执宜治云、朔塞下废府十—,料部人三千御北边,号代北行营,授执宜阴山府都督”。其后,复命执宜之子朱邪赤心(李国昌)“徙节振武”。乾符间(874—879年)、令国昌“统云中突骑逐”黄巢,以其子李克用为“云中守捉使”⒁。到唐末,李克用曾在云中与契丹阿保机盟会,双方“约为兄弟,阿保机曾赠给李克用“马千匹,牛羊万计”。此后,直到辽代,沙陀人仍留居于本境。同期,吐谷浑人也曾在本境活动,如《旧五代史·唐书》载,乾符五年(878)“吐浑赫连铎乘虚陷振武,(朱邪国昌)举族为吐浑所虏”。
回鹘、沙陀、吐谷浑之在本境活动,惜史不载其人口状况,只能概而述之。至于其它游牧族,如薛延陀、奚等,因其在本境活动时间短暂,故略而不述。
隋唐时期 公元851年,杨坚废北周静帝即皇帝位,建立隋王朝,次年改元开皇。开皇七年(587),隋灭后梁,九年(589)灭陈,中国重新统一,土默特地区亦入隋之版图。隋王朝在本境的建置,《隋书·地理志》有如下记载:
“榆林郡:开皇七年置,置胜州。统县三,户二千三百三十。榆林、富昌、金河”。
“定襄郡:开皇五年置云州总管府,大业元年府废。统县—,户三百七十四。大利”。
榆林郡之金河县在本境,《隋书》注云:“开皇三年置,曰阳寿,及置油云县,又置榆关总管,五年改云州总管,十八年改阳寿曰金河。二十年云州移,二县俱废。仁寿二年又置金河县,带关”。大利县下注曰:“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金河县在今托克托城以北,仁寿二年(602)废而复置,户口以三县均之约近八百户,四千余人。大利城在今和林格尔北土城子一带,原为隋王朝为启民可汗所筑,大业初(606年左右)置大利县,为新置定襄郡郡治,而废云州总管府,全县约近四千人。金河、大利二县人口不足八千人,足见当时本地区的主要居民系突厥族(参见上文)。
隋末,全国各地纷纷起义,反抗隋炀帝的暴政。大业十三年(617),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于618年建立唐王朝。唐太宗即位后,于贞观四年(630)派李靖、李勣率军击破东突厥颉利可汗,唐分其故地为二,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贞观十四年(640),移定襄都督府于宁朔(陕西靖边、横山之间),移云中都督府于朔方(今乌审旗南部,红柳河北岸)。另外,唐初曾在汉定襄故城置云州,有“户三千一百九十六,口七千九百三十”⒂。贞观十四年徙云中都督府于恒安镇(今大同东),空其地以居突厥阿史那部。其后该部部众渐盛,于是置单于大都护府,《旧唐书·地理志二》的记载如下:
“单于都护府:秦汉时云中郡城也。唐龙朔三年(663)置云中都护府。麟德元年(664)改为单于大都护府。东南至朔州三百五十七里。振武军在城内置。天宝(742—755年)户二千一百,口一万三千。在京师东北二千三百五十里,去东都二千里。金河,与府同置”⒃
有唐一代,本地区为唐王朝的驻兵重地。据《旧唐书》载,“振武军,在单于都护府内,管兵九千人,马千六百匹”。“云中守捉……在单于都护府西北二百七十里,管兵七千七百人,马二千匹”。《绥远通志稿》说;“唐自贞观初平突厥以来,即分设都护、都督等府,以统蕃户。复于冲要郡城所在,间设总管,大总管等官,以成军民兼治,蕃汉相维之势”。景龙二年(708),唐为“屯军马而重秋防”,由张仁愿主持修筑了三受降城,其东受降城在本境(今托克托城以北),“管兵七千人,马千七百匹”。
综上所述,除突厥人外,居于本境的军民共约三万七千余人。
辽金时期 五代时期,五十余年间梁、唐、晋、汉、周五朝互代,中原分裂,战乱频仍。当时,契丹强盛,神册元年(916),耶律阿保机率军“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⒄。河曲系指东兴(磴口)至喇嘛湾的黄河河段,就是说包头以东,大青山南北广大地区尽属契丹,神册五年(920),契丹“攻天德”(即今乌梁素海西北岸),“拔其城”,“徙其民于阴山南”。天显十一年(936),契丹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以报之。至此,土默特全境尽属契丹,居住本境的汉、沙陀、回鹘、吐谷浑等族人民成为契丹属民。大同元年(947),契丹改国号为辽。辽王朝在本境的行政建置,《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如下:
“丰州,天德军……太祖神册五年攻下,更名应天军,复为州。有大盐泺、九十九泉、没越泺、古碛口、青冢——即王昭君墓。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统县二:
富民县:本汉临戎城,辽改今名。户一千二百。
振武县: 本汉定襄郡盛乐县。背负阴山,前带黄河。元魏尝都盛乐,即此……太祖神册元年,伐吐浑还,攻之,尽俘其民以东,唯存三百人防戍。后更为县”。
“云内州,开远军,下,节度。本中受降城地。辽初置代北云朔招讨司,改云内州。清宁初升。有威塞军、古可敦城、大同川、天安军、永济栅、安乐戍、拂云堆。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统县二:
柔服县。
宁人县”。
“宁边州,镇西军,下,剌史。本唐隆镇,辽置。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
“东胜州,武兴军,下,剌史……太祖神册元年破振武军,胜州之民皆趋河东,州废。晋割代北来献,复置。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统县二:
榆林县。
河滨县。”
丰州,隋唐时期在今五原之南黄河北岸,契丹于920年攻下该地后,在今呼和浩特东白塔一带另建一城,徙其民于此,亦名之曰丰州,州治即富民县。该县千二百户,以每户五口计,全县约有六千余人。另据《辽史·兵卫志》载:“富民县丁二千四百”。每户出二丁似不可能,故该县人口当在万余至数万之间。契丹虽曾尽俘振武县居民而东,尚留三百人防戍,这些人是否有家口,史籍未载,但设县以后,人口亦当有万余。大盐泺、九十九泉不在本境,略而不述。
云内州州治柔服县,《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在今土默特左旗三两乡黑河南岸。该州辖境为土左旗以西,包括包头、固阳及巴彦淖尔盟东部一带。东胜州在今托克托县一带,宁边州在今清水河县一带。以上三州惜无人口记载。以丰州为例,辽代人口约占金代人口的五分之一,以此比例计算,云内州约有人口二万多,东胜州约三千多,宁边州约有六千余,综计全境人口不超过五万人。
女真族于十二世纪崛起于白山黑水间。辽天庆五年(1115),完颜阿骨打即帝位,建立金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年),金将阇母、娄宝招降辽天德(丰州)、云内、宁边、东胜等州,从此本境扩入金王朝版图。金在本境的建置及人口状况,《金史·地理志》的记载如下:
“丰州,下。天德军节度使。
辽尝更军名应天,寻复,金因之。皇统九年(1149)升为天德军总管府,置西南路招讨司,以之德尹兼领之。大定元年(1161)降为天德军节度使,兼丰州管内观察使,以之管部族直撒,军马公事,并隶西南路招讨使。户二万二千六百八十三。县一,镇一:
富民县,晋旧名,有黑山、神山、镇一,振武。
云内州,下。开远军节度使。
天会七年(1129)徙奚第一、第三部来戍。户二万四千八百六十八。县二,镇一;
柔服县,夹山在城北六十里。镇一,宁仁,旧县名,大定后废为镇。
云川县,本曷董馆,后升为裕民县,皇统元年(1141)复为曷董馆,大定十九年(1179)复升,更为今名。”
“宁边州,下,剌史。
“国初置镇西军,贞祐三年(1215)隶岚州,四年二月升为防御。户六千七十二。县一,宁边,正隆三年(1158)置。”
“东胜州,下,边剌史。
“国初置振武军,有古东胜城。户三千五百三十一。县一,镇一。东胜。镇一,宁化”。
“净州,下,剌史。
大定十八年以天山县升,剌史兼权讥察,户五千九百三十八。县一。
天山,旧为榷场,大定十八年置,为倚郭。”
以上各州,除净州外,均沿辽旧名,只是辖境稍有变迁。如净州,为丰州支郡,在大青山后一带。云内州的云川县待考。东胜州则只治黄河以东,约当今托克托县境。宁边州同辽代。各州人口仍以每户五口计,可得:丰州约十一万三千人,云内州约十二万四千人,宁边州约三万余人,东胜州约一万七千余人,净州约二万九千余人。除去丰州、云内州居于本境之外人口,今土默特地区总人口应在二十万左右。
元代 十二世纪后叶,蒙古崛起。成吉思汗六年(1211),蒙古伐金,当年十月,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率军越过阴山,先后攻克云内、东胜等州,土默特地区遂入蒙古,本境以东的官山、九十九泉(在今卓资县北)成为蒙古贵族的避暑地。如1231、1232年,太宗窝阔台“避暑于九十九泉”、“官山”。其后,元朝在本境的建置,沿用完颜氏金朝旧名,而隶属则多有改革。《元史·地理志》载:
“丰州,下……金为天德军,复为丰州,旧有录事司并富民县,元至元四年(1267)省入州”。
“东胜州,下……金初属西夏,后复取之。元至元二年省宁边州之半入焉。旧有东胜县及录事司,四年省入州”。
“云内州,下……金为云内州,旧领云川、柔服二县,设录事司。至元四年省司、县入州。”
“净州路,下,领县一:天山,下。”
元代与金代相较不同者有三,一是本境各州不领县;二是废宁边州,以其半转隶东胜州;三是升净州为路,领天山县。至于人口状况,仅在大同路之下注明“户四万五千九百四十五,口一十二万八千四百九十六。领司一、县五、州八。”依此,每户平均不足三口人。如以一司、八州均之,每州仅五千一百余户,一万四千余人,本境也仅有近五万人,较金代减少近五分之四。但是元代本境人口是否锐减到如此程度,却值得怀疑。
首先,元朝太保刘秉忠《过丰州》诗曰:“出边弥弥水西流,夹路离离禾黍稠”。元人魏初的《丰州》诗也有“荞花如雪近丰城”之句,足见农业生产颇为发达。倘若丰州仅有五千余户人家,原野上怎么会有“禾黍稠”、“荞花如雪”的景观。其次,元代丰州城中设有“捏只局”、“杂造局”等机构,手工业、商业相当发达,正如《马可波罗游记》所说:天德省(即丰州)“人民靠商业、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维持生活”,居民中有佛教徒、回教徒和基督教徒”。这分明是对丰州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一个概略介绍,决非人烟稀少景象萧条的样子。因此,元代本境人口应比《元史》所载更多。但究竟有多少,尚待进一步考察。
明代 朱明王朝在土默特地区几乎没有行政建置。《明实录》载:洪武六年(1373)冬十月,“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丰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由此可知,早在明初,已将本境居民迁徙到中立府(即安徽凤阳)一带,辽、金、元以来的丰州,东胜、云内等州均弃置,仅建立若干军事据点。据《明史·地理志》载,洪武四年(1371),置东胜卫(在今托克托城一带),二十五年(1392)八月,分置东胜左、右、中、前、后五卫,次年二月即罢中、前、后三卫,到永乐元年(1403),分别徙东胜左、右卫于卢龙县和遵化县。正统元年(1436)虽复置,后仍废。另外,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云川(今和林格尔土城子)、玉林(今和林格尔新店子一带)、镇虏(今托县黑城一带)等卫,永乐元年徙治北直畿内(今晋北一带)。宣德元年(1426)还旧治,到正统十四年(1449),均废弃,卫城遂虚。
东胜、云川等卫前后两次设置,存在仅三十五年,有明一代,本境均为蒙古游牧之地。
二、土默特部人口
1368年蒙古退出中原以后,在北方继续保持其政权体系,史称北元。十四世纪后叶到十五世纪八十年代,北元的封建领主纷纷割据,不断互相攻伐、吞并,蒙古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一时期曾在本境活动而可缕指者,如永乐间的阿鲁克台,正统至景泰间的也先,天顺间的孛来,成化间的毛里孩、阿罗出、癿加恩兰等,因其迁徙不常,又无确切资料,人口状况阙如。
约当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达延汗统一蒙古,将各部分为左右翼六个万户,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土默特和永谢布。土默特万户的分地为以今土默特地区为中心,包括乌拉山前后及乌盟东部、北部的地域。在明人载籍中,凡涉及土默特者,均称之为“满官嗔”(或满官正,即蒙郭勒津)。究其原因,彼时属于土默特万户的科赛·塔布囊(即火筛),系蒙郭勒津部首领,经常与明朝冲突,如弘治七年(1494),“可汗西部大酋脱罗干之子火筛壮用事,大为边患”。弘治十三年(1500)春正月,火筛攻上谷(张家口以东,延庆以西),二月败明军于云中(今大同),七月又移师攻榆林(陕北),十一月攻偏头关⒅,直到正德年间仍有火筛与明军冲突的记载。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土默特地区和鄂尔多斯,明朝边臣几乎谈火筛而色变,如平江伯陈锐奉命征剿火筛,以屯兵不进而获罪,故而有平江伯怕火腮(筛)的笑话。正因为如此,明人在其记载中,往往以火筛、满官嗔代替土默特。对此,沈曾植在《蒙古源统笺证》中解释说:“彼(指《续文献通考》)以蒙古勒津统土默特,此(指《蒙古源流》)殆以土默特统蒙古勒津也”。史实证明,沈曾植的解释是正确的,蒙郭勒津仅是十二土默特中的一个部落。
达延汗时期土默特部的人口,《万历武功录》只是笼统地说;“西部三,曰应绍不,曰阿儿秃厮,曰满官嗔,大营二十五,众可十三万。”这里的十三万之众,是右翼三万户的兵力,属于土默特万户的有多少,尚难确定。有关土默特人口状况较明确的记载,是在阿勒坦汗成为土默特部领主之后见于史籍的。汉文史籍所载的土默特部人口,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约当嘉靖初年,阿勒坦汗成为土默特部领主,《续文献通考》说;“满官嗔部下分八营,旧属火筛,今从俺答,合为六营……众可四万”。这里的“众”,实为“控弦之士”的同意语。如以四口之家出一战士计算,嘉靖初年土默特部人口应在十六万左右。此其初期阶段的人口状况。
第二阶段,是阿勒坦汗与其兄墨尔根济农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万历武功录》说,阿勒坦汗、墨尔根济农每次入边,“大辈十万,中辈数万,少者数千”。这表明,阿勒坦汗昆仲在与明朝的冲突中,多则可动员骑兵十万越过明长城作战。《嘉靖实录》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该书“嘉靖二十年八月甲子”条载:“虏酋分道入犯。俺答阿不孩下石岭关,径趋太原。吉囊由平虏卫入。众各七八万。”明朝镇抚等官为开脱战败的责任,在向朝廷报告敌情时,故意夸大蒙古兵力是可能的。但是,土默特、鄂尔多斯起码各有五至六万兵力则不成问题。一次战役投入五万兵力,加上用于其它方面(如守卫老营、辎重、畜群等)的战士,阿勒坦汗的总兵力当在六万左右。以此计算,其人口当有二十余万。
第三阶段,即1542年墨尔根济农去世以后。当时阿勒坦汗成为右翼各部实际的领袖,势力急剧增强,中央汗庭惧其威胁,于嘉靖二十六年(1548)东徙,土默特部领地扩大,人口亦随之增多。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七月,阿勒坦汗“调众十余万”。于八月发动了包围明都北京的“庚戌之役”。此役之后,土默特部愈加强盛,《明史纪事本末》说:嘉靖三十二年(1553)冬十月,“朵颜纠俺答众二十万薄古北口,烽火达京师”。三十六年(1557)秋八月,“俺答众二十万入雁门塞”。这里的十余万、二十万,当然包括从鄂尔多斯、哈剌慎等部调集的骑兵,但主力无疑是土默特骑兵。《明史纪事本末》说“俺答强盛,有骑十余万”。这个数字是比较切合实际的。照此计算。1550年前后,土默特部的总人口当在四十万左右。为了说明这个估计是否切合实际,下面引用明人的有关记载,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隆庆四年(1570),阿勒坦汗与明朝达成贡市协议,次年接受明朝的顺义王封爵。其时是土默特部的鼎盛时期,其人口,《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载有赵全等人被缚送明廷后的如下供词:
“黄台吉可七千,摆腰可二千,兀慎可一千,居野马川、鸽子堂,乡天城、阳和、怀安、万全右卫,去边五十余里……
委兀儿慎,可一万,居大青山。
多罗土蛮,可一万,居黄河西北,乡神木。
俺答可二万,躬提兵七千,居丰州滩,去老营堡、平虏、威远、右卫可三百余里。而以三千属打儿汉倘不浪,以一千属火屯倘不浪,去老营边可六百里。以五百属莽兀十倘不浪、淮折汉倘不浪、王八屯儿,去平虏边可五百里。以二千属出浪那言,去平虏边可四百里。以一千五百属歹臣倘不浪,以五百属打儿汉,以五百属土儿箇,去平虏可五百余里。以五百属脱脱儿墨,去偏头关可二百余里。以二千属恰台吉,去右卫可百里。以五百属青山哑拜倘不浪、宰散倘不浪,去右卫可三百余里。以一千属把里台吉,兵兔台吉,去右卫六百里。以五百属我的户倘不浪,去右卫五百里。以五百属打腊台古,去右卫以西可三百余里。以三百属真武窟儿、把都儿倘不浪,去右卫以东可六百余里。”
以上共计控弦之士五万一千三百名。这个数字是可信的。明隆庆朝首辅高拱的《伏戎纪事》记载了明朝审讯赵全、李自馨等人的过程,说“活口幸在,乃不得一尽虏情,亦可惜也。于是选伶俐晓事卫经历九人,使入狱中”,“向以虏之……将领几人,是何姓名,年记各若干,所领人马各若干;某强某弱,某与某同心,某与某有隙;其所计欲如何,中国如何可以制伏,以及纤息动静皆问之。日各书一纸来……至得虏情甚悉,至今封存焉。”高拱还记载了赵全“对簿”时的态度。赵承认自己“在虏用事多年也曾替他(指阿勒坦汗)掠地攻城,使他大得志……我孝顺他,可谓至矣。今乃为他一个孩子,将我等绑缚而来,不如蒿草,无恩至此,我恨不得食其肉”。据此可知,赵全等所供“虏情”当无保留,可惜高书未载详情。而《万历武功录》的作者瞿九思显然没有见到封存的审讯档案,因而他所记载的“供词”既不完全,也有失实之处。瞿书供词中仅列出十二土默特的摆腰、兀慎、委兀儿慎、多罗土蛮四部,隐约提及把林、打剌二部,其余各部,如蒙郭勒津、王吉剌(鸿吉拉特)、兀鲁、毛明安、布喀勒斯、杭锦等均未涉及。供词所列阿勒坦汗直隶的各酋长,住牧地多在老营堡、右卫(今右玉县)以北,阿勒坦汗大本营范围之内,即今之土默特地区。而把林部在“阳和(今阳高)正北山后歹颜那失机住牧,离边五百里”,打剌部在“得胜堡边外垛兰我肯山后住牧,离边三百里”⒆。且作为一个部落,打剌也不可能仅有五百名战士。所以,土默特部全盛时期的人口,应把上列各部考虑在内,以每部一千名战士计,上述五万一千名之外还应加上七千名。此其一。其二,《明史纪事本末·俺答封贡》载:“俺答老矣,娶二妾,弃其妻,黄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俺答予万骑自备”。阿勒坦汗晚年所娶二妾,其一即《万历武功录》所谓“俺答酋妇转爪,”《阿勒坦汗传》所谓“钟金哈屯”,即三娘子。黄台吉因其父“居恒偏爱后妻”,父子间因“不相能”而“心愈疑”,曾说“老婢子(指俺答)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据此,阿勒坦汗给三娘子等万骑用以自卫,当系情理中事。其三,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开始,土默特部众就已西迁,当时俺答“羡青海富饶”遂“携子宾兔(系鄂尔多斯领主之一,阿勒坦汗侄孙)、兵兔等数万众,袭据共地”⒇。此后,右翼三部继续西迁青海一带。西迁的部众被称作“鞑靼土默特”。《神宗实录》万历六年十二月癸卯条载:“巡按陕西御史赵辑题:虏之盘踞西海,日与番僧溺志焚诵,并无回巢消息。部落八万有奇逐水草,而乘机刁抢往往而有。”到十七世纪初,住牧西海地区的人数更多,据载,“海部兄弟八支,兵数十万”(21)。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大,兵力达不到数十万,人口有十数万则是可能的。其四,嘉靖中,土默特部众开始向东扩展,逐渐形成以赶兔(噶尔图)及其母大嬖只(大比吉)为首领的兀爱营。该营人数虽不详,但从清初所建土默特左、右两旗看,左旗八十佐领,右旗九十七佐领,共一百七十七佐领,兵丁达二万六千五百余名,人口约十三万多,其中虽半数以上为兀良哈人,亦足见明代东迁的土默特人数(蒙郭勒津、巴岳特等部)甚多,否则,土默特左旗怎么会有蒙郭勒津旗的别称呢?
综上所述,以土默特地区为中心,西至青海一带,东至满套儿(今丰宁县)—带,土默特控弦之士当在十万名左右,总人口约四十万,这个数字的估算并不过份。
另外,前述赵全供词说:“大小板升汉人可五万余人”。这是1570年的数字,到万历十一年(1583),明兵科给事中王亮在其条陈中说:“板升夷(华)人众至十万”,“板升之人终不可驯,宜酌量审处”(22)。这尽管是个概数,但是板升华人加上在蒙古各户充当仆役及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匠人,十万之数并不夸大。故而除去迁徙至西海、辽蓟一带的部众不计外,土默特部众的总人口(包括汉族)亦有四十万左右。正是由于人口众多,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相当发达,为土默特部的强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和人力基础,因而土默特部才成为十六世纪中国北方举足轻重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三、清代土默特地区人口
十六世纪末,土默特部逐渐由强盛走向衰弱,特别是扯力克汗卒后,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王)位公开分裂。1613年,博硕克图(卜石兔)虽袭汗(王)位,却“号令不行诸部”,阿勒坦汗时期土默特部所向披靡的雄风已不复存在。崇祯元年(1628),察哈尔部林丹汗西征,土默特部被击溃,博硕克图汗逃至鄂尔多斯,不久去世,部众除逃匿者外,均役属于林丹汗。四年以后,即崇祯五年(1632),后金皇太极率满洲军西击察哈尔部,林丹汗“尽驱归化城富民、牲畜渡河西奔”,后金遂占据土默特地区。
从1628年至1632年的五年间,本地区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战争破坏。土默特部在受到林丹汗打击之初,即有相当多的部众避匿山间或者东徙,与兀爱营的部众会合。林丹汗西奔时究竟有多少人被裹挟西去不得而知。后金占据本境后,皇太极下令“烧绝板升”,灾难更为严重,奔逃者当为数更多。王氏《东华录》说:皇太极“驻跸归化城,居民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被俘者有多少也不得而知,他们是沦为满洲奴隶,还是给还了归降后金的土默特封建领主,史无确载。关于归附者,《归绥识略》、清编《土默特旗志》说:“天聪六年(1632),大军征察哈尔,以林丹汗西奔唐古特,移师归化城,博硕克图汗子俄木布及其头目古禄格、杭高、托博克等集众降”。《蒙古源流》也说:“土默特所余之大小诸诺延,收聚举国之众(降)……均依次加恩有差。”这里的“集众”,“收聚”,显然是招集逃匿各处的部众降附满洲。所集之众的数量,王氏《东华录》载:天聪九年(1635),“分土默特壮丁三千三百七十多名为十队,每队以官二主之”。崇德元年(1636),清廷在土默特编旗设佐,仍以上述三千三百余丁编为二十佐领。可见清初土默特两翼的全部兵丁仅有此数。以每丁五口计,两翼总人口约为—万六千余人。至于板升华人,史籍虽不载其命运如何,大约也不外被掳或逃亡,所存无多。这就是明末清初土默特地区的人口状况。
清代,以崇德元年为起点,到乾隆七年(1742),这百余年间是土默特两翼人口的恢复上升时期。从现存土默特历史文献档案中可知,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土默特两翼佐领已由二十个增加到四十四个,仍以每佐一百五十丁,五口之家出—丁计算, 总人口当为三万三千余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由台吉家仆增编勋旧佐领三个,次年将浩齐特二个佐领编入右翼,康熙四十六年(1707),又将无量寺等七大寺黑徒编为十三个公中佐领,两翼佐领数达到六十二个。按前述方法计算,共计兵丁九千三百名,总人口当为四万六千余人。根据以上资料,将土默特两翼人口增长情况列如下表:
年代
佐领数
丁数
人口(估)
备注
1636
20
3370
16850
原编佐领数
康熙中
44
6600
33000
人口增殖编为二十二佐领
1694
47
7050
35250
台吉家仆编为三佐领
1695
49
7350
36750
编入浩齐特二佐领
1708
62
9300
46500
十五寺黑徒编为十三佐领
以上人口估算与实际可能有出入,如兵丁一项,按清朝对土默特两翼的定制,额设甲兵五千名,壮丁、幼丁三千八百名,共计八千八百名,人口当为四万四千余人,但这个人口数中不包括喇嘛、沙比纳尔及副户(即不出壮丁的旗民)。据乾隆七年(1729)十月,建威将军补熙、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归化城都统班达尔计等给朝廷的奏疏中说:“土默特两翼额甲五千名,壮丁、幼丁三千八百名,出征年老、残废退甲人等并其妻子、寡妇、孤子家口,以及喇嘛、沙比纳尔共六万余口。”应该说,这才是当时土默特两翼的实际人口。与清初的二万余口(将喇嘛、沙比纳尔等包括在内)比,总人口约增长二倍。
土默特人口增长的原因,一是入清以来,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促使“生齿众多”;二是明末大动乱中逃避他方的部众陆续归来;三是编入部分别部落(如浩齐特)部众。土默特两翼人口的发展,也是清康、雍、乾三朝鼎盛的一种反映。
从乾隆中年开始,土默特两翼人口渐呈下降趋势,可惜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各朝人口状况无记载可资参证,但光绪年间有关土默特两翼人口的记载亦足可说明问题。俄国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载:“土默特行政机构所保存的比较准确和肯定的人丁资料只有应征参加军训、检阅或其他活动的旗人的数字……计有:
左翼
各甲兰管辖的苏木 户数 人口
由第一扎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337 1572
由第二扎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287 1331
由第三扎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475 2595
由第四扎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267 1229
由第五扎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361 1573
由第六扎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226 988
右翼
由第一扎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304 1449
由第二扎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441 801
由第三扎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397 1614
由第四扎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292 1321
由第五扎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289 1227
由第六扎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420 1900
总计左翼的三十个苏木有一千九百五十三户,九千二百六十八人;右翼的三十个苏木有二千一百四十三户,九千三百零八人。
呼和浩特土默特旗总人数为四千零九十六户,一万八千五百七十六人。”
“上述的人口数字—万八千五百七十六人——是所有土默特旗民的数字,无论是定居的还是游牧的,男女老幼都包括在内。这个数字是我从关于1887年人口调查的官方档案中摘出的。”
这种载于官方档案的应是正户的人口数,并不包括副户及喇嘛、沙比纳尔等。关于后一类人,波兹德涅耶夫接着说:“关于那些虽被编入军籍,但却从未被动员或服过兵役的土默特平民及沙比纳尔,我们只知道这一点,就是根据1887年的调查结果,他们的总人数为五万二千八百四十三人。这是我根据嘎兰达的谈话记下的数据。”
以上两项共计七万—千四百—十九人,比乾隆七年还多了万余人,显然是不实际的。因为按乾隆七年总人口与正户人口的比例是7:4.3,即正户占总人口的71.5%,副户、喇嘛、沙比纳尔占28.5%。按此比例,土默特两翼总人口约为二万六千余人,副户、喇嘛、沙比纳尔当为七千五日余人,而不是五万二千余人。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呢?首先,嘎兰达(参领)的口述不足为凭,他向外国人介绍本旗人口,可能故意有所夸张,以示本旗的兴盛。其次,按清制,旗民中的健康男子,凡适龄者均隶军籍,既隶军籍,就不可能不服兵役,只有喇嘛、沙比纳尔例外。再次,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以各召黑徒编为十三个佐领后,沙比纳尔逐渐减少。当时黑徒共三千五百八十人,其中的一千九百五十人编入佐领,留在各召的还剩一千六百三十人,以每户四口人计算,共约六千五百余人。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无量、延寿、广化等十五寺黑徒仅有七百六十九人,连同其家口,也不过约二千八百人左右,即使加上其它各召黑徒及共家口,也不足四千人。可见沙比纳尔减少甚多。另外,喇嘛也有所减少,如宁棋寺(太平召)原有喇嘛八十余名,嘉庆二十四年仅剩五十名;崇寿寺(朋顺召)清初有喇嘛一百五十名,嘉庆二十四年仅剩七十八名,平均减少42.7%。1819年土默特两翼全境七十四座大小寺庙共有喇嘛一千四百四十二名,较清初减少千余名。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蒙古及蒙古人》所谓“未被动员或服过兵役的土默特平民及沙比纳尔”的“总人数为五万二千八百四十三人”的记载是不符合实际的。
清末土默特两翼人口,清编《土默特旗志》亦有记载。该书载:土默特“左翼所统共户千六百四十有九,职官至甲兵男妇幼丁共口七千七百三十有六;右翼所统共户千七百有四十,职官至甲兵及男妇幼丁共口七千八百六十有四。综计三千三百八十九户,一万五千六百名口。”这是正户人口总数,若加上副户及喇嘛、沙比纳尔(仍以28.5%计),总人口当在二万一千左右。这大约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编修该志书时的统计数字,上距1887年仅二十年,二十年间土默特左翼减少三百零四户,—千五百三十二人;右翼减少四百零三户,一千四百四十四人。共计减少七百零七户,占17.26%,二千九百七十六人,占16.02%。甚至连《土默特旗志》的修纂者也发出这样的慨叹:“国初以来蒙人亦繁盛矣。当日兴师遣戍常以千计。举数百里之众,生养休息二百六十余年,椒聊瓜瓞,当如何绵绵继继,蕃衍盈升,而今民数乃如此,以燕晋秦边鄙之民填塞于其境,枝强尾大,毋亦有可虑者乎……蒙人警焉,治蒙者思焉。”
从1742年至1887年,一百四十六年间土默特两翼人口由六万余人减至二万八千余人,锐减53.4%,年递减率为0.37%,而1887年至1906年的年递减率则为0.801%,足见其人口减少的趋势愈来愈剧烈。其人口增减情况如下图所示。
造成土默特两翼人口减少的原因很多,主要的有下列几方面:
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从清初至雍正朝,土默特两翼属众保持了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本境良好的自然条件加上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较快,因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康熙间增编佐领即为显明例证。但是,从雍正末年至乾隆朝,清廷对土默特牧场采取了大规模开垦的政策。牧场辟为农田,致使土默特的畜牧业受到致命打击,牧民被迫弃牧营农,虽然清廷曾拨给两翼旗众户口地亩,然而蒙古族既不谙耕作,又须出征、当差,遂造成“有地而不善耕耘,无畜而难以孳牧”的后果,兵丁不得不以户口地“招民垦种”,“收租以自养”,而出租土地的后果是渐致土地沦失。根本既丧,必然直接影响到蒙古族的经济生活,导致出现贫蒙。乾隆七年(1742),上距清廷大规模开垦仅仅数年,失地现象已相当严重。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的奏折中就说:土默特两翼“系在内扎萨克四十九旗之内,向来并无俸饷,俱随水草游牧生理。自康熙三十年以后,蒙古等始行耕作,其有力之人虽开垦耕种,仍赖草地滋生牲畜。从前自备鞍马,屡次出征,并每岁纳粮当差及养赡家口,甚为充裕。数年以来,牲畜消耗,地亩失时,现今生计已不比从前……又数十年来,民人聚集归化城,并携眷在各村,与蒙古种地杂处者四五十万,是以地方日窄,而蒙古生计日窘”。奏折中还列举了下列事实:两翼属众四万三千五百五十九人中(23),无地者达二千八百一十二人,地少或不足一顷者达二万四千二百六十人,土地较多者一万六千四百八十七人。无地和少地者竟占人口的三分之二,因而建威将军、山西巡抚和归化城都统才不得“不筹画经久之计”,获准重新调整户口地亩,以每口一顷分配地亩,“以作永业”。但是,开垦不已,土地继续沦失,“蒙古生计日窘”是必然的结果。例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尚有较殷实的旗丁购买女仆的现象,到嘉庆以后,此类现象已完全绝迹。诚如清编《土默特旗志》所说:“台吉而上才足自存,兵丁之属衣食多缺”。经济条件的恶化,必然对人口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土默特人口锐减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其次是差徭繁重。据《清实录》、《土默特旗志》等书载,土默特兵丁以从征打仗为首要义务,国家每有战事,往往征召土默特兵丁从征,每次千名至三千名不等。平时的差徭也很繁重,如在将军衙门、副都统衙门、旗务衙门、兵户二司、操演营、旗库、巡警营、各卡伦、渡口、城门、庙坛等处轮流值勤当差的,每月多达七千七百多人次(延寿寺、辅国公负责的卡伦守卡人员不计),加上各种临时派遣的差徭,如接送显官、护送驿递、限期缉捕人犯等等,当差的人数更多。因此,清编《土默特志》说:“兵无薪饷、全倚户口地亩且耕且牧,充当各路苦差”,形成“蒙民穷困日甚一日,种族零落,庐帐萧条”。足见繁重的差徭也是造成土默特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
再次,是出家当喇嘛。土默特蒙古一般每户有三子者必有一人出家当喇嘛,甚至有二子者亦有一人当喇嘛,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如察素齐荣氏,约当道光年间,佐领荣穆扎布兄弟三人,其兄、其第均为喇嘛,荣穆扎布七子,次子、六子也为喇嘛。据统计,乾隆年间,无量寺等七大寺共有喇嘛一千二百零九名,嘉庆末年,无量寺等十寺喇嘛也达一千四百一十七名,倘把其余六十余召的喇嘛计算在内,大约在二千五百名左右。按照佛教戒律,喇嘛是不能娶妻的,因而这也是影响土默特人口增长的因素之一。
还有一点需要述及,即灾荒、疫病及战争造成的伤亡。关于灾荒,较早的记载欠详,以光绪朝为例,光绪二年(1876),口外各厅“连年甚灾”,“饿殍遍野,蒙旗亦大饥”,“甚至有人相食者”。十七年(1891),门外各厅“冻旱成灾”,“少壮逃散,妇幼出卖,老弱饿死者大半。厅令掘大坑掩埋之,俗名曰万人坑……蒙旗饥民亦伙”。关于疫病,史书记载颇鲜,仅以同治元年(1862)为例,是年本境瘟疫流行,“归化城厅尤甚,城乡交通断绝,多有全家就毙者”。至于从征,每次均有大最伤亡,如咸丰三年(1853)三月,土默特官兵千名奉调“驰往清江浦一带”作战,次年三月,仅有七百五十名“撤回归屯”,阵殁者达四分之一。六年(1867),土默特官兵五百名调往山东作战,“冠县之役”“阵死蒙兵二百余名”,战殁者达三分之二(24)。因此,灾荒、疫病和战争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土默特人口的增长。
清代在本境居住的,还有汉族、回族和满族,分别简要介绍如下。
汉族 如前所述,明代板升华人曾达五至十万,经明末的动乱,到清初,这些人已不见于载籍。清代大量出现于本境的汉族,是十八世纪以来陆续迁来定居的。
康熙中,汉族尚无出口垦殖者,当时本境间有农耕者,亦系蒙古族。张鹏翮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奉派出使俄罗斯,曾途经本境,他的《奉使俄罗斯日记》五月十七日条载:“此二日所见蒙古,皆土屋,能耕种艺麦糜子,时方五月中,麦仅二寸”。十九日条亦载:归化城“有城郭土屋,屯垦之业,鸡、豚、麻、黍、豆、面、葱、韭之物”。足见彼时土默特蒙古有少量农业。汉族农民来本境垦殖,当始于康熙中年以后。康熙五十八年(1719)范昭逵奉命随兵部尚书勘测蒙古台站,著有《从西纪略》。当年五月十五日过杀虎口进入本境,书中载:“午余,次佛爷沟,土人进奶茶。此后所履皆蒙古地。盖归化城南间有山、陕人杂处,而归化以北,更无华民矣”,但在麦大力庙(即美岱召)一带“有陕人于此种地”。由此可知,到康熙末年,已逐渐有山西,陕西两省汉族农民来本境垦殖,人数不多,仅只“间有”而已。
首先进入本境的汉族系商人。《奉使俄罗斯日记》载:“外番贸易者,络绎于此,而中外之货亦毕集”,“归化城外番贸易,蜂集蚁屯”。可见康熙二十七年,内地商人已云集归化城,与外藩蒙古进行贸易,因而才有“中外之货毕集”,贸易者“蜂集蚁屯”的景象。乾隆七年喀尔吉善等的奏折所说的“康熙三十年以后……民人聚集归化城贸易,并携眷在各村,与蒙古杂处种地”,为张鹏翮的记载作了很好的注脚。
张鹏翮在《奉使日记》中曾向清廷建议;“归化城……乃冲剧扼要之地,控制之法良不可忽……即如台湾远在海外,亦为郡县。应照此例,将归化城亦设为郡县……将死罪中可免之人,发往开垦,填实地方”,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更遐荒之区为冠裳之地,增版宇而广圣化,度越古帝王远矣”。清廷是否采纳了这一建议,未见载籍,但以后清廷对本境的开垦措施,基本是照此进行的。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在黑河、浑津圈地设立粮庄,接着允许口里农民以“跑青牛犋”的形式出边垦殖。雍正元年(1723),清世宗下诏谕:“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不得阻挠”。雍正十三年(1735),清廷派尚书通智前来归化城督办开垦事宜,当年,土默特左翼都统丹津便“奏请”开垦土默特牧场四万顷,接着大规模招民开垦大粮官地,于是晋、陕农民蜂拥而至,数年之间,包括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内,人数已达四五十万。这虽是一个概数,但已足证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汉族徙来本境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因而才有喀尔吉善等惊呼“地方日窄,而蒙古生计日窘”,担心若“不为筹画经久之计,恐将来穷蹙日甚,殊费周章”。事实上,清朝统治者并未认真筹画经久之计,到光绪年间,据《蒙古及蒙古人》记载,即使是大青山后,也有“一些汉族商人和农户来到这些土默特游牧区安家落户,而且据说人数每年都在剧增”。由此可知,到清季,所有土默特牧场均已被垦殖。由于乾隆以来年年都有汉族迁来,要统计精确的人数几乎不可能。这里列举的,是清末的数字,有些还是估计数,故而只能作参考。
光绪末年编修的《归绥道志》所载本境各厅人口如下:
“归化城厅户口:
本城五路除召庙、衙署、公所、空房、空门、蒙古不计人口外,所有铺房居民人等,男女大小共二万七千二百八十八名(此现在册)。
本城八十一街,设立街长八十一名,牌长三百三十一名,共计三百三十牌,计三千一十七户,男一万五千二十三名,女八千二百七十九口。以上男女共二万四千八百零二名口(光绪二十二年册)。
四乡共三百零七村,设立村长一百二十名,牌长七百七十八名,共七百七十八牌,计七千六百七十八户,男四万八千五百八十六名,女二万七千九百八十九口。以上共男女七万六千五百七十五名口(光绪二十二年册)。”
“萨拉齐厅户口:
一城四乡三百三十七村,汉回民人三十余万,包头一城四乡二百七十七村,汉回民人二十余万。通共境治人民约六十万,兼辖蒙民并洋人及奉教之人俱不在数内。”
“托克托厅户口:
本厅治铺户共积八十一家,铺伙二千六百五十五名,住户二千八百八十三户,男妇大小二万四千三百九十三名。
河口镇铺户共积九十二户,铺伙二千八百三十二名,住户九百二十户,男妇大小六千二百六十名。
四乡户口共积二百五十五村,共积住户七千零一十三户,男妇大小五万六千七百名。”
“和林厅现在住户考;
八千八百七十六户,男女大小五万五千—百四丁口”。
“清水河厅户口;
本街分为四甲四十八牌,计四百七十六户,男一千一百九十六丁,女九百八十五口。
四乡分为七十四甲六百九十三牌,计六千九百二十一户,男二万零一百八十—丁,女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五口”。
上引资料中,除萨拉齐厅和包头镇户口外,各厅户口当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或稍后登记在册之户口。清廷于光绪十年(1884)对本境寄民编籍后,为科敛赋役,对户籍管理较前严格,因而户口数还是相对真实的。当然,编籍并不限制人口迁徙,迁入本境的流民(即无籍之民和无业之民)当不在少数,因而实际人口可能要比《归绥道志》所载多。至于该书对萨拉齐和包头镇人口的记载,显系估计,且高估甚多。据1942年编写的《包头市志》(未刊)载:道光十四年(1834)该镇人口总数为一千五百户,一万零四百九十人。三十六年后的同治九年(1870),增长为二千八百户,二万五千人,年平均增长3.58%。照此计算,到光绪三十二年,包头人口当在三万二千至四万人左右。萨拉齐厅人口虽有增长,但总不及新兴的商业城镇包头的增长幅度大,即使按包头人口增长速度计算,其人口亦不会超出十至十二万。至于武川,光绪二十九年虽已设厅,但所治包括四子王、达尔汉贝勒、茂明安三旗境内之民人,在土默特两翼境内者约万余人,其余本文未加抄录。总之,清末本境汉族人口数虽有统计,但很不精确,如萨拉齐厅(包括包头)仅概说四十余万,大约与实际人口数颇有差距,比较客观地估计,全境人口当在六七十万之间。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天灾人祸,即使是已编籍的民人流徙量也很大。如清水河厅乾隆年间人口已达一万六千余口,此后历年均有增加。但“因所垦熟地或被风刮,或被水冲”,“口内招徕之民逃回原籍者实繁”,光绪八年(1882)编查户口,仅得—万四千余人。因而上述人口数只能反映本境汉族人口的大略情况。
满族 女真族最早涉足本境,是在1632年,当时后金皇太极率满洲兵征讨林丹汗,占据了归化城。自此之后,后金(清)即委派要员(如贝勒岳脱、归化城将军费扬古等)常驻于此,负责防务并监督土默特两翼官民。雍正末年,清廷兴建绥远城,工竣之后,于乾隆四年(1739)将右卫八旗官兵及其家属移驻城内。绥远城系驻军营垒,最初共有满洲、蒙古、汉军三千九百名,其后驻防兵数次变更,如乾隆十二年(1747)拨八旗开户兵二千四百名于直隶、山西,调京城满洲兵一千二百并余丁五百名充补兵额。二十五年(1760)改驻防兵额,设步军、养育兵各四百名。二十九年裁撤汉军,分拨直隶、山西改补绿旗营,到乾隆三十年(1765)该城兵额始定,“实存兵二千七百名,内领催、前锋、马甲二千名,步兵四百名,养育兵三百名”。八旗男妇子女数目:男四千三百六十一名,妇三千六百一十五名,子一千五百九十六名,女二千一百五十五名”,“共一万些千八百二十七名”(25)。迄清之世,绥远城满族人口基本保持了这个数目。
回族 回族,史称回回。回族在本境的活动,历史颇久。元代的丰州即有回族生息,如陕西行台御史瞻思即为丰州人。明代有关回族在本境的活动情况,史无确载,但十五世纪中叶,也先曾据有本境,其商队由回回主持,在与明朝的贸易中,往来本境当系情理中事。其后,原在新疆北部游牧的蒙古野乜克力部首领,如伊思满(即伊思马因)、亦卜剌(即易卜拉欣)、癿加思兰等率众东徙,先后在本境及周围地区活动数十年。从上述酋长的名字看,他们显系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他们率众东来,很可能其中就有若干回回。《万历武功录》载,十六世纪四十年代,阿勒坦汗曾令所部“往钞应绍堡回子”。由此可以推知,回族确曾于明代在本境活动。
入清以后,随着本境商业的繁荣,回族逐渐定居于此,从事商业、农业的均有。回族之徙来本境,主要有如下几个来源。其一,康熙间,归化城、张家口形成口外两大贸易基地,准噶尔等部与清朝贸易的商队,大部分由回回组成,经常居住归化城的回族约三百余人。清朝与噶尔丹的战争爆发后,清廷曾下令遣返张、归二地回回,其中部分不愿离去者,定居于归化城。据载,当时包括由张家口迁来的,归化城约有回族二百余人。其二,乾隆间,新疆回族数千人随清军来到呼和浩特(一说为护送香妃留居于此,清廷赐其一马之地),其中的一部分人定居于八拜村。其三,陕西大荔、长安及河北等地的回族,因商业活动迁徙于本境。其四,同治年间,宁夏回族起义后,甘肃灵武、金积、平凉等处回族为躲避清军的杀戮,相率避乱迁来本境。回族因职业关系,一般居住于商业发达的城镇,因载籍较少记载,其人口状况不甚清楚。《归绥道志》仅载托克托城回民四十九户,河口镇六户,两地共有回民一百六十七人,其余各厅则多与汉族统计在一起。据近来的一些探讨性文章,清末呼和浩特有回族约三千人,包头回族约二千人,察素齐回族十六户,约百人,萨拉齐回族当数倍于此。此外可可依力更、和林格尔等处也有一些回族居住。总计本境回族,大约有五千余人。
四、民国以来本境人口状况
蒙古族 民国建立以后,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绥远军政长官频繁更换,以土默特旗为例,1915年至1928年的十四年间,先后调换十一任总管,平均任期仅一年又三个月。这些总管多为各系军阀派到土默特旗的代理人,他们只知秉承绥远都统旨意,大肆科敛赋税,充实宦囊,对旗政建设弃置不顾,因而长期未进行户口登记。直到1928年7月满泰接任总管之后,才在全旗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较为认真的户口调查。1931年至1932年,由比丁处按左右两翼,以甲、佐为单位进行的户口调查,计有参领、佐领、骁骑校、官员数、领催数、村数、户数、披甲、闲散、妇女、幼童、总计等十二项。调查之后形成两种表册(姑且称之为甲种、乙种),甲种是呈报蒙藏委员会的,乙种大约是留作施政参考的内部资料。两种表册的数据差距颇大,如甲种表册所列左翼“男妇老幼共二万六千三百九十一名”,右翼“男妇老幼共二万九千八百四十五名”,“左右两翼总数五万六千二百三十六名”(26)。而乙种表册所列全旗人口则成为一万七千九百零七名,比前者少了两倍多。为便于参阅,兹将两种表册的数据列表附后(见表—…)。
两种表册的数据,哪种可靠呢?笔者以为乙种反映的是当时土默特旗人口的真实情况,为什么呢?满泰出任总管后,一改以往旗署重要职务(如秘书长、副官长等)由客籍人士担任的局面,秘书长、科长及一二等科员全由本旗蒙族担任,为了本旗利益(如扩大声势,争取国大代表名额乃至维护旗制等),而有意扩大人口数,甲种表册大约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说乙种表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全旗的人口状况,因为该表是依据各佐的上报资料综合而成的,册内载有各村披甲、闲散、妇女、幼童详细数字,而甲种表册则无。此其一。其二乙种表册所载入口数,与清末两翼人口数相比,二者不相上下,基本一致。其三,即使土默特旗人口有所发展,也不可能在短短的二十年间由二万余猛增到五万六千余人,更何况民国以来土默特蒙古人口根本没有增长,而是继续处于下降趋势。
造成上默特蒙古族人口继续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一,多数蒙古族更趋赤贫化,如民国四年(1915)开始颁发的“乙卯大照”,使众多蒙古族户口地地权丧失,从而生计顿失。其二,绥远军阀当局的赋敛苛重,仅差徭一项,土默特蒙古即被迫支应旗县两重摊派,在“一羊二皮”盘剥下,不少人“髓尽力枯”而破产。其三,天灾人祸的侵袭,如1929年的绥远大灾,蒙古族冻饿而死者,出卖子女者,瘟疫夺去生命者为数甚多,加之土匪遍地,“蒙民稍有资产者,莫不受到刁抢”,使其亦陷入贫困境地。其四,绥远境内广种鸦片,染有烟瘾的蒙古族变卖家产者也往往而有。有此数端,蒙古族人口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从附表一亦可看到,个别佐领所辖十余村,统共才三十五人,足见人口萧条到了何种程度。
1931年以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土默特旗未进行人口调查。1945年9月土默特旗政府着手复员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发放国民身份证,同时进行户籍登记。可惜这次户籍登记资料未能全部保存下来,目前所见到的已残缺不全。1947年蒙藏委员会曾派出西盟调查组,对土默特旗进行全面调查,其《调查报告》所载人口数,大约就是利用了土旗政府的户口登记资料,当时全旗人口为二万九千八百九十七名(详见表二)。
上列人口数比1931年的人口数多万余名,单从数字看,土默特旗人口增长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据载,口肯板升村1925年尚有蒙古族十五户,到1933年却仅剩二户。这并非绝无仅有的事例,据笔者调查,解放前土默特蒙古绝户者的比例,往往是同村汉族的数倍。仅这一个侧面亦足可反映土默特蒙古族人口减少的状况。其原因仍如前述诸条,只是有所加剧而已。那么,为什么表二所列人口数反而增多了呢?除了统计欠精确的因素而外,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日伪时期,将归化城、和林格尔、八十家子、五十家子、新店子、萨禄庆等驿站的站户八百余人划归土默特旗管辖。二是日寇投降后,公主府蒙古族数百人加入土默特旗籍。三是原伪蒙古军官兵,在日寇投降后,有的落籍于本境。
据1950年初统计,土默特旗共有二万五千余人,其中包括召河地区的三千余名汉族,蒙古族实为二万一千余人。与1947年相比,增加近三千人。原因大约与战争有关,如有的在别地驻防,部队溃散后回旗及别旗蒙古族入籍等,
汉族 民国以来,土默特地区汉族人口仍处上升趋势,个别地方较清代增长幅度还大。民国初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很零散,比较系统记载本境各县人口的是《绥远概况》和《绥远分县调查概要》。兹据两书资料列如表三:
上表仅能概略反映各县人口状况,其统计资料并不怎么准确,如萨拉齐县人口两书竟相差十七万余人,归绥县1932年比1934年少七万余人,而该县1937年以各乡为单位进行的人口统计,全县共149164人(缺山区救国、泽民二乡),较1932年又少三万余人。短时间内人口增减幅度如此巨大,似乎不大可能,唯一的解释是统计的不精确。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本境汉族曾有迁徒,据统计,总人口较三十年代有所减少(详见表四)
回族 1912年以来,土默特地区回族较清代更趋集中,主要聚居于通衢大邑,如呼和浩特、包头两市,以及铁路沿线的萨拉齐、察素齐等城镇,而另一些地方随着商业、运输业的萧条,回族逐渐迁往他处,如河口镇、善岱等地即是如此。有关本境回族人口的资料不多,仅以呼包两地为例述录于此。据《归绥县志》载,1932年全县回族二千四百三十七户,共计九千七百四十八人,主要聚居于呼和浩特旧城,察素齐、毕克齐也有分布。到1949年,呼和浩特回族共约八千三百余人。包头回族,据《包头市志》(未刊)载,1937年全城有二千九百九十八人,到1942年增至四千六百零一人。1942年至1949年,萨拉齐回族由一千一百四十一人减为六百四十人。而包头则增到五千一百七十九人,总之,到全国解放前夕,本境回族约为一万五千人左右。
满族 民国肇建以后,本境满族人民经历了较其他民族更为坎坷的历程。居住于绥远城的满族困顿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驻防八旗官兵及其家属赖以生活的俸饷取消,向来当兵吃皇粮的满洲兵丁身无长技,殷实者尚可靠典当度日,一般人只能充当苦力或作小商小贩勉强糊口,连妇女也走出家门,有替人充当褓姆者,也有加入“缝穷队”的,生活艰难不言而喻。1928—1929年绥远大灾时,满族生活更趋困难,除部分妇孺被人贩子贩卖他乡外,当时掀起“回老家”的热潮,相当一部分人拖家携口跑回东北谋生,另外一些人则离开世代居住的新城,流落他乡,包头、萨县、武川等处均有少量满族散居。
二是清朝被推翻后,社会舆论认为中国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侮,均系清朝造成,因而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迁怒于满族,满族群众在政治上受歧视,精神上受压抑,因而相当一部分人将其民族成分改为汉族。
正因为如此,本境满族人口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据统计,1953年居住于新城的满族仅一千七百余人,可以相见,1949年其人口当不超过一千五百人,加上散居本境各地的满族,总数亦不足两千人,约为清代人口的六分之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土默特地区人口的这样几个特点:
1、本境在历史上既是北方民族活动的大舞台,也是他们与中原王朝发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的重要地区。随着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力量的消长,不同历史时期本境的主体民族亦不同。匈奴、华夏(即汉族)、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均曾为本境主体民族,时间长短不一,一般为百余年至数百年。十三世纪元朝建立以后,蒙古族成为本境主体民族,历七百余年未变。
2、从历史发展看,本境主体民族不论为何族,居民均以各族杂居形式生息,如汉代的汉与匈奴,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敕勒、匈奴和汉,唐代的突厥与汉、沙陀等,辽代的契丹、汉,金代的女真、契丹、汉等,元代的蒙古、色目(包括回回)、汉等族,都是杂处一地。而本境蒙、汉、回、满杂居局面,肇始于清朝前期,1884年口外七厅改制,寄民编查户籍,最终以官方承认的形式将汉回等族在本境的居住权肯定下来。
3、从十八世纪开始,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三百余年间,由于统治阶级的掠夺,土默特蒙古的经济生活每况愈下,进而造成人口锐减。特别是经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数十年的黑暗统治,土默特蒙古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人口更趋减少。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民族关系上受岐视,是本境各少数民族在旧社会的共同遭遇,其人口不发展甚至减少,是旧社会造成的恶果之—。
4、与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汉族人口从清至民国基本处于上升状态。这并不是说汉族人民遭受的压迫、剥削不严重,相反,他们是反动统治阶级科敛赋役的主要对象,穷苦劳动人民死于天灾人祸者甚众,绝户者亦颇多,但其人口不断得到补充,主要形式是从内地不断徙来,故而人口数量始终处于上升状态,数量通常是蒙古族的数十倍。
5、本境人口构成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男多女少。男女比例汉族为1.2:1~1.4:1,蒙古族则为1.3:1~1.5:1。只有特殊时期男女成反比例,如解放战争时期,萨拉齐十八至三十五岁年龄段的男女比例为1:1.2。原因是国民党绥远当局大肆抓兵,使许多青壮年男子被抓或者逃亡,当时整个土默川均是这种情况。
6、在人口素质方面,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稍有文化者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偏僻地区比例更低。另外由于卫生条件极差,疾病流行,加之吸食鸦片者较多,各族群众健康状况很差,平均寿命不足四十岁。这也是旧社会造成的恶果之—。
一九九O年五月至九月四日
注释
1、《史记·匈奴列传》
2、3《汉书·匈奴列传》
4、《晋书·北狄传》
5、见《后汉书·南匈奴传》
6、《史记·赵世家》
7、《史记·匈奴列传》
8、《晋书·地理志上》
9、《绥远通志稿》卷一上
10、《隋书·突厥传》
11、《旧唐书·突劂传上》
12、《旧唐书·突劂传上》
13、《新唐书·回鹘传》
14、《新唐书·沙陀传》
15、见《新唐书·地理志三》,《旧唐书·地理志二》曰:“云州……乾元元年(758)复为云州,领县一,户七十三,口五百六十一。”
16、《新唐书·地理志》曰:“金河,中,天宝四年置,本后魏道武所都,有云伽关……”据此,金河县应在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一带。而《中国历史地图集》则将金河县标在今托克托城以北黑河东岸。孰是?待考。
17、《辽史·太祖本纪》
18、《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
19、《北虏风俗·世系表》
20、《明史·西域二》
21、《崇祯长编》
22、《神宗实录》万历十一年九月甲辰条
23、此当为土默特两翼正户人口
24、见《清季蒙古实录》
25、《绥远旗志》
26、甲种表册的人口总数内,将三百六名领催统计在内,而领催是包括在披甲数内的,显重复,另外计算亦有误,按各佐披甲、闲散、妇女、幼童数相加,左翼26200人,右翼29692人,总计55892人,不是56236人。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