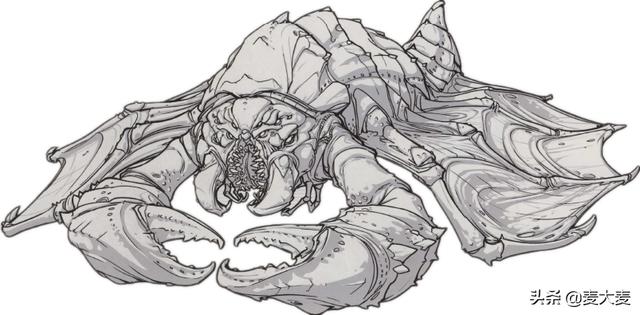李泽厚蒲公英这小野花鲜亮(李泽厚蒲公英这小野花鲜亮)

又到了拔蒲公英的季节。
蒲公英给我最早的印象,是吴凡那幅小女孩吹蒲公英的画,还是非常年轻的时候看到的,至今印象犹存。可见,蒲公英给我的感觉很好。
但在美国后院要拔除的蒲公英,却是开得遍地的灿烂小黄花。这小野花鲜亮、普通、幼小,它一片片地漫布开来,尽管毫无章法,可以说是乱开一气,却使整个庭院显出一片金黄。我觉得挺好,并不难看。不过按美国住家的规矩,却必须铲除。我至今也不了解为何定要铲除的道理,总之要拔掉就是了。于是乎拔。用手,用小铲、大铲、专门制造的铲来拔。
大大出我意料的是,这小黄花的根非常坚韧,它长且粗,特别是非常的长。要把它连根铲除或拨出,非常不容易,而且是拔不胜拔。经常是累了大半天,似乎清除了一小片,第二天,就在那块认为已被根除的土地上,迎着阳光,小黄花又照样地茁壮地灿烂地开了起来,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好雇请专业人员大洒药水予以消灭,反正现代人类的科技发达。

这蒲公英的难拔使我想起五十年代下放劳动时的田间除草。除草劳动种类很多,我特别记起的是,像拔蒲公英一样,拔那长在庄稼中的野草。那野草倒不开花,但像恶霸似的躺在地面,四肢放肆伸开,长得又肥又壮。老乡说它们夺取庄稼的水分和养料,必须拔除。但拔除也不容易,虽说没拔蒲公英这么难,却也要长久蹲下身去,好费一番气力。
因此在这劳动中,我很憎恶这些难以拔除却又必须拔除的野草。
记得当年暗中想索:人们,当然包括我自己,都读过许多歌颂野草的诗文篇章,从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到鲁迅著名的野草散文集,都在赞颂野草那顽强的生命力,却从没想过这顽强的生命力恰好是庄稼和农家的死对头。所以我当时想,那些诗文和自己的喜爱确乎是由于没有干过农作耕耘,因之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距离甚远的缘故。
我非出自农家,又素不爱劳动,属于当时应下放劳动以改造思想的标准对象,对野草的爱憎不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吗?但是,我一面除野草,也信服上述理论,活儿也干得不错;一面我又仍然喜爱那“春风吹又生”和鲁迅的野草文章。我欣然接受“拥护劳动人民便应改造思想”的严密逻辑,却又依然不愿体力劳动,不愿改造和“改造”不好。
我虽从未在思想检讨会上以野草作例,证说自己改造之痛苦艰难,却的确感到我这脑子里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正如当年一再宣讲“知识分子最没知识”的经典论证是非(菜)与麦(苗)不辨,似乎很有道理,因为我的确辨不清。但又立即想到,爱因斯坦可能也分辨不清,为什么必须人人都要分辨得清呢?
当然,我并不敢说,心中嘀咕而已。

由蒲公英而想起拔野草,如今一切往矣,俱成陈迹。且回到这目前的拔蒲公英吧。除了难拔之外,它最最使我惊异的是,小黄花过不了多久就变成了圆圆的小白球。在一些郊野,它们还成了大白球。它们高耸、笔直,不摇不摆,但如果你手指稍稍一触,它便顿时粉碎。它们是失去了生命最后岁月的僵尸。它们没有树叶陪衬,没有一丝绿色,就是赤裸裸的狰狞的大白球,彼此比肩挺立在一块、一排、一片。它们与那小黄花似乎毫无干系,完全异类。
这使我非常惊骇,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爱的、美丽的、天真烂漫的小黄花竟变成了如此凶悍、绝望、疯狂的大白球了呢?太不可理解了。难道时间一过,岁月一长,就会如此么?就必须如此么?
我散步归来,天色渐黑,四野悄然,就那些白团团的大圆球顽强地竖立在那里。面对它们,我却一点也没有岁月流逝的感伤,只感到一种莫名的、真正的恐惧。“繁华如注总无凭,人间何处问多情。”可怕的大白球代替了诗样的小黄花,你于是永远也找不回那失去的柔情和美意。

(原载《明报月刊》2007年1月号)
来自 来自 李泽厚著;马群林选编. 李泽厚散文集[M]. 2018 P30-31

敬请持续关注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