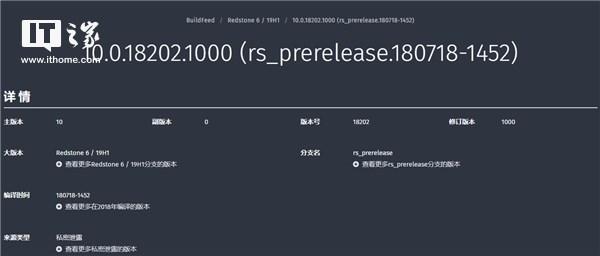冯远征的独白(表演是什么表演不是)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孙雯
“冯远征是总那么不一样的好演员,是有担当有想法的演员队长,还是与众迥异的表演教师。”
这是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对冯远征的评价,在《冯远征的表演课》这部随笔集的封面上,这句话比标题还要突出。
对于好演员冯远征的“好”,普通大众已从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电影《非诚勿扰》、话剧《茶馆》中深有体会,而这部刚面世的新作,会让我们了解作为“演员队长”和“表演教师”的身份。

《冯远征的表演课》由后浪出版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共同推出,冯远征分享了近40载戏影人生,并初次公开他在北电、上戏的授课内容。
近年来,《演员请就位》《演员的诞生》《我就是演员》《演技派》等大热竞演综艺的火热,促生了大众对“演员”“演技”等话题有的关注。

冯远征的课堂
这既源于镁光灯下台前幕后被天然的瞩目,更源于种种行业积弊下爆发的迫切呼唤——“表演是什么”“要演员不要流量” “偶像如何转型”。说起来,演员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因为,从巅峰到谷底仅一步之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冯远征的经验,是写给演员的,但又不仅仅是写给演员的。因为他说了——
这本书为什么叫《冯远征的表演课》? 第一个,我是希望名字直白,让人一听就是在讲表演;再就是不懂表演的人、喜欢表演的人,通过这本书可能学到一些表演;懂表演的人看完以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那么,表演到底是什么?
对于这个话题,那些火爆的综艺节目中,演员被导演、制片人、编剧乃至学者、媒体、剧评人、普通观众一一点评,似乎关于表演,谁都可以说上一点儿。然而演员,或许才是最懂演员的人。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如果让“演员队长”来说表演为什么叫“表演”。他认为,“表”是表面、表现、表达,“演”是演绎,用我们的外在,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感受我们的内心,再通过身体把内在的东西表达出来,就是表演。
他还抛出了自己的提醒——表演不是“演表”:“两个字颠倒一下,就是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演表”是外→外的过程。当你开始“演表”的时候,你就失掉了最动人的东西。”
如何与面向大众解读表演这件事儿,冯远征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哭戏哭不出来,导演会问,你在家里跟谁感情最好?你说姥姥。导演又问,你想不想你姥姥?她现在怎么样?你一想,就哭了。这就是真情实感,靠自己的下意识。但这种真实不是人物的真实,是演员本身情感的流露,你只是在用自己的哭或笑去完成人物的台词。这就是为什么你都演完了可能还止不住眼泪,你哭的不是人物,你哭的是自己的悲伤。”
值得一提的是《冯远征的表演课》,还特别收录了曾在微信公号上大火的《我穿墙过去》一文,讲述青年冯远征在德国求学时的往事。
这样的讲述,在书中并不缺乏,冯远征回顾了自己从跳伞运动员到专业演员,到柏林求学,再到回归心怀眷恋的北京人艺,留下松二爷、魁格、顾贞观等一个个经典形象,以娓娓道来的讲述,展示了他在舞台上、镜头前的戏影人生。

《茶馆》剧照
【抢鲜读】
1978年,还在读初中的我进入了北京业余跳伞队,梦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跳伞运动员。一直到1981年高中毕业,4年间,我每周都要去跳伞塔练习,也多次参加全国的业余跳伞比赛。
出于对跳伞的坚持,我做出了人生的第一个选择,为了参加全国的跳伞比赛而放弃高考。高中毕业考试结束后,我就背着行李进入集训队,开始了跳伞集训生活,一直到当年8月份参加全国比赛。然而,就在全国比赛结束之后,专业队的教练告诉我,因为年龄太大、体格太瘦,我不能参加专业运动员考试。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我茫然了。
在家待业的光景,我每天坚持看书,后来在哥哥的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做拉链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 门缓缓打开,国外一些流行的东西开始陆续进入国内,牛仔裤就是当时流行的服饰。做牛仔裤需要拉链,所以,我的工作可以说也是一份流行的工作。在拉链厂的一年,我结识了几位文艺爱好者,他们喜欢表演,也时常拉着我和他们一起讨论,我深深地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了。他们把我带进了艺术的世界,带入了表演行业。
当年和他们一起去参加业余文艺培训班,报名费很便宜,30块钱学3个月,1周学两次。在培训班,表演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 一扇进入艺术世界、心灵世界,和自己对话的窗。我一下子被吸引了,就像学跳伞时一样。
中学时代的我,虽然成绩很好、表现不错,但不爱说话,是一个内向的人。跳伞这项运动改变了我,它让我把内心最渴望的东西释放出来了,比如坚持、勇气、专注,它打开了我的一扇窗。而表演的这扇窗,让我感受到了一个不同于跳伞的世界。所以一打开,便喜欢上了。从那时候起,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演员。
然而,从开始学表演,“打击”就接踵而来。在那个年代,要想成为一名演员,是要靠“颜值”的。虽然后来我到联邦德国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戏剧系进修,主攻的格洛托夫斯基表演学派认为,任何人只要智商没问题,都可能成为优秀的演员。由于我那时很瘦,几乎所有教表演的老师都认为我的“形象”不好,这让我一度感到自卑,唯一让我有信心的是我的作品构思和对表演理论知识的理解。虽然是业余学表演,但我都认真对待。每次汇报演出,哪怕一次小品构思,我都会竭尽全力。
如今回过头看这段经历,过程可能有些波折,但我依然要感谢它。没有这段经历,没有最初这些对自我的认知、对艺术的实践、对人生的思考,我也不能对艺术、对表演有更深刻的爱和更深厚的领悟,也就不能成为如今的我。
在拉链厂实习一年期满正式转正的时候,我有些犹豫,因为喜欢表演,想从事表演行业。于是,思考再三,我毅然放弃了那份较为稳定的工作,一心一意地去学习表演。我知道我因为外形条件而不太被看好,但天无绝人之路,我有幸遇到了几位恩师。正当我因为不被看好而自卑的时候,我的跳伞队教练跟我说,要学表演就去找他姐姐,谁知道他姐姐便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钮心慈老师。我跟钮老师说,我不行,干不了。她就鼓励我,说我条件挺好的,很有自己的个性,学表演、当演员不一定形象好才行。
在中戏我还结识了表演系教声乐的宋世珍老师,跟她免费学习了2年。在我最心灰意冷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教了你这么长时间,你要放弃吗?一个人要有追求,你可能干不成演员,但学了一样就要学好。你回去好好想想,3天之后,如果决定不学,那就不要再来了;如果决定继续学,那你就再来。”3天之后,我对宋老师说,我要继续学!
1984年,我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这一场考试不但经历了一些波折,也悄悄为我的艺术之路开启了一扇大门。
那时大家推测谁能过初试、复试、三试,我依然是不被列入通过名单的人,但一想到有老师们的鼓励,我就信心满满。顺利通过初试后,就期待着复试了。参加复试的时候,我坐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当老师喊我的时候,我却没听见。最后才知道,老师喊我的意思是让我下一组第一个考。我一想,上一组我排最后一个比较沾光,如果是下一组考的话,就是第一个。我们考生都不想第一个上,因为感觉比较吃亏。但没办法,老师说上一组叫完了,只能等休息后的下一组。一个小时后,我第一个进去复试。老师介绍了一下考场规则,我就开始了。
复试的科目有四项:朗诵、声乐、形体和小品。我朗诵的是一首叙事诗,准备得很充分,诗也很拿手,朗诵得声泪俱下的时候,一个老师喊了停,我说我还没朗诵完,老师说可以了。考声乐的时候,我唱了一首《驼铃》,越唱心里越难受,到唱副歌的时候,我就停了下来。老师就问我,怎么不唱了?我小声说了一句,我不想唱了。老师说,你可以唱上去,唱一个高音听听,我就说我不想唱了。老师也感到有些无奈,只好作罢。考形体的时候,我展示了一套广播体操,老师就让我下去了。我旁边坐的第二个考生是一个女生,等她前三项考试完后,老师就让我跟她一起表演小品,小品名叫《重逢》,时间、地点、人物关系让我们自己思考、自己表演,第三个考生复试完我们就上场。时间很紧,在我们讨论怎么设定场景、情境的时候,我灵光一现,想到我之前看过很多关于知青的书, 就跟她建议我们可以表演一个知青返城的故事。那个小品听说反响很好,很多考生都隔着门缝看,我更有了信心。
复试结束后,有一位老师找到我。我看着她面熟,感觉像面试时的一个老师,还没细想,她就问我多高多重,我一一回答。她说 她正筹备一个电影叫《远乡》,缺一个男主角,想让我试试,我答应了。试戏那天正好是我的三试,在考试的同时还要去剧组试戏,一关关过下来,最终选中了我来演这部戏,就是后来的《青春祭》。而这位导演就是第四代著名导演张暖忻。
也许冥冥之中有一种缘分,让我与张暖忻导演相遇。我对她拍的讲中国女排精神的电影《沙鸥》有很深的情结,因为影片中有很多情节跟我的经历有几分相像。早在业余学习表演的时候,我就跟同学说,我的梦想是跟张暖忻导演合作,演她的电影,哪怕戏份不多也行。没想到,当时这样一个遥远的愿望,几年后就实现了。
1985年,我考上了北京人艺。
人艺的话剧,当时我看过3次。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过曹禺先生的历史剧《王昭君》,第一次知道,原来话剧是这个 模样。第二次是在人艺小剧场,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被称为“中国首部先锋戏剧”。我在黑暗中泪流满面,因为剧中无业青年黑子的苦闷和孤独,和当时我的心态十分相近。第三次是在首都剧场。我那时已经开始学习表演,和一个朋友买了位置最好的票,看人艺大戏《小巷深深》。那天我坐在观众席中默默地想:“这辈子,如果我也能站在人艺的舞台上演戏,就知足了。”
所以,我当然不能错过人艺学员班招生的这次机会。那一年,学员班招生16 名,我们将在人艺学习2年,不断地淘汰、筛选, 最后留下一小部分。我们的班主任是童弟老师和林连昆老师。林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拍过电视剧,有人拍过电影,但是希望你们不要骄傲,从零开始。”
那时距离我从拉链厂辞职,发誓要学表演,已经过去了整整3年。3年中的一切挫折、成就,从那一刻起都在我心中归零,我的 人生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摘选自《冯远征的表演课》后浪出版授权发布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