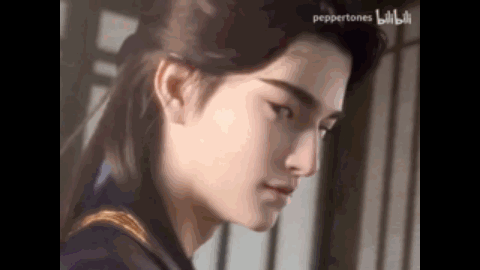(可读性背后的意义偏离)
由江苏省翻译协会主办的《翻译论坛》自2014年创刊以来,刊物影响力逐步提高,刊出稿件的被引用率不断增加《翻译论坛》中的论文多次被CSSCI期刊文章引用,在2017年第5期的《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就曾两次被引用今天推送的这篇论文发表于《翻译论坛》2015年第2期,在《外语教学》2018年第1期中被引用,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由江苏省翻译协会主办的《翻译论坛》自2014年创刊以来,刊物影响力逐步提高,刊出稿件的被引用率不断增加。《翻译论坛》中的论文多次被CSSCI期刊文章引用,在2017年第5期的《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就曾两次被引用。今天推送的这篇论文发表于《翻译论坛》2015年第2期,在《外语教学》2018年第1期中被引用。
可读性背后的意义偏离
——从蓝诗玲英译《阿Q正传及其它中国故事——鲁迅小说全集》谈起
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曹新宇 甄亚乐 杜涛 高小雅
摘 要: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拥有母语国的语言和审美优势,其译文往往比中国翻译家的译文更受读者欢迎。然而西方汉学家翻译时对“可读性”或“通顺”的过度偏重往往会导致原作意义的偏离和损害。本文以英国汉学家蓝诗玲所译《阿Q正传及其它中国故事——鲁迅小说全集》为例,从主题意义和文化意义两个层面来讨论蓝译鲁迅小说在可读性背后的意义偏离,以此说明采用归化策略产生的通顺“透明”的译文往往会出现原语文化的损耗。但作者同时又认为,汉学家译者与中国译者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使他们在解读原语文本的过程中,关注点与中国译者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于中国译者的解读丰富了原作的意义和内涵。
自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文学作品外译和对外传播成为一个国家层面的大议题。就其中的译者模式而言,除了近年来因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凸显出其重要性的海外汉学家与以汉语为母语的译者合作翻译的模式之外,主要存在中国翻译家独立翻译和海外汉学家独立翻译两种模式。
与西方汉学家译者相比,中国译者更能将“他者文化的译者不易觉察的本族精华提供给国际社会,完整地呈现本国或本民族的形象与精神风貌”(毛凌滢,2009:65-66)。为了达到完整呈现本国或本民族形象与精神风貌之目的,中国译者往往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然而,中国译者所译经典文学作品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表明,这种翻译策略并不怎么奏效。相比之下,西方汉学家采用“归化”的策略,着眼于译文的“准确性”、“可读性”与“接受性”,其译作往往更受西方读者的欢迎(胡安江,2010;谢天振,2014)。“归化”的翻译策略与“可读性”以及“通顺”的语篇策略往往互相关联,互为因果(Venuti, 2004)。汉学家译者在“对译入语国家读者细微的用语习惯、独特的文字偏好、微妙的审美品位等方面的把握上”,有着“国内翻译家较难企及的优势”(谢天振,2014:4),但是他们对“可读性”和“通顺”的偏重是否会带来对原文意义的偏离呢?
一
鲁迅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王富仁,1999),将其短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并出版的学者和翻译家共有18位(杨坚定、孙鸿仁,2010:49),其中蓝诗玲(Julia Lovell)翻译了鲁迅所有的小说作品,包括《彷徨》、《呐喊》和《故事新编》三部小说集以及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用文言撰写的《怀旧》。其译文以《阿Q正传及其他中国故事——鲁迅小说全集》(后简称《鲁迅小说全集》)为题由企鹅出版集团出版。
在所有鲁迅小说的英译本中,蓝诗玲的译本被认为“肯定是最为清晰易懂的”(Wasserstrom, 2009)。王树槐(2013)在比较莱尔、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蓝诗玲三个版本的《药》之后发现,蓝译最大程度地使用了“译者调节”手段,“叙事语言生动活泼,语义充满张力,读者乐于接受……大众性、娱乐性最强,更为普通英语读者所接受”。蓝诗玲(李梓新,2009)本人在接受《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也坦言,自己“在翻译的时候都尽量考虑英国读者的接受度”。在《鲁迅小说全集》正文之前的“翻译札记”(A Note to the Translation)中,她又强调了自己对译文“通顺”的重视(Lovell,2009)。
蓝诗玲采用了多种方法来保证译文的通顺。比如,她尽量减少脚注和尾注,而是将背景知识巧妙精练地融入正文。再如,在文化负载过多,需要较多篇幅进行解释之处,她简化并省略部分词句,如《阿Q正传》开头出现的关于各类“传”的解释,《理水》中对“禹”名字的一段戏仿,《采薇》中对同一人物不同的称呼。
然而,蓝诗玲对“通顺”或“可读性”的过度重视是否会导致鲁迅原作中意义的偏离和损害呢?王树槐(2013)指出,蓝诗玲对译文的调节导致“叙事方式、节奏张力有时受损,鲁迅语言的独特风格被平淡化了”。 寇志明(2013)认为蓝诗玲为了追求译文的“可读性”,“将小说的棱角磨平并进行简化”,如《狂人日记》开篇高语域和低语域之间的转换在蓝诗玲的译文中未有体现;在《呐喊》序言中,蓝诗玲“简单直白”的文笔使鲁迅作品因“支离破碎”的句子而产生的现代性全然消失;《呐喊》序言中对“寂寞”和“回忆”的翻译都曲解了鲁迅原文的含义。那么从主题意义和文化意义来看,这种为了保证译文“通顺”而进行的删减或简化是否也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偏离和损害呢?
二
广义而言,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就在于“某一结构特征在某一特定文学语境中所产生的主题意义(thematic value)”(申丹,1998:60)。这其中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首先是“语言特征”(linguistic feature),然后是“语言特征所产生的心理效果(psychological effect)”,最后是“语言特征以心理效果为桥梁在特定的上下文中产生的主题意义或美学效果(aesthetic effect)”(申丹,1994:9)
鲁迅的小说每一部都有鲜明深刻的主题意义。《补天》是《故事新编》的第一篇,写于1922年冬天,原题《不周山》。《补天》是“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鲁迅,1981:341)。“人的缘起”在小说中描述得非常清楚。女娲“掬起带水的软泥”揉捏出一个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又拔起一根紫藤,抡在泥水中,泥水落到地上就成了“许多伊先前做过了一般的小东西”。如此,人就被创造出来了。
文学的创造过程比人的创造要复杂得多。《补天》中呈现了汉语文学起源从“‘声音繁变’到‘寝成言辞’再到‘言辞谐美’的口头文学三阶段,终向‘箸于竹帛’的书面文学飞跃的阶段性特征”(赵光亚,2014:27)。第一节中,那些小东西被创造出来后便开始“Nga! Nga!”地叫,之后开始“Akon, Agon!”地说,然后又“Uvu, Ahaha!”地笑了,从三个字母到四个字母再到五个字母,从单音节到双音节再到三音节,从两个重复的单词到两个略有变化的不重复的单词,再到两个长度和字母构成变化都很大的不重复的单词,其中已经有了“声音繁变”的意味。
原文:
“Nga! Nga!” 那些可爱的小东西可是叫起来了。
……
“Akon, Agon!” 有些东西向伊说。
……
“Uvu, Ahaha!” 他们笑了。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间看见的笑,于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来。(杨宪益、戴乃迭b,2002:10-11)
译文:
The tiny creatures began to yelp.
…
“Sky! Lord!” some began to babble.
…
They gurgled with laughter—the first laughter she had heard in the universe. And for the first time, her lips curled unstoppably in to a smile. (Lovell, 2009: 299)
蓝氏译文中省略了“Nga! Nga!”和“Uvu, Ahaha!”两处字母音的翻译,只保留了第二处字母音。对读者而言,译文清楚易懂,无需花费过多的“处理努力”(processing effort)来理解原文中字母数量渐增、音节数量渐增、长度和字母构成变化幅度渐增的字母音,然而原文中语言创造从简单到复杂,从重复到变化的“声音繁变”的过程却荡然无存。此外,第二处字母音“Akon, Agon”被译成“Sky! Lord”,原本无意义的字母音被赋予了额外的含义。相比较,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原样保留了三处字母音,读者在阅读过程可能需要稍作停顿,以理解这三处字母音的汉译,但口头文学创造过程中“声音繁变”的意图被保留下来了。
鲁迅在《采薇》中对伯夷和叔齐的描写充满反讽意味。伯夷和叔齐一方面“迂腐地恪守已成陈迹的先王之规矩”(郑家建,2001:34),反对周武王“不仁不孝”,“以下犯上”;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毫无勇气捍卫自己的尊严,在出走路上遇到“小穷奇”打劫就露出懦弱、卑怯的神态。两人在首阳山食薇度日,以“不食周粟”来表示忠于先王。可一旦阿金姐揭穿事实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们又无力面对事实,绝食而死。表面看来伯夷和叔齐忠于先王,不做二臣,实际却是懦弱无能,逃避现实。伯夷对周文王的称呼饶有趣味。
第一节中叔齐跑来报告,传言武王要伐纣,伯夷回答:
原文:
我们是客人,因为西伯肯养老,呆在这里的。烙饼小下去了,固然不该说什么,就是事情闹起来了,也不该说什么的。(杨宪益、戴乃迭b,2002:118)
译文:
We are guests here, living off the charity of the King of Zhou, a great respecter of old age. We’ve no right to complain: either if the pancakes get smaller, or if something worse happens.(Lovell, 2009: 335)
第五节中,伯夷和叔齐隐居首阳山,伯夷闲来无事,与人攀谈,将自己的身份一一说与他人听:
原文:
两人在路上遇见,便一同来找西伯——文王,进了养老堂。(杨宪益、戴乃迭b,2002:118)
译文:
Meeting in their self-imposed exile, the two of them went together in search of King Wen of Zhou and were accommodated in his Old People’s Home. (Lovell, 2009: 348)
《孟子·离娄上》中说“吾闻西伯善养老者。”焦循正义说,“西伯,即文王也。纣命为西方诸侯之长,得专征伐,故称西伯。”(百度百科b)简言之,西伯是西方诸侯的领袖,并非一国之君。伯夷一直称文王为“西伯”,甚至在首阳山与孩子、樵夫攀谈的时候,都只说自己前去投奔的是“西伯”。这表明他并不承认文王为一国之君,而只是纣王任命的诸侯首领。蓝诗玲将这两处的“西伯”译成“King of Zhou”或“King Wen of Zhou”,而不是译成Earl of the West,读者不需要花费“处理努力”来判断这两处的“Earl of the West”和文中其他部分出现的“King of Zhou”是否是同一人,的确做到了流畅易懂,但是原文中所表现的伯夷和叔齐反对周武王讨伐纣王,死忠于商王的主题意义就丢失了。在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中,“西伯”和“周文王”分别被译成“Earl of the West”和“King of Zhou”。
三
词语中蕴涵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最可能表现在“词语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词语的联想——派生意义”(冯玉律,2000:289)中。如果将词语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联想——派生意义省略或简化,其中所反映的文化意义就会产生偏离或被损害。
《理水》中,文化山上的一群学者讨论到底是否有禹这个人。一位学者说“‘禹’是一条虫”,“‘鲧’是一条鱼”,另一位学者反驳道:
原文:
“不过鲧却的确是有的,七年以前,我还亲眼看见他到昆仑山脚下去赏梅花的。(杨宪益、戴乃迭b,2002:70)
译文:
But Gun does exist. I saw him with my own eyes seven years ago, smelling the plum blossom at the foot of Kunlun Mountain.(Lovell, 2009: 319)
赏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之一。寒冬腊月,百花凋零,唯有梅花傲霜凌雪,独占枝头。自古以来,赏梅受到多少文人雅士的追求与喜爱!在中国,赏梅一般着眼于色、香、形、韵、时等方面。蓝诗玲将“赏梅”译成“smell the plum blossom”只顾及梅花的香味,于梅花的色、形、韵、时都未表达。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译成“enjoy the plum blossom”,语义模糊,但也因此增添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原文:
“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的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清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杨宪益、戴乃迭b,2002:178)
译文:
When your father sprinkled well water over them, they hissed and roared, slowly turning blue. On this went for seven days and seven nights, until the swords lay, almost invisible, at the bottom of furnace—two pure-blue, transparenticicles.(Lovell, 2009: 556)
“井华水”是清晨第一次汲取的井水。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井泉水《集解》中记载,“汪颖曰:平旦第一汲,为井华水”(百度百科a),尤其以山泉井的井华水为精品,冬暖夏凉、清纯甘冽。中医认为此水味甘平无毒,有安神、镇静、清热、助阴等作用。《铸剑》中用“井华水”来冷却通红的剑,直至剑成为“纯青”、“透明”的冰。王妃生下一块“纯青透明”的铁本属异事,用这样的铁来铸剑,其锻造之法必定也不同寻常。蓝诗玲将“井华水”译成“well water”,只有单纯的“井水”之意,其中的传奇色彩和异国色彩都被尽数抹去。 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成“clear well water”,虽然没有译出清晨第一次汲取的井水的含义,但却强调了其清澈纯净。
四
自十七世纪以来,“通顺”就一直是英美文化语境下的最高翻译标准。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第三条就是译文应具备“原创作品的通顺(ease)”(郭建中,2000: 69)。在英美文化语境下,将外国文学作品译入英语往往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德南姆(Sir John Denham)翻译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将拉丁文中的人名、地名或是省去不译,或是泛化改用其上义词;与房屋建筑相关词汇使用英国的对应词。使用“通顺的翻译策略,使他1656年翻译的《埃涅阿斯纪》比其他版本更‘自然易懂’”(Venuti, 2004: 60)。亚历山大·蒲柏用英雄双韵体(heroic couplet)翻译《荷马史诗》,使这位古希腊诗人的作品“韵脚整齐,或使用素体诗(blank verse),用词典雅(Venuti, 2004: 66)”,风格高雅典丽。歌士瑞(William Guthrie)使用英国国会辩论的语言翻译西塞罗的《论演说家》,使西塞罗俨然成为一位国会成员。
译者在翻译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时尚且以本国语言文化为中心,采用归化的策略,生产出通顺的译本以达到各自的政治或审美目的。中国文学作品在欧洲处于边缘地位,中国文明和英国所处的“西方文明”有本质性差异,在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过程中,汉学家译者更是追求译文的“通顺”,并使用归化的策略。
二十世纪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翻译《西游记》,“凡译者难以找到合适的表述或读者难以理解之处”,都会被删减或简化。他删去了部分中国读者最喜读的片段以及大量诗歌,大大简化了小说中与道家炼丹、长生术相关的内容,最后译文长度不及原作的三分之一(Wong & Chan,1995: 427)。他的译文在“风格和用词”上无人能比(Yu, 1977),但是从他的译文中无法“理解为他翻译提供原材料的文本所体现的文化”(Spencer, 1975: 36),译文在本土的“可理解性和文化力量方面的得(更是)超出外国文本和文化遭遇的失”(Venuti 2000: 68)。
另一方面,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中国文学外译也不能一味否定汉学家翻译这种译者模式。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加,当代汉学家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身份与十九或二十世纪的汉学家大不相同。当代汉学家大都具有“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以及中国情谊”(胡安江2010:12),蓝诗玲就曾在南京大学交换学习一个学期。尽管这些汉学家的译作也追求“通顺”,因而出现原作主题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偏离与缺失,但他们对中国文化持一种友好的态度,不会任意解读中国文化形象或将其丑化。他们与中国译者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使他们在“阐释”原文意义和作者意图的过程中,关注点与中国译者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于中国译者的解读丰富了原作的意义和内涵,使同一部作品得以以不同的形象和风貌出现。
本文的撰写得到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文化精品课题(外语类)”(项目编号13sskyjwhw-34)和“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201410307064)的资助。在撰写过程中,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James Hadley博士在资料方面给予了诸多帮助,在此致以谢忱!
参考文献:
[1] Goldblatt, H. Why I Hate Arthur Waley? Translating Chinese in a Post-Victorian Era [J]. Translation Quarterly, 1999(13&14):33-47.
[2] Julia Lovell. 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3] Spencer, J. The Explorer Who Never Left Home [J]. Renditions, 1975 (5), Cited from Howard Goldblatt. Why I Hate Arthur Waley? Translating Chinese in a Post-Victorian Era [J]. Translation Quarterly, 1999(13&14): 4.
[4]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5] Wasserstrom, J.China’s Orwell [N]. Time, 2009-12-07.
[6] Wong S. K. & Chan, Man Sing. “Arthur Waley”, in Chan Sin-Wai and David E. Pollard, eds. 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P, 1995, cited from Howard Goldblatt. Why I Hate Arthur Waley? Translating Chinese in a Post-Victorian Era [J].Translation Quarterly, 1999 (13&14): 37.
[7] Yu, A. C. The Journey to the West[Z].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cited from Howard Goldblatt. Why I HateArthur Waley? Translating Chinese in a Post-Victorian Era [J].Translation Quarterly, 1999 (13&14): 38.
[8] 百度百科(a).井华水 [DB/OL].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83kOO1c0zhNatBcH_ufLsxL59jGhwsQ2lRhAb6z8N6ig3TY1w1ALPg5BasBrEN0PW1G_CJ-fI18lvMCktZxqJ, 2015-02-24.
[9] 百度百科(b).西伯 [DB/OL].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uYjjZ_k0v4HY9i3Neyl-KEelkbTQR_jqeDAmpDBMvkwkXo4gslZwtNsu2f9rG5Ni2qojANUmZ2JBOnswmrWf, 2015-02-24.
[10] 冯玉律. 词语的文化内涵与翻译[A]. 郭建中(编),《文化与翻译》[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11] 郭建中. 泰特勒翻译三原则中译辨正[J]. 中国翻译,2013(3):68-70.
[12] 胡安江.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 中国翻译,2010(6): 10-16.
[13] 李文静. 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 中国翻译,2012(1):57-60.
[14] 李梓新. 专访英国翻译家朱莉亚·拉佛尔:把鲁迅和张爱玲带进“企鹅经典”[N]. 外滩画报,2009-12-17,第366期。
[15] 鲁迅. 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 寇志明. 因为鲁迅的书还是好卖:关于鲁迅小说的英文翻译[J]. 鲁迅研究月刊,2013(2):38-50.
[17] 毛凌滢. 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与译者汉语文化能力的培养[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9 (1):63-67, 94.
[18] 申丹. 文学文体学的分析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 (3): 7-13.
[19] 申丹. Lingustic Stylistics and FictionalTranslation(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0] 王富仁.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上)[J]. 鲁迅研究月刊,1999(9):49-57.
[21] 王树槐. 译者介入、译者协调和译者克制[J]. 外语研究,2013 (2): 64-71.
[22] 谢天振.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学,2014 (1): 1-10.
[23] 杨坚定、孙鸿仁. 鲁迅小说英译版本综述[J]. 鲁迅研究月刊,2010 (4): 49-52.
[24] 杨宪益、戴乃迭(a). Call to Arms [Z]. 鲁迅. 呐喊,北京:外文出版社,2002.
[25] 杨宪益、戴乃迭(b).Old Tales Retold [Z]. 鲁迅. 故事新编,北京:外文出版社,2002.
[26] 赵光亚. 利用小说进行考古——鲁迅《补天》中的文学起源问题考论[J]. 鲁迅研究月刊,2014 (6): 24-32.
[27] 郑家建. 《故事新编》:文本的叙事分析与寓意的文化解读[J]. 鲁迅研究月刊,2001 (2): 33-40.
(原文参见《翻译论坛》2015年第2期)
本文转自:江苏省翻译协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