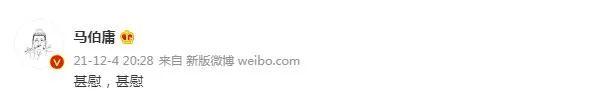普陀山与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在普陀山同住7天后)
1925年旧历5月中旬,已出家7年的弘一法师抵达了浙江普陀山。他这次前来,是为了向高僧印光法师行弟子礼。
印光法师比弘一大了20岁,他一生弃绝名利,以身作则,极力弘扬净土宗,他被后世称为莲宗第十三祖。

印光法师与弘一法师
拜访印光法师前,弘一就与印光法师有了很多渊源。因缘凑巧下,弘一还在1920年为他的《印光法师文钞》撰写过题词。在题词的序里,他虔诚地赞道:
“余于老人向未奉承,然尝服膺高轨,冥契渊致”。
在跋语中,精通文墨的弘一依旧对印光予以了极高评价,他说:
“老人之文,如日月历天,普烛群品,宁俟鄙倍,量斯匡廓。”
也正是从此后起,弘一与印光法师有了通信往来,信件的内容,多围绕修行展开。有一次,弘一还在信中请教印光法师“如何刺血写经”。
印光法师收到信后,立即给了回信,他不仅在信中具体介绍了刺血写经的利弊、方法和前人的经验,还着重谈了修行入道的关键。此外,他还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弘一写经时的“不合格之处”。
随着印光法师对弘一的不断点拨,弘一对他也越来越服气了。在1925年给好友王心湛的一封信里,他写道:“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印光法师”。

让弘一非常沮丧的是,当他在信中向印光法师提出“愿册弟子之列”时,却未得印光法师首肯。
见印光法师拒绝了自己,弘一以为:是自己的诚心不够。于是,他竟在阿弥陀佛佛诞日,“于佛前燃臂香,乞三宝慈力加被”,之后,他再次“上书陈情”,可他依旧未得准许。
弘一并未因此气馁,他只再度“竭诚哀恳”,依旧未得准许的情况下,他决定亲自前往。
弘一带着“出家七八年来梦寐以求的一大愿望”来到普陀山后,顾不上吃饭休息,便来到了印光法师所住的法雨寺(后寺)。
“弟子弘一,想求见印光法师!”弘一作揖向寺前看门的小僧人道。小僧答了一声“请稍候”后,便转身去了印光法师的关房。
不多时,小僧回来作揖道:“师父吩咐了,概不见客,法师请回吧!”
弘一被拒绝后,并未离开,他干脆坐在寺前那棵大树下等,他心想:印光法师肯定会出来,出来见了面兴许就能改变想法了。
傍晚时分,已顶着烈日苦等一天的弘一终于见到了和僧众一同出门的印光法师。弘一恭敬地站起并作揖,两人默然对视良久后,印光法师终于微微向他点了点头。

民国年间的普陀山
这之后的七天里,弘一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印光法师。而印光法师则每日该干嘛干嘛,似乎身边根本没有第二个人。
佛家说“真正的修行往往在日常生活里”,所以,吃饭、扫地皆是修行。弘一也深知这个道理,他将印光对自己的“无视”看成了“教导”。
每天,弘一都如“依葫芦画瓢”一般跟着印光,他发现印光每日的衣食住等方面,都极为粗劣。每天早晨,他仅食白粥一大碗,连咸菜也没有。
弘一不解地问:“为何不吃点咸菜?”印光法师听了淡淡道:“我初来普陀的时候,早饭是有咸菜的,但我是北方人,吃不惯,因此改为吃白粥不吃咸菜,已经三十多年了。”
每次吃完饭,印光法师都会用舌尖舐碗,至极尽方止。弘一见了,虽不解其意,却也跟着照做。
和所有出家人一样,印光法师也是“过午不食”,他的中饭相比早餐略“丰盛”,通常是一碗饭,一碗大众菜。
每次吃完中饭,印光法师还会将水倒入碗中,涤荡其余汁,然后以漱口,并轻咽下,他每次这次这样做时,都像在举行一个重要仪式,似乎唯恐有一点点残余之饭粒菜汤。
弘一还留意到,印光法师平日非常慈善,可当他看到有人在寺内用餐而剩下饭粒时,他立马会大声呵斥道:“你好大的福气,竟然如此糟蹋粮食。”有一次,有客人将冷茶倒弃在痰桶里,他见了也大声训斥了客人。
这一切,弘一都看在了眼里,疑问也慢慢升腾起来。
终于,一次饭后,弘一学着印光法师的手法,用水冲碗并咽下后,印光法师开口了,他看着弘一的眼睛认真地道:“要惜福啊!”
就这么一句话,弘一顿时就明白了:珍惜吃食,是惜福。“只有惜福,才能留住福分”,弘一在心里感叹道。
也是到此时,他才终于明白,为何印光法师坚持一人独居,且事事躬自操作,从不让任何侍者帮忙了。“福是不能享的,一旦享福,福分就没了!”弘一一边作揖一边叹道。

弘一法师
也从悟明白这层开始,弘一再看印光法师每日自己扫地、擦拭油灯、拭几、洗衣服等,便再也不奇怪了。他知道:这趟普陀山之行后,他的整个修行都会发生变化。
印光法师能有如此体悟,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他自幼多病,尤其眼疾严重,后来,他的双眼几乎失明了。一心念佛后,他的眼病竟然不治而愈了。
弘一的经历和印光法师颇相似,他在俗时,也是多病缠身,有一段,他甚至觉得自己就要暴病而亡了。他也是出家后,身体才逐渐好了起来。
弘一突然懂了:自己出家为僧,日日过苦行僧的生活,本身就是惜福,惜福了,福报才到了自己身上,顽疾也才慢慢缓解了。
7天后,得到教诲的弘一即将离开普陀山,临行前,他和印光法师辞别。临走前,他问道:“师父,弟子还有一事不明,请开示。”作揖后,他接着道:“佛法,究竟如何救国救民呢?”
印光法师听后略一沉吟道:
“因果之法,为救国救民之急务,必令人人皆知,我有如此因,将来即有如此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果。想挽救世道人心,必须从此入手。”
离开普陀山时,弘一心里满满都是感恩,7天时间里,他耳闻目睹一代大德的嘉言懿行,并得到了他的开示。

印光法师
后来的弘一法师,其修行变化之大,足以让所有人惊讶。
离开普陀山后,弘一辗转到了宁波,并挂单于四明山四大丛林之一的七塔寺云水堂。得知消息后,他在俗时的老友夏丏尊赶来探望。
夏丏尊没想到:自己这次见到的弘一,竟与他记忆中的弘一,完全不一样了。也是这次与他相处后,他被深深触动。
夏丏尊印象中的弘一,是那个极其讲究吃穿住用的公子哥儿。记忆中,这位公子哥儿,只要有一丝不舒服,就会想方设法改善之。
到了云水堂后,夏丏尊发现:“公子哥儿”竟与四五十个游方僧,同住桶舱式的房间,这房间的床铺还是上下两层排列,弘一的床铺在下层。
见到夏丏尊后,弘一笑容可掬地打招呼,并主动告诉他:“桶舱里,茶房待我很和善,这里睡得也挺舒服。”
夏丏尊听了有些惘然,他心道:“过去锦衣玉食的他,如今怎么甘心过这种简陋朴素的生活,他到底怎么想的啊?”
“你就跟我去白马湖小住几日吧!”夏丏尊开口道,语气几乎哀求。弘一却并不为所动,他于是再三恳请,弘一终于答应前往。
收拾行李时,夏丏尊几乎要哭出来:他的铺盖,竟是用一条磨破的席子包裹的。夏丏尊心里有一百个疑惑,弘一也觉察到了,但他并未说什么。
到了白马湖后,夏丏尊替他打扫房间,却被他制止了。

右三为弘一法师,右四为夏丏尊
夏丏尊并不知道,自打与印光法师同住7天后,他已决心:为了惜福,事事亲自动手。
他更未对夏丏尊提及:这趟普陀山之行后,他更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了。而自己的“罪孽”,自然与他早年的挥霍有关。他多少觉得:是自己昔日的行为,损了自己的福德,以至于到中年时多病缠身。
铺好床铺后,弘一拿出黑破不堪的毛巾,去湖边洗脸,并用柳条刷牙。夏丏尊见了,忙拿了一套新的洗漱用品跑来道:“用这套新的吧,这不碍事的,是小物件。”
弘一却忙不迭地把那条破手巾珍重地张开给老友看,意思是:它还不是很破呢。“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眉眼带笑地说道。夏丏尊看着老友,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因知道弘一过午不食,中午时分,夏丏尊特地多做了几碗素菜送来。可弘一却坚持只要一碗菜,夏丏尊不肯,死活加了一碗。
弘一用餐时,夏丏尊一直在旁边陪着。他看到弘一吃饭时,竟仔仔细细把饭一粒一粒地划进嘴里,用筷子夹起一块萝卜时,他脸上流露出的那种郑重其事和了不得似的神情,让夏丏尊见了,“几乎要流下欢喜惭愧的泪水”。
第三天,夏丏尊继续陪着弘一用餐,有碗菜盐酱加多了,夏说:“这菜太咸了!”可弘一却欢喜地一边嚼着一边道:“好的!咸有咸的滋味,也好的!”
夏丏尊看向弘一,发现他脸上的神情,如在吃世间的美味佳肴,滋味无穷。
接下来的几日,弘一坚持要走到夏丏尊家吃饭,而不肯让他给自己送来,他说:“出家人,本来就是乞食,走走,更好。”
到了夏丏尊家,弘一法师见吃食有些丰富,便叮嘱道:
“一碗青菜已经蛮好,千万不要再搁香菇、豆腐一类的东西了。五月间我在普陀山参礼印光法师,见他早饭光是一碗白粥,中午吃的菜里,连油都不搁的。相比之下,我比他奢侈多了。在惜物一事上,我还得向法师学习呢!”
话说到这儿时,夏丏尊才终于明白:弘一的种种变化,与弘一在普陀山的那7日有关。自此后,他便不愿违背老友的修持准则了。他明白了,自己若坚持按自己说的做,很可能会“好意干扰了他一心追求的境界”。
弘一法师离开后,夏丏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弘一经由与印光法师的七日有了大变,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夏丏尊
夏丏尊耳闻目睹弘一的一言一行后,联想到关于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境界问题,也联想到了生活态度和艺术境界的关系问题。
夏丏尊确信:觉得世间没有不好东西的弘一,已经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这种境界,抛开宗教不说,已经可以称作“将生活艺术化”了。
艺术的生活,原是关照享乐的生活。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束缚,还它本来面目,如实地关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
另一方面,夏丏尊也悟到:自己过了大半生,平日吃饭穿衣,何尝想到过真的滋味。乘船坐车,看山行路,何曾领略过真的情景。
后来,夏丏尊将自己的这些切身感受,写在了为弘一弟子丰子恺漫画所作的序里。他想用这种方式,让弘一所经由“惜福”得到的真理,告诉所有人。
人的言行要改变,从来都是始于思想改变。而很多的思想改变一旦发生,就会影响一生。往后余生里,弘一一直将“惜福”二字作为修行的一部分。
弘一法师病重时,仍一心惦记战争中的难民,为了安置更多难民,他将夏丏尊送给自己的白金水晶眼镜当掉了。“舍物”用于福德之事,是大的“惜福”,这点,弘一早已参透。
弘一法师圆寂前七天,居士罗元庆送来专治疟疾的奎宁,弘一坚持不肯受,理由是“自己福德不够”,经再三劝说,他才接受了其中的六丸,可至死,他也未服一丸。

弘一法师圆寂图
弘一法师至死都在启发世人:“惜衣,惜食,非为惜财而缘惜福”,而惜福,正是累积自己的福报。某种程度上,惜福即是“有德”,弘一也经由惜福,让世人看到了他的“大德”。
后世常将弘一与虚云、太虚、印光并称为“近代四大高僧”,他们四人出身、阅历等等皆不同,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极度惜福之人。
老人常言:惜福者受福,不惜福者受祸!这话,用在弘一等人身上,最是恰当。若非惜福,世间安有名扬天下的“律宗十一代祖弘一”呢!
(附注:文中弘一与印光法师见面时间,网传为1924年,但作者查阅弘一年谱、弘一致李圣章两封信等诸多史料后考证:两人会面时间应为1925年。
讹传出处是《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的一篇讲演稿,之所以出错,因为有部分作者,凭借讲演稿中“弘一说自己前往普陀山时印光64岁”,不假思索推断当时为“民国十三年”。实际,年龄算法,有虚岁、实岁之算!这点,恰被他们忽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