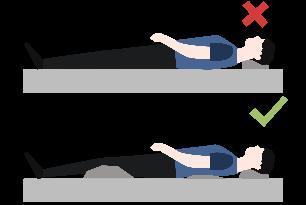李金发二十世纪诗歌(诗怪对李金发诗歌之晦涩的思考)
(本文由【思想走在荒路上】所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李金发,1900~1976,开创中国象征派诗歌。
一通常人们将李金发称为“诗怪”(这个标签本身并不重要)。解读李金发的诗歌仿佛必须将其置于“象征主义”这一框架下才能探其究竟,可遭遇的更大的尴尬是纵使如此也不一定就能一明其义。我认为,“诗怪”之称表达的仅仅是同时代人在视野上对当时世界诗歌认识的狭窄。可奇怪的是,对李金发诗歌的“怪”感到“怪”的不仅是他的同时代人,甚至包括现今的众多读者和评论家。大家每每谈到李金发时仿佛不提一下“诗怪”一词话题就进行不下去,就对不住自己对李金发的深刻洞见。同时又表现出审视李金发诗歌时常犯的一个错误,按照德国语文学家胡戈·弗里德里希的说法,即评价当代诗歌时“仅仅关注某个国家,仅仅关注最近的二三十年。这样一来,一首诗看起来就是无语伦比的‘突破’”。李金发的诗歌一入文坛即让人大感惊讶,被认为前所未有,别开生面。但只需把审视的眼光放宽至二十年代的全世界,就不难发现李金发的诗歌创作并非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尽管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可能是)。与李金发同时代的众多外国诗人他们的诗歌风格与李金发诗歌相较是何其相似,无论是瓦莱里、洛尔卡、艾吕雅、布莱蒙、蒙塔莱,还是更早的波德莱尔、兰波、魏尔伦。他们的诗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晦涩。“晦涩难懂”是李金发之所以受到苛责的最大的原因。可以说,李金发的诗歌就像是在鸭群中破壳的鹅蛋,本是天鹅,却被一群鸭子用鸭子的眼光来看待。当然,闹笑话的责任不在鸭子,而是鸭群中从未出生过天鹅。何况这只天鹅还是一只黑天鹅,就更不能不让鸭子们感觉到它很怪。如果我们把李金发的诗歌往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全世界的抒情诗这一范围里一放,他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怪”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果说李金发仅仅是因为写出这类“晦涩难懂”的诗就被称为“诗怪”的话,那么,自波德莱尔以来的几乎所有西方现代诗人都可被称为“诗怪”了。
一位论者认为,李金发“注定是一个开拓性的诗人而不是一个成果积累型的诗人”。也就是说,存在着诗歌以外的意义大于诗歌本身。具体地讲就是李金发最大的贡献即引进了象征主义,至于他诗歌,本身很难荣登大家之作的殿堂。这位论者接下来还评论道,李金发的诗歌“难以在任何一种经典意义上被记住……他的诗经不起细读和分析。”对此我不以为然。就如同我前面所说,李金发就是一只出生在鸭群中的黑天鹅,被一群鸭子以鸭子的眼光审视着。如何理解李金发——自然规避不了对象征主义的言说——但还要跳出象征主义,也就是说“不应按照机械的原则硬将作家(当然也可以是诗人)套进某某主义的模子”(纳博科夫语)。然而后者之于现在的我而言难度较大,请允许我先从简单之处起步。
二我的生活中大多数人对象征主义存在着巨大的误解,认为所谓的象征主义就是将一种诗歌创作的手法抬高到了“主义”的地步。以至于,只要一首诗运用了象征手法,或者,只要是让人“读不懂”,他们就干脆把它扔进“象征主义”这一框子里,同时心里也就油然而生出一种莫名的心安,例如他们就是这么对待“朦胧诗”的。诚然,“朦胧诗”中有大量象征手法的运用,有些也表现出一些现代性特点。但它们依然不是象征主义诗歌。那它们属于什么主义的诗歌呢?——什么主义也不属于。就连“朦胧诗”这一称谓也只是一个美丽的、尴尬的误会。
“幽深晦涩”、“颓废感伤”,是人们对李金发诗歌的通常印象。但怎么个“幽深晦涩”、“颓废感伤”,我们通过比较沈尹默的《人力车夫》与李金发的《弃妇》更能得到一个直观的印象,同时也看看当诗歌涉及现实时两位诗人各自是如何处理的。
人力车夫
日光淡淡,白云悠悠,风吹薄冰,河水不流。
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甚么?
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
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
弃妇
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
遂割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
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
越此短墙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
如荒野狂风怒号:
战栗了无数游牧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
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
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
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
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
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
长染在游鸦之羽,
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
静听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
徜徉在丘墓之侧,
永无热泪,
点滴在草地,
为世界之装饰。
通过与《人力车夫》相比,李金发的《弃妇》所表达的本质特点即,诗歌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转译。两首诗歌的言说对象都涉及现实。对于《人力车夫》人们轻易地能解读其义:通过强烈的反差表现出坐车人和拉车人天壤之别的生存处境,并同时可以将这一现象上升到“对不公平的黑暗社会”的批判。这是典型的以主题为先导的解读方式。李金发的《弃妇》(以及他其他的诗歌)之所以“难懂”、“难读”正是因为主题(或言说内容)被言说方式置于其下。这种言说方式使诗人面对现实时不是去客观地描述它、渲染它,而是使其陌生化,甚至是使其发生变形。《弃妇》首先以弃妇自身作为言说主体出场(至于这“我”是不是诗人内心的外化这并不重要),“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割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何来的急流的鲜血?何来的沉睡的枯骨?以及黑夜、蚊虫、荒野、狂风?在写这诗时这位弃妇的身旁是否有这些事物,——甚至,是否真有一位这样的弃妇身在诗人眼前,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与事物作为一种“材料”在诗人的笔下被重新建构成一个世界——迥异于现实世界。如果说现实世界就是一种让人习以为常的存在对象,李金发诗歌要做的就是让人惊讶,让人不安,对已被众人默认为“是”的世界说“不”。但如果只是“否定现实”的话,难道《人力车夫》没有做到吗?有,不过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一种还让人熟悉的方式。李金发则使用暗示,使我们本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起来,甚至变得惊悚起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若换作沈尹默他会如何处理“弃妇”这一对象。把她的外表描述得肮脏、落魄,内心幽怨无比或者连幽怨也没有,完全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然后读者就可以轻松地、习惯性地将其视为对黑暗社会的指控,好像一部作品不指控一下“黑暗的社会”就不好意思出来见读者。李金发则不。他没有直接表明立场,而间接表明的立场是否是批判的立场且直指“黑暗的社会”这也难说。可以说,李金发的诗歌没有什么社会功能,而是更接近于艺术品的品质。如果他要使他的这首《弃妇》具有社会功能他应该怎么做?在诗的最后添加上几句弃妇振聋发聩的“怒吼”,或者让这“怒吼”成为诗歌每一节的尾巴,制造出循环复沓的效果,然后读者就可以心满意足地将这种“怒吼”视作弃妇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那“黑暗的旧社会”的血泪控诉。更或者,他可以把这首诗写成内心独白,让弃妇述说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鬼样子的。不,李金发都没有。李金发的诗歌不是要反映现实,做现实的传声筒,而是要转译现实,无论这种转译是以暗示、变异还是分解、错置的手段来达成的,总之,要以一种不同于甚至反日常生活逻辑的方式再建对日常生活的认知。“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然后随红叶而俱去。”李金发转译弃妇的哀戚,不是为了让这哀戚被谁听到,送给谁拿去做批判社会的工具,而是发挥一种奇妙的想象力,首先以“游蜂之脑”表现这哀戚的微小,之后以“与山泉长泻”表现这哀戚的巨大,最后以“随红叶而俱去”表现这哀戚最终化作虚无,无人问津。他选择的也不是让人熟悉的传统的意象,甚至也不是让人能一明其义的意象。他以创造性的想象在诗歌这一艺术世界中赋予词语以新义、新面孔,既费解,又有说不出来的吸引力。谈到此,可能一些读者表示只同意李金发诗歌“费解”这一观点,至于对“又有说不出来的吸引力”可能有所微词。这没什么,正如莫雷亚斯在《象征主义宣言》中所表示的,象征主义表现的本就是一种全新的美学原则,而习惯了原有的诗歌表达方式的读者对其不断斥之为晦涩难懂是不足为怪的。
朱自清说李金发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朱自清对李金发诗歌特点的评论一点也不新奇。诺瓦利斯也做了类似的表达:“诗歌,单纯悦耳,但是却没有任何意义和关联,至多只有单个的诗节可以理解,仿佛充满了最不同事物的碎片。”自波德莱尔以来,诗歌创作就呈现出一种趋势:诗歌的意义越来越不再指向内容,而是偏于形式。这种形式表达的是:诗歌渐渐地不再是单纯的对对象的言说,而是一种“将语言魔力置于语言内容之上,将图像动力置于图像含义之上”。这一倾向使诗歌发展到后面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晦涩难懂。李金发的诗歌师从的还是早期象征派的波德莱尔和魏尔伦,他诗歌中的“图像含义”大多还保存住,言说方式的重量还未远远超过言说内容。
三最后,谈谈我对象征主义的看法。
我并不为李金发引进象征主义这一中国从古未有的创作原则而欢欣鼓舞、兴奋不已。实际上李金发的诗歌水平大体上表达的还是早期象征派的特点,准确地说,他与波德莱尔、魏尔伦更为接近。与兰波就开始显出距离。象征主义特别强调诗歌的音乐性,但这音乐性可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技巧上的押韵、讲究格律。波德莱尔认为诗人应该是语言魔术师,或者说“声音魔术师”。诗歌通过不同词语非同寻常的搭配就能像钢琴一样弹奏出音乐。而兰波更是进一步发展了波德莱尔的观点,提出“通灵”一说。诗人是通灵者,他在诗歌中将语言的芳香、色彩、声调熔于一炉。这就是兰波的“语言炼金术”。
兰波,1854~1891,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这种现代诗歌创作观很大程度上冲击到了中国诗歌的传统观点,尤其是是自古中国诗人对诗歌境界最高的追求:意。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如此说道:“意为主来词为奴。”诗歌以意境为主,词语为奴。意境少而词语多,就是“主客颠倒”。而兰波则这么阐述道:“我计算每一个辅音的形式和运动,幻想借助语言与生俱来的节奏发明一种诗歌的原初词汇,这样的词汇,或早或晚,可以让所有感官领会。”象征主义经由兰波和马拉美发展出了一种“语言魔术”——“语言传达意义的功能和语言作为音乐力场中一个独立有机体的功能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发生了分离……人们可以以一种组合方式调配语言的声音元素和节奏元素就如同调配魔术公式一样。诗歌的意义就来自这些元素而非主题上的谋划……抒情诗人成为了声音魔术师。”(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P36)“声音魔术师”?这是什么?我们想象得出吗?伴随这种语言魔术而生的是对暗示的强调。“具有语言魔术的暗示性诗歌分配给词语全部主权,让其成为诗歌行为的第一原创者。对于这样的诗歌,真实的不是世界而仅仅是词语。”(同上,P170)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将词语作为原创者的诗歌观是如何深深冲击到我们对诗歌的理解。为何如此?因为它和中国传统诗学——两种相背的诗学观——之所以产生如此强烈的碰撞其背后表达的是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在各自作为诗歌的语言基石后的巨大分歧。这个分歧通过翻译一眼便可望之。
以拼音文字创作的西方现代诗歌翻译成汉语后发生了大变(反之亦然)。弗里德里希以兰波的散文诗《大都市》为例(法语原文省略)。其中有一句诗翻译成汉语是“这些残忍的鲜花,人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心灵和姐妹,在欲望前进行诅咒的锦缎”。这句诗是什么意思?习惯从内容上解读诗歌的读者可能要大伤脑筋了。——这句诗没有意思。为什么把“鲜花”称为“心灵和姐妹”?——不为什么,仅因为这两个词在法语中包含了与“鲜花”这个词同样的元音!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诗歌在何等的程度上是不可翻译的。被翻译成另一种迥异的语言后它究竟丧失了什么。被翻译的诗歌与原文已不是一回事。
象征主义是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一样具有原型意义的创作美学,滋养了一大批的西方现代抒情诗人。但西方现代抒情诗人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诗并不表意,诗存在”让我感觉是一把架在我们母语脖子上的剑。
其实在李金发的诗歌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以象形文字创作的象征主义诗歌与拼音文字所创作的有着截然不同的道路:李金发的诗歌几乎没有任何音乐性,诗歌中的节奏很大程度上是靠情感来牵动;而诗歌的绘画感却非常强烈,意象繁富,色彩淡丽,情调清幽,一些诗句甚至略有几分古典韵味,但就是没有象征主义所强调的音乐性。在暗示力的来源上,如果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主要是来自声音的话,那么李金发诗歌的暗示力则基本来自图像。
深受象征主义影响的梁宗岱如此阐述道以其为基础之一所提出的纯诗说:“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及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达光明极乐的境域。”而这纯诗是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梁宗岱的纯诗观给我的感觉是意图营建一种乌托邦式的诗歌观。他似乎并不认为(或未意识到)诗人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住了其诗歌所能“舞蹈”的范畴,以及规定了其所能舞出的“最美之舞”。还是说,梁宗岱只是移植了象征主义的“部分枝条”,而这“部分枝条”又有着可被“中国化”的可能?这个问题则不在本文思考的范围之内。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