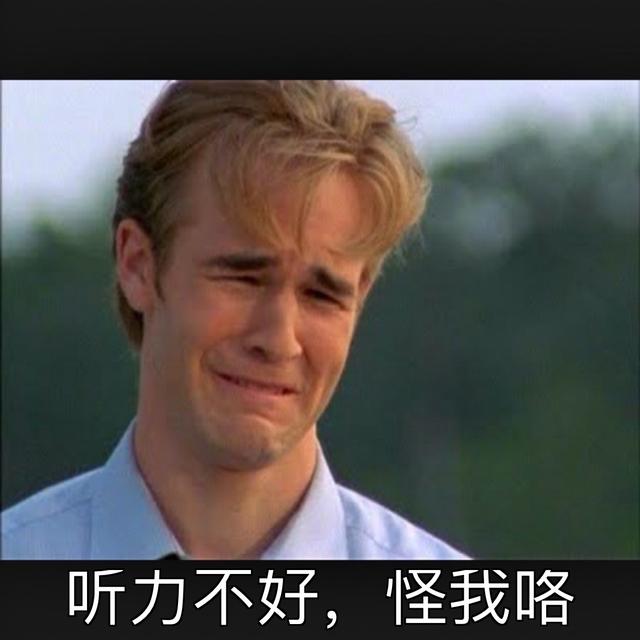琴书吕洞宾戏牡丹第一集(关学曾和北京琴书)
在北京琴书的发展史上,关学曾是一位承前启后、艺术造诣颇深的艺术家。他自十几岁拜师学艺起,至今已有50年艺龄。50年(本文应撰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编者注)来,他呕心沥血,历尽艰难,为祖国的曲艺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今天,人们一提到北京琴书,就会想到关学曾;一提到关学曾,就会想到北京琴书。甚至连他的退休,也引起了“老北京”对于北京琴书发展前途的忧虑。

这是关学曾生前演唱北京琴书时用过的大鼓
从旧社会街头卖艺的一个穷艺人,成长为新中国的鼓曲艺术家,关学曾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求索之路,奋斗之路。
1922年8月1日(阴历六月初九),北京城南龙须沟附近东大地一巷的关春伦家,生了个儿子,父母给他取名关士清。关家是旗人,在清朝年间,也曾享受过旗人的特殊待遇,但到了士清父亲这一辈,“吃钱粮”的旧例早已革除,关家和许多八旗子弟一样陷入困顿境地。士清的父亲什么手艺也不会,他只好靠卖菜和“打鼓儿”(买卖破烂儿)维持家里生活。小士清8岁时,家里为了省些房租,搬到西唐洗泊街。这里是贫民区,关家过的也是贫民的日子,过年时,一家老小连饺子都吃不上;晚上,为了省灯油,只用火炉子的微光照个亮儿。后因房租问题,房东借故同他们打架,士清父亲被国民党的衙门关了三天。出来后,他一怒之下,便又携家室老小搬到沙土山街12号。这里门前便是破烂市,关家常年就靠买卖破烂儿度月。
士清父母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地想供孩子上学,可惜力不从心。士清上学的时间,连起来沒有超过半年的。上个两三月,没钱了,就失学,在家温习功课,等父亲买卖好一点了,挣了点钱,他就又接着上学。他上的是私学,比较自由,有钱就上,没钱就歇,这样断断续续学了两年多。
10岁时,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他只好彻底辍学,帮着家里做小买卖了。夏天他到金龟池冰窖趸来冰块儿,沿街叫卖“冰核儿”。有时候,他也卖“山里红串”、“摘手”(人家挑剩下的次等水果)、西瓜等,但卖臭豆腐、酱豆腐的时间最长。
他卖的王致和臭豆腐,很受老北京人的欢迎。特别是在下雨天,生意就特別好。因为雨天有些人不愿出门买菜,买块臭豆腐就窝头,一顿饭就打发过去了。附近硝盐厂的工人们,差不多都认得这个卖臭豆腐的小孩。
这期间,士清借做小买卖的方便,插空儿到茶馆听过鼓书。旗人人家,爱听“玩艺儿”的挺多。关家也有这个传统。士清的母亲还能唱上两口儿,有个姨也会弹弦子,也会唱。士清从小耳濡目染,也就对鼓书发生了兴趣。
他在八九岁念书的时候,就爱听铺子里的喇叭(即收音机)里说书的节目。做小买卖时,他到街上的时候多了,听说书的机会也更多了。他住家的沙土山一带,就有好几个茶馆里有说书的,唐冼泊街的忆盛鑫茶馆,是他经常去听书的地方,那里有评书、大鼓(长书)等等。听一小段子,要收一大枚铜钱,他仗着自已是小孩,同茶馆的人也熟,就不花一个子儿,听“蹭儿书”。
有时他到胡同东口一家铺子门口,站着听广播里的说书,有孙呈海的西河大鼓《三下南唐》,翟青山的单琴大鼓《黄风配》等等,他越听越上瘾,都忘了吃饭。当时他心里就很想干这一行。
到了12岁的时候,有人介绍士清到前门外湿井胡同专营批发洋货的宝成堂当童工,做拉锁。管吃管住,一个月l元工钱。士清便去了。头一个月拿回家l元钱,父亲领他去鞋店花9角钱买了一双新靴。这是他来到世上头一回穿新鞋。以前,他的衣服、鞋帽,都是父亲收破烂时挑捡出来的旧物,从未买过新的。这件事给地留下的印象很深,几十年过去了也难忘记。
后来,因宝成堂掌柜的待童工太苛刻,每日干活早起晚睡还不算,动不动还要挨打。士清父母心疼他,只叫他干了一年就不让干了,回到家里继续做小买卖。一个偶然的机缘,使关士清走上了鼓曲艺术的道路,而且后来以艺名“关学曾”扬名曲坛,成为一代鼓曲名家。
关家的房东李大妈是单琴大鼓艺人翟青山的亲戚,也是后来关学曾老搭档、著名琴师吴长宝的姥姥。
士清和吴长宝自小相识,在一起玩耍。士清13岁时,吴长宝去天津投奔表兄翟青山学说书。转过年来,李大妈同关家商量,想介绍士清也去翟青山门下学艺。关家自然同意。双方讲好,等翟来京上电台说书时,促成此事。
士清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他用“打鼓儿”挣来的5元钱,到打磨厂西头的宝音斋乐器行买了一台扬琴,专等翟青山来时拜师学艺。
但是,事情很不巧。翟青山同聘请他到电台说书的源利银行闹了矛盾,上电台的事吹了,翟也不来北京了。
过了些日子,李大妈过来告诉他家,从天津来了个单琴大鼓艺人常德山,是源利银号约来上电台的。同李家也是老相识。士清便通过李大妈的介绍,拜常德山为师。
按艺门规矩,立下“师徒字据”。请孙呈海为保师,魏德祥做引进师。拜师仪式比较简单。大概师父也了解关家贫穷,没有请客,没讲更多的排场。
这一年,关士清l4岁,正式开始了学艺生涯。以后取艺名关学曾。
当时,单琴大鼓在京、津一带很流行。这种曲艺形式最早源于京南(马驹桥、采育、大兴、河北安次县等地)一种叫“犁铧调”的民间俗曲。清朝中后期,发展成五音大鼓。演员的说唱,加上三弦、四胡、扬琴、鼓板四样乐器伴奏,故称“五音”。起初,在农村里流行。特別是碰上丰收年办喜事,或逢年过节,或冬日农闲、茶余饭后,爱好唱“五音”的农民聚到一起就即兴唱起来。
当时的段子有:《大烟恨》、《大烟鬼叹五更》、《小姐儿俩拾棉花》,等等。城镇里也有专业演员唱五音大鼓,但不多。约上世纪20年代,有一年农村里闹灾荒,一些农民携儿带女进城要饭吃,有会唱五音大鼓的,便沿街卖唱,挣钱度日。
当时,城里艺坛的规矩,必须拜师后,同行才许可他演唱。有些人就拜鼓曲艺人田玉福为师,起艺名都带“德”字儿,如:常德山、魏德祥、翟德林(即翟青山)等。其实,他们都是带艺投师,为的是表明已拜过师,好去茶馆等处挂牌演唱。顿时,京城里五音大鼓流传开来。
电台也邀一些有名的演员去说唱,像翟青山的长篇说唱《黄风配》,就很受观 众的欢迎。翟先生在长书方面颇有造诣。有一回,他上电台,弹三弦和拉四胡的因事全没来。他的演唱只好用一台扬琴伴奏。没想到播出来后,大受听众欢迎,群众都反映好听。既清新优美,词义又听得清楚。于是,翟先生便决定去掉其它乐器,只用单琴伴奏,名称也改为“单琴大鼓”,翟青山从此更红了。
其他艺人也跟着他学,只用单琴伴奏,单琴大鼓这一名称也就被承认了。但上地摊、书茶社等一些人多热闹的场所演唱,一台扬琴音量太小,有时还得加上四胡,才能把音量衬托起来。这又不能叫单琴大鼓了,又改称琴书、单琴大鼓和琴书这两种名称作为“北京琴书”的前身。一直流传到解放初期。
关学曾一开始投师常德山,学唱单琴大鼓,实际上是这一曲艺形式的第二代专业艺人。旧社会里学艺很苦,师父只管使唤徒弟,很少正式教艺,徒弟得自个儿去琢磨。一开始,常德山和魏德祥教学曾打琴。学了20来天,刚有个眉目,师父就带他上电台伴奏,还学了几个新段子,如《小姐儿俩拾棉花》、《小寡妇上坟》、 《监桥会》等。师父告诉他如何背词,如何上板上眼。他在伴奏时,也暗睛琢磨师父的唱腔,用心学习,这才渐渐入了门儿。
当时,他除了跟常先生上电台外,大都到下处(妓院)演唱。多是唱十几分钟的短段子,没说过长书。按当时规矩,园子(书场、书茶社)要求说长书者,起码要能连起来说“一转儿”(2个月)。这很 不容易。一般说书的有两条道儿:一条是“册子”,即按照书本上的词儿去说;另一条是“江湖”道儿,就是插入一些在书本上看不到的情节。说唱长书最有本事的,要数翟青山的师父田玉福老先生。
学曾跟常德山学了半年多。在一个冬日里,常德山把关学曾叫到跟前,说:“我眼下穷得不行,要奔钱,没功夫教你了。你岁数小,别误了你的前程。赶明个儿,我请石金荣先生当你的师父吧。”
原来是常德山抽“白面儿”,把身子骨搞垮了,唱不了了。后来,这个穷艺人连饿带病,“倒卧”(死)在天坛坛根儿下了。常德山临死时,学曾正跟着石金荣学艺,连个面也没见到。他知道师父的死信以后,难过了好几天。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