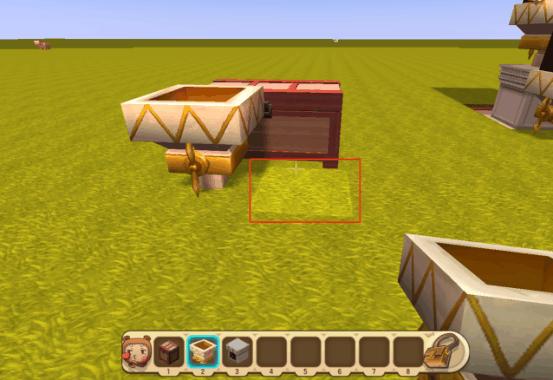活在南坡下三(活在南坡下三)
7扑老眼儿
8看戏
9村子的气息
10害怕长大
11东舀浆
七(扑老眼儿)
麦子入仓以后,人就闲了下来。
村里的狗和村里的人一样,闲的像一块块石头,镶嵌在村里村外任何一个角落,晨晖中,夕阳下,远远的瞅,近近的瞧,一动不动。
玉米、绿豆,黄豆等等许多的种子都在在地下卯足劲的吮吸着养分,等待破土而出时的辉煌,麦粒们躺在粮圈里,回味着丰收的喜悦,它们彼此热烈的交谈着,憧憬以后会有一场多么新奇浪漫的旅行,它们会坐上汽车,乘上火车,走出乡村来到城市,

“或许,我还能坐上飞机呢!”一粒麦子说,她的话引起一场笑声,
“真的”,她严肃的说:“当我在麦田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蒲公英自由自在的飞行。”
街头的狗卧在石臼旁的阴凉处,院子里的狗,有窝的和没窝的都不进窝里,它们都觉得外面更敞亮些。鸡踱着步子,搜寻着壤土下面的草籽、虫子或者是主人洒落的食物。
一粒玉米躲在狗腿之下,它窃窃自喜,以为可以避开鸡们的目光,有了再次孕育、发芽,绽放绿色的机会。
谁知道一只红冠金羽的大公鸡看见了它,嗝嗝嗝的叫着,尖尖的喙毫不留情的叨了下去,谁知道用力过猛方向偏了点,竟然啄在了狗腿上,老黄霍的一下爬起来,狠狠瞪了公鸡一眼,却没有吭声,又挪了一个地方继续趴下。
一只吐着长丝的虫子从树上垂下来,身上包裹着叶子,在风中晃晃悠悠的打着秋千,安逸得很,院子里发生的一切,尽在眼底,它才不管那些事儿呢,除了控制好高度,不被鸡们啄食,真正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享受着悠悠然的生活。
我坐在炕上,从一个小小的窗格子里注视着外面。湛蓝的天空被一扇窗户分割,还有一朵比新棉花都白的云朵也被分割,我仔细查过,一共被窗棂分成九十九个正方形的小块,每一个方块里的景色都不一样,我为自己足不出户却能看见九十九个天空感觉窃喜,虽然九九归一,它会在我踏出屋门后重新合为一体,但是现在的我能把一件事分成九十九个部分来看,还有什么琢磨不透的呢?
街道上传来一阵喧闹声,鸡停住嘴,抬起小脑袋朝门口看了看,竖起耳朵听了听,不为所动,又低下头,继续着自己的工作。
小黑站在在墙头,像模特一样来回走了几场猫步,咪咪叫了两声,嗖的一下,跳到树上,隐遁于绿叶中不见了。
我跳下炕,穿上鞋,飞快的跑到街上。山神庙的东墙角有一片空地,大大小小围拢几个人。紧挨着土墙根挖了一个鸡蛋大的小土坑,距离土坑三四米的地方,小胖正在用一枚二分钱的硬币划着一条长线,为了把线划的直一些,他撅起屁股倒趴着一点点后退,一不小心撅在迷糊的脸上,砰的一声放了个响屁,嘣得迷糊“妈呀”的喊了一声,赶紧躲到一边,小胖解嘲的说:别怕别怕,响屁不臭,臭屁不响。
划好了线,几个人就站在小土坑边上,每个人拿着一枚硬币向线上投,谁距离横线最近谁就负责收集起硬币,在手心拢一拢,捏到一块,站在横线上,脚尖不能触线,然后就把手里的钱投向小土坑。
小廋是第一个投,他站在线外,把手臂与坑尽量放成直线,眼睛瞅着土坑,手里攥的钱瞄准,“嗖”的一下扔了过去。硬币有落在坑里的,有掉在坑外的,几个人一拥而上,小廋把坑里的钱掏出来,摊在手掌心数着,单数的话就装起来,等于是赢了,双数的话就得往里赔钱,二赔一,小廋的运气太差了,投的十个硬币进去了八个,他得赔八分钱。
几个人喊着抓着扔着,忙的不亦乐乎,我看了一会儿,觉得索然无味,什么事儿只有参与进去,才能收获快乐或者失落,自己可没有闲钱来干这事儿。我积攒着爸妈给的和自己在煤矿旁边拾的废铁换来的每一分钱,我想买书,等我攒够五元钱,就走路去西村供销社买书,西村距离南坡二十多里地,那可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
(八)看戏
午饭后,大伙儿坐在祠堂前的石阶上聊天,祠堂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屋顶上各种颜色的琉璃瓦,院里当中为青石铺就的过道,两侧是苍翠的松柏。祠堂前面的石阶上窄下宽,每一层的棱角都凿成了椭圆,既美观又可以避免老人孩子滑倒时发生危险,可见当年的人们做事是多么的审思缜密。

得胜叔远远的过来了,边走边喊:
看戏喽,下午晚上都有戏”
他的嗓门大大的,中气十足,唯恐旁人听不见!
“有戏,唱啥戏?”
赵孬接过话茬,烟袋锅子朝鞋底上敲了敲。
“五女拜寿,听说还有县剧团的名角助兴呢!”
“哦,那可中,”赵孬竖起了大拇指!
得胜叔的大嗓门说罢,双臂一垂,十指并拢,身子轻侧,拇指与食指轻轻揉搓,做捏手帕状,头轻微抬起,娇羞的目光似水柔情,扭扭捏捏唱道:
爹爹收我螟蛉女,
没齿难忘养育恩。
归来拜寿无孝敬,
娘亲见责也该应。
大伙儿看着他的模样,乐得都是前仰后合。
大礼堂台阶下是一片空地,东西长南北窄,东边是一个坡,出门晚的人慌着看戏,一边踉跄着步子下坡,一边吹胡子瞪眼责怪身后跟着的娘们:你真是老牛拉破车,慢慢腾腾,还不快点,迟了就没好位儿了!
礼堂外空地上有卖小吃、卖杂货的,四乡八邻来看戏的人也多,拥挤着、爹喊闺女儿喊妈,熙熙攘攘的好不热闹。在南坡有亲戚的人可不慌,为啥,下午人多了就晚上看,反正有吃有住有夜场,何苦和别人去挤着一时!
和南坡人沾亲带故的,当天就有人捎来了信儿。不论是出了门的姑,还是娘家她亲舅,早早就开始了准备,鸡关窝里,猪扔圈里,狗被拴在院子里看门,急的上串下跳,汪汪汪叫着抗议,家里的活儿安排停当,就穿着一身过年才上身的涤卡衣服,提上两匣子点心,悠哉乐哉的来了!
南坡人实诚、好客,平时吃啥不讲究,亲戚来了可不能慢待,刚刚从俺家门前经过的是三个蛋的舅,洞湾村的。
毛缸多远就瞅见蛋的舅来了,就赶紧迎上去,接过点心匣子,客客气气让到家里面,安排钢蛋去打酒,铁蛋去割肉,毛蛋最小也安排有任务,去鸡窝里掏刚暖出来的蛋,媳妇叮叮当当在厨房里忙活着,煮的蒸的炒的,有啥做啥,没啥也要想办法去买,饭菜香味从东头飘到西头,又被风追逐着,从西头又跑回了东头。
想想也就是这个理儿,亲戚们老远来了为个啥?不就是吃好、喝好,然后就是得得劲劲看几唱戏吗。为了让他舅满意,三个蛋吃罢喝罢,满脸红光又集体出动,早早去占上了几个好位置。
晚上看戏和白天就是不一样,首先是灯光得劲,白天有光,舞台不亮豁,晚上幕前灯、幕后灯、顶灯、侧灯都打开,那黄澄澄的龙袍更黄了,红艳艳的将旗更红了,绛红色的幕布在怀梆特有的乐曲中缓缓拉开。
梆子、板胡、锣、鼓、笛子、笙、二胡、三弦等等乐手们吹、拉、弹、敲一起开始,气氛马上就高涨起来。紧接着,白发须眉的老生踱着步子出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忠实本分的老院公。
南坡怀梆剧团的演员和乐队都是本村的农民,农忙时他们一头扎进庄稼地,犁地、耙地、打坷垃、播种,什么都会干,而且干得都好;一队、二队都有剧团上的人,可是从来没有因为演出而耽误了庄稼。农闲时他们排练,大队部里是最热闹的地方,宽敞的屋子里时不时传出演员们咿咿呀呀的拉嗓、练嗓和乐器调弦的声音。
有时为了提高大家的演技,还从外地请来老师,我从大人们的腿缝中钻过,蹲在地上听那位老艺人讲课,学怀梆,先要学会十字韵,讲什么菊花指、弧形指、山膀手,还有文丑、武丑、花旦;不过这些我都听不懂,我只喜欢看演坏人的大白脸,和“喳喳喳哇呀呀”的杨七郎!
我们小孩子不喜欢看文戏,总觉得干巴巴唱着没味道。更喜欢看《反西京》之类的武戏,台上武旦、花脸你来我往,枪挑刀劈,我们在台下也没有闲着,举着树枝棍子来回比划,最后被大人们斥责着一轰而散。
礼堂的戏台下面是空的,观众席正对着东西有两个洞口,每到这个时候,我就领着迷糊、狗蛋几个死党,趁着戏没开演前,偷偷溜进礼堂,钻到戏台下面玩,那里面黑咕隆咚的,最适合捉迷藏了。
等到开场后,想出也出不去了,头上脚步声、唱戏声、翻打声响成一片,灰尘纷纷扬扬洒下,弄得我们好像遁在地下的土行孙,最后只得从戏台正前面的两个出口爬出来,灰头土脸的,引起坐在前排观众的一阵惊呼,搞得我们几个人狼狈不堪,红着脸跑了出去。
礼堂里,《五女拜寿》演得正酣,杨尚书稳坐高堂,五个女儿如花似玉;礼堂外,叫卖声此起彼伏,卖藕粉的左手拿碗,右手执壶,壶到碗满,一碗晶莹透亮、香气四溢的藕粉就捧在手中,拿着小调羹,一点一点的品,舍不得大口的吃;尖尖的和红辣椒一模一样的辣椒糖,酥脆香甜;扎在草窠上的冰糖葫芦,那圆溜溜的大山楂披着一层金黄色的糖衣,不知吸引了多少孩子馋嘴的目光。
我和几个伙伴爬上礼堂旁边的一个老柿子树上,它有着粗壮的身子,外层的树皮,裂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手一剥就掉了下来,是我们家的自留树,与八月黄,小火罐等树不一样,它叫做老叫停(豫北方言),果实很大,等到秋季成熟的时候,轻轻撕掉一层皮,就露出橙色的、一丝一丝粘在一起的果肉,咬一口,满嘴香甜,特别好吃。

我把叶子对折起来,捏住两头,屏住呼吸,吹了起来。虽然我会唱的歌曲不多,但是,有些调调还是能吹出来的,像《东方红》、《南泥湾》等等,也吹个八九不离十。
迷糊呆呆的盯着我,鼻涕滴流多长,吸一下收回大半截子,一会儿又垂下去多长,唉,狗蛋说他是粉条公司的厂长还真没错啊!
礼堂里传来戏曲终场的锣鼓声,一会儿,人们纷纷涌了出来,看那架势,好像是洪水冲垮了堤坝一般。
我领着两个死党,从树上出溜下来,迎着人潮往里面挤,本来就拥挤的人群更乱了。我们也顾不得男人们的呵斥,女人们的数落,从他们的腿缝中钻了进去。
其实,我们这样做的原因,不过就是爬到观众席的铁椅子下面,拾一些人们丢弃的半截烟头,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一个个拆开,把烟丝装进小袋子里。
我们三个都用黄花条根做了一个烟袋锅子,装上一锅拾来的烟丝,点燃,蹲在墙根,好像三只调皮的猴子,人模狗样的从鼻孔喷涌着烟雾。
在那虚无缥缈的烟雾中,竟然出现了一个烟圈,冉冉升起,由小变大,圈住了树木,圈住了礼堂,最后圈住了整个村子。
(九)村子的气息
都市有都市的气息,乡村有乡村的气息,每个村子都有不同的气息,当然,南坡也有南坡的气息。
“哞,哞”,福贵刚刚迈过门槛,就听到自己家黄大壮的喊声,黄大壮不是人,是头牛,可是它与福贵的感情比父与子都亲。
福贵拿起墙窟窿里一个带叉的木棍插住门褡,转身就走,在山里,寻常人家的大门从来没上过锁。
穿过祠堂,走过高低不平的堎头,老远就闻到了秸秆混杂着草叶、牛粪发酵后的味道,浓浓的,一股股青草的气息。
虽然远在几百米之外,当中还有几座房子遮挡,他家的牤牛黄大壮已经嗅到主人的气息,硕大的脑袋对着福贵走来的方向,拖着长长的高音叫着。
它的叫声唤醒了酣睡的太阳,羞红着脸,扭扭捏捏从大山之后走了出来,浑身上下散发着温馨的气息。
东头的风起了个早,无聊的在小学校附近闲逛着,被小琴妈烙玉米面饼子的香气吸引过来,它贪婪闻着,垂涎欲滴。
西头的赵和尚是个光棍,一个人生活,平时早饭总是懒得仔细打理,可是今天必须得吃饱,因为上午就要去山上背荆条,那活儿可不轻巧。
他熬了满满一锅小米粥,黄灿灿的,又从房梁上取下吊着的篮子,拿出两个白面馒头,掰开泡在碗里,本来还想再炒个萝卜啥的,忽然隔壁李寡妇炒鸡蛋的香气漫溢而来,赵和尚狠狠闻了几下,好像已经吃进了嘴里,端起大碗,呼呼噜噜吃了起来。
从城市而来的人,乍一下是接受不了乡村里的气息的。
猪圈牛棚鸡舍的味道,做柿子醋的酸味,烧锅做饭的烟熏火燎之味,气味的差异划分了生活环境的差异,适应性弱的会捂住鼻子,后悔来错了地方,适应性强的会感慨的说,这种味道才是农村独有的啊,这样的地方才能唤醒乡愁。
我们家的前院西侧有一个猪圈,养了一大一小两头猪。说它大,不过是与小的相比,如果与邻居家的那头黑小三放到一起,估计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父亲知道我顽皮,叮嘱我好几次,千万不要去逗黑小三。据说,那是邻居小随从他岳父家抱的猪娃,长着一身硬硬的、犹如刺猬般的黑毛,人送外号叫黑小三。
小随的岳父住在北山里最偏僻的软枣洼村。去年家里的母猪发情时,一只身强力壮的野猪越过一米多高的石墙,跳进了圈里,黑小三就是它们爱情的结晶,有着纯正的太行野猪的血统。
其实,即使父亲不说,我也不敢去它的跟前挑衅,因为每次上学路过黑小三的猪圈时,那个家伙总是将两只前蹄放在围墙上,一边做着引体向上,一边不怀好意的盯着我。我知道,小随垒得那个低矮猪圈,对黑小三这种翻墙越户的高手来说,不过是小小的毛毛雨。我曾好几次看见它越过围墙,半夜在村子里面游荡,如今的它引而不发,不过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罢了。
父亲有文化,能读会写,喜欢开家庭会议,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给我们讲话,从历史到学习,从农耕到发展经济。我记得他曾经说:农村养猪,积肥的价值比高于肉,俗话说得好,羊粪当年富,猪粪年年强,粪沤好,庄稼饱,年年收成肯定好。
为了沤好粪,父亲在猪圈上没少费心思,别人家的圈打的是土胚,我们家用的是石头,一是不怕猪嘴拱,二是肥积的多了撑垮不了圈,等到拉粪的时候,掀开几块石头,清粪就容易得多。
猪这种家畜,特别懒,偌大的圈里,除了吃,它们是走到哪、拉到哪、睡到哪,父亲经常用秸秆,黄土给他们垫圈,脏一层,挖一层,垫一层,肥沤得快,积得也多,门口一直散发着草叶腐烂发酵的味道,虽然,有些刺鼻,却并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而且还隐隐夹杂着炊烟的味道。
每年秋季,收完玉米之后,大街小巷,田间地头都是人们拉着平车、赶着牛车施肥的身影,有圆圆的,好像玻璃球样的羊粪;有大块的牛粪,散发着腥气的鸡粪,当然还有沤得变了颜色,却是庄稼人最喜欢的猪粪了。

出粪,是最能彰显我们家人多力量大优点的时候了。
父亲掀开猪圈临街的一角,拉粪用的小平车前后都装上了挡板,用绳子一束,也不怕它掉下来。
父亲跳到圈里,把两头猪赶到旁边,猪哼哼唧唧就是不想挪窝,我拿了几块白菜帮“唠唠唠”喊着,把它们引了过来。
父亲开始用鐝头刨,刨一层,就用铁锹往小平车上装一层,越挖越深,越深肥料沤得越好,颜色也由浅变深,气味也越来越浓,深埋在地下的秸秆与草叶被猪的屎尿腐蚀,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父亲装好了一车粪,用铁锹把两边拍实,唯恐掉下来,他高兴的说:“好粪入了土,一亩顶两亩啊!”然后,又无限憧憬的说:“好好干,明年让你们天天吃大白馍!”
哥哥和父亲轮换着刨粪装车,大姐架辕拉车,二姐和我在小平车的两头拴上两根绳子,在前面帮忙拉,小妹跟在车子后面,遇到上坡时,在后面用力的推。外公和妈妈在地里等着卸车,每隔一段卸一堆,卸完车后,再把粪均匀的洒开。
南山下,田野中,人们在忙碌着,贫瘠的土地有了农家肥的润泽而变得肥沃,清苦的生活有了勤劳的付出而得到改善,南坡人虽然不能称得上是肩挑日月,手转乾坤,但是他们的坚韧乐观 、淳朴善良却永远感动着这一方的大地。
而只有到了此时,村子的气息才最浓,味道才最正。
(十)害怕长大
有一天雨后,我走在老村的小径,发现影子长长的,脚印像落叶,一个个镶嵌在身后,忽然,莫名的感觉到了害怕,自己不知不觉中竟然长大了!
爸爸正在拾掇一棵不大不小的树,树从根部砍断,还被放在一盆火上熏烤。
我躲在门后偷偷啜泣,为自己突然长大而难过。
父亲拿起那棵树,像枪一样端起来,放在眼前瞄一瞄,然后顶到地上拗了拗,树皮被煎熬的青气弥漫在院子,它不痛,没有呻吟,身子却挺直俊拔了。
人终究要长大的,父亲说,就像这棵树,虽不能参天,但也做了只镢把。
(十一)东舀浆
“妈妈,我长成大人了吗?”
抚摸着书包上的红五星,我开心的问。
“快了,快了,你看俺孩儿都上学了。”
……
我背着妈妈缝制的小书包,手里还提着一只装满糖水的小瓶子,神气活现的走出了家门。
上学了,告别了懵懵懂懂的童年,从此之后,我要用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再也不做那个尿床的孩子了。
我在作业本上工工整整写下三行字:
大南坡村
一年级
牛保红
拿着我的作业本,启蒙老师赵小妞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我:
“同学们都看看,作业本封面就应该这样写,村、班级,姓名从上而下,一目了然、工工整整的多好!”
然后,她又拿起赵有利的作业本,其实赵有利就是我的死党跟屁虫迷糊,小妞老师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她指着迷糊说:
看看你写的字,像狗爬的一样,而且还像对联一样竖着写,谁教你了?
……
小学校在村子的东头,一座长方形的院子,东西相对两排房子,东边的一排,从北向南依次是校务处,二年级、三年级与四年级;西面子排是一年级和五年级,两个教室之间是拱形的过道,我们称呼它是“大门胡同”,胡同两边放着几根粗大的木梁,下课后,我们就爬到上面玩耍。
一年级的教室很大,没有课桌,前后依次放着几排长长的木头板子,下面用砖块磊的墩子垫着,凳子都是孩子们从自己家里面带来的。
黑板是用水泥在墙上做的框子,然后涂上黑色的油漆做的。
抬起头,房梁上还有用毛笔写的“造反有理”之类的黑色标语。有的窗户上的玻璃破了,就用薄木板钉住了。
教室的北边有一块空地,面积不大,叫东小场,呈半圆形,边缘长满了野草,下面是个土崖,挺高的,可以远眺北山、西小庄。
东小场在八月十五是个热闹的地方,福新叔会在这里和西小庄的人比鞭,鞭子是用 牛皮做成的,鞭稍还系着红绸子,甩起来“啪啪”的,清脆响亮,能够传的很远很远。
自从上学以后,我最爱起早到东小场读书,坐在土崖的边上,迎着晨风,既凉爽又安静,背古诗,念课文,书声琅琅,很是惬意。
赵老师看我学习努力成绩也好,就让我做了班长,这让迷糊、狗蛋他们羡慕不已,更是形影不离的跟着我,牛哥长牛哥短的巴结,唯恐我取消他们做小弟的资格。
其实,班长名字好听,却是个繁琐的差事,每天要收发家庭作业,维持课堂纪律,最主要的是,冬天还要照顾好教室里的煤火。
每天放学,同学们纷纷背上书包奔出教室,瞬间就只留下我一个人。
我从校务处打来水,去教室外的墙角铲上煤,再去东小场的边上端些红土,把煤渣拌上红土均匀的和好,准备封炉子。
封火以前,要用火捅子把燃尽的炉渣捅干净,活好的煤要不稀不干,稀的话会把炉眼堵住,火就被闷死了,干的话,半夜火燃得旺了,煤燃尽了就会乏死。
每次封住火,还不能走,先在教室写完作业,再去看看封好的炉子堵眼儿了没有,看到稀煤已经焙干,指头粗的窟窿里燃着暗红的碳火,才整理书包离去!
第二天早上,被小闹钟“叮铃铃”的响声吵醒,望着窗外天际已经发白,想起床吧,又怕冷,就窝在被子里不想起来,假装打呼噜赖床。
外公起得早,做好了饭,舀出来放在桌子上,又拿过我的棉袄在火上烤,烤透了,烤暖了,喊了我好几遍,才一万个不情愿的坐起来,睡眼惺忪的穿上。
吃过饭,赶紧去学,因为我是班长,拿着教室的钥匙,必须在其他同学到校以前开门,进了教室,书包都来不及放下,先去看看煤火灭了没有,把炉子捅开,冒着蓝光的火焰窜上来,教室里的寒气就小了许多,暖和起来。然后才拿着语文书去东小场背诵课文!
有时候,背诵累了,会望着连绵起伏的北山发呆,看着一大片洁白的云朵,被风轻轻的推着,飞过了窑并地,飞过了北山,又飞过了一排又一排的远山,最后消逝在天际。
忽然,我想起了《一千零一夜》中的飞毯,闭上眼睛,感觉自己迈步登上了如棉絮般松软柔和的云朵,飘啊,飘啊,飘出了太行山脉,飘过了繁华都市,飘向了一望无垠的大海……
远眺太行山脉,峰峦叠嶂,绵延起伏,虽然无语,却隐含着气势磅礴的霸气,造就出无数鬼斧神工的美景,它位于山西省与华北平原之间,纵跨京、冀、晋、豫四省市,绵延八百多里。是中国地形第二阶梯的东缘,也是与黄土高原的东部界线。
而南坡村位于太行山最外面一道山脉之中。
我喜欢看书,喜欢一个人站在地图前面瞎想,有时候去校务处抱作业本时,看着地球仪发呆,想在上面寻找“南坡”的名字。
从小就一直崇拜古人的智慧,他们不但将独到的见解、非凡的智慧运用在伟大的工程上;而且还将自己的想法与期望浇铸在文字中。
我对古代造字的仓颉很感兴趣,据说他是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历史传说中仓颉生有“双瞳四目”。而目有重瞳者,中国史书上记载只有三个人,虞舜、仓颉、项羽。虞舜是禅让的圣人,孝顺的圣人,而仓颉是文圣人,项羽则是武圣人。
仓颉在汉字创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
但是,我对东小场下面的古井“东舀浆”三个字琢磨了很久,都没有参悟透彻。
这个名字,我想了好几年,从小的时候跟着母亲去挑水,到慢慢大点了跟着姐姐去挑水,直到自己也会趔趔趄趄去挑水时,还是没有弄懂这个名字的准确含义。
“东舀浆”,东是方位,在南坡村东,浆在百度上解释:浆,较浓的液体,常用组词有泥浆,琼浆,包含有水等。舀字自不必说了,既有人在此生活,必定要“舀水”取用,以供做饭、种植之日常所需。而且,根据记载,赵五佬从山西迁移至南坡时,就在“东舀浆”东北方向的土崖下,挖了数眼窑洞居住,遗址至今尚存。
每到礼拜天,在家里憋闷的无趣,就约几个小伙伴去东舀浆玩。
经常来小学卖冰糕的人叫胡兰,家是博爱的,二十岁左右,中等个子,人长得机灵,对我很好。在小学的大门胡同里,他把驮着冰糕箱的自行车向后一拉,车架支好,就和我并排坐在一根木梁上。聊的投机了,他还把贴胸口袋里的黑白照片拿出来让我看,那是他女朋友的照片,长得很俊,长长的辫子垂在胸前,好看的瓜子脸,羞羞的笑着。
坐了一会儿,胡兰要走了,他还得去别的地方,于是,我就领着迷糊、臭瓜和狗蛋到东舀浆玩。
出了小学右转下去一个陡坡,左边有一处老院子,右边是一个土窑,原先是圈羊用的,土窑的洞口是用石头券的,约有两米长,进去后里面漆黑一片。打开手电,可以看到正前方有一堆土,那是从洞顶塌下来的,我们从来也不敢在里面玩。
出了土窑右转,是一条极其狭窄的小路,路左侧是一条深沟,雨季时,突发的洪水沿着高低不平的河道奔流而下势不可挡,与其他支流汇聚到山门河,流向广阔的平原,最后注入到大沙河。
小路右侧是山体,生长着灌木荆棘,靠近古井旁边有一个溶洞,洞口快被草叶等杂物盖住了,那个溶洞其实挺深的,我们就钻进里面玩耍。
洞里面黑乎乎的,没有灯什么也看不见,迷糊的爹在村里的煤窑做电工,我们去那儿玩的时候,收集了一些电缆线的皮,扎成一串就成了火把。我走在前面,顾不得脚下高低不平、磕磕绊绊,走了百十米,到了溶洞的深处,这个地方挺奇特的,有的地方又高又宽,像是大厅,可以在里面撒欢打闹;有的地方又矮又窄,非得爬着才能勉强过去。
到了大厅以后,我擦着了一根硫磺棒,那是我们在拉煤的大50拖拉机上偷的,黄色、粉色,各种颜色的都有,大小和粉笔差不多,是拖拉机启动时助燃用的。
借着五彩缤纷的亮光,可以看见洞顶有许多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石笋、石幔,有的像莲花,有的像宝塔,有的像人物,还有的像是公鸡,感觉进入了魔幻世界,几个人张大嘴巴傻傻的看着,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地下还有如此的景观。
多年以后,随着地质的变化,深处的溶洞被淤泥逐渐堵塞了,只有无数的荆条藤蔓横曳在洞口,儿时的笑声也随之被长久的封存起来。

出了溶洞,向东走七八米远的地方,就是古井“东舀浆”。我们在祠堂玩的时候,听白发苍苍的奎爷说过,它的源头是泉水而不是地下河,泉水从山体逐渐渗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片洼地。
几百年间,每逢遇到大旱之年,方圆十来里之内的乡邻都来此汲水,取得多了,水就浑浊,如同泥浆,故取名东舀浆,不过却从来没有干涸过。后来,有识之士募捐,券井加顶,又修了十几个石阶,才建成现在的模样。
东舀浆的水清冽甘甜,犹如仙露,水质极的好,喝着刚打出来的生水,既不会生病,而且解乏提神,烧出的开水也没有一丁点的水渍。后来,村里又在其他地方又打了一眼机井,虽然有数百米之深,但是水的品质远远不能和古井相比。

东舀浆的左上方有一座小庙,特别的小,但是很精致,全部是石头凿刻而成,庙顶三个椭圆形的石块,应该是代表着脊兽,上面雕刻的花纹逼真细腻,栩栩如生,那一朵朵的花儿含苞欲放,宛若天成,细细欣赏那不俗的工艺,少说也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听老人讲,那是一座龙王庙,护佑着东舀浆的甘泉喷珠吐玉、永不枯竭。
古井的位置在山凹里,深入地下二三十米。我们几个人踩着几百年来被无数人脚踩鞋踏磨滑的台阶,小心翼翼的走下去,两边是石头磊成的墙体,无数的绿植在墙体里生长,垂下绿油油的身子。
台阶有 个,在第 个的台阶上方有一座被镶嵌在墙体里的石碑,碑文是这样写的:
离开石碑,只有四五级台阶就进入井室,里面有 平方左右,券石铺地,墙体也是石头,古井在井室的正中,一个方形的洞口,里面即是荡漾着碧波的井水。
“东舀浆”的井水,夏天清凉甘甜,比城市里卖的汽水都好喝;冬天不凉,清澈透明不冰牙。
天热的时候,人们从地里回来,挑上担子,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晃晃悠悠来到东舀浆,刚迈下两级台阶,第三级还没有落脚,凉气刷的一下就扑面而来,台阶两侧的野草藤蔓,或许受用惯了这天然的舒爽,摇摇摆摆好不惬意。再往下迈两级台阶,汗就收了一半,等到进了井室,身上早就没有了汗,浑身的毛孔张着,贪婪的吸收着清爽。
井沿边放着退役的伞兵绳,也不知是谁的,不管谁来拿起来就挂袢、放桶、拔水,收绳,到了傍晚没有人挑水了,才会有人来收走。
干活的人挑着一担水,来到树荫下,不用碗不用瓢,俯下身子,伸长脖子,一头栽进桶里“咕咚咚咚”畅饮着,一口气喝个够,一晌的困乏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然后说一声“真得劲”,就挑起担子,顺着来时的路,晃晃悠悠的走了。
走了,都走了。
干活的人走了。
迷糊走了,狗蛋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看着小路痴痴的发呆。傍晚,夕阳的余晖绕过椿树、桐树的阻拦,将那暖黄色的光影投射到路上,仿佛是一架时光放映机,把几百年来历史倒放:
就在这条路上,从道光年间开始,留着长辫子的南坡人挑着水走过;民国时期,穿着长衫的南坡人挑着水走过,解放前后,穿着对襟衫子的南坡人也走过,六七十年代,穿着中山装涤卡绿的南坡人还走过,即使到了八十年代,十几岁的我也摇摇晃晃的挑着水走过。
古槐见证着村子的历史,目睹着它的兴衰,牢记与传承,是它永世不忘的责任。古井用它的乳汁哺育着无数的南坡人,她像一位母亲,在她母乳流尽的时候,能毫不犹豫的用自己的血来代替。古人常说饮水思源,扪心自问,我们做到了吗?
水,已经成为活在南坡下的人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也是压在整个干旱太行山区头上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于是,水库,引水的渠道,以及坑就应运而生了。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