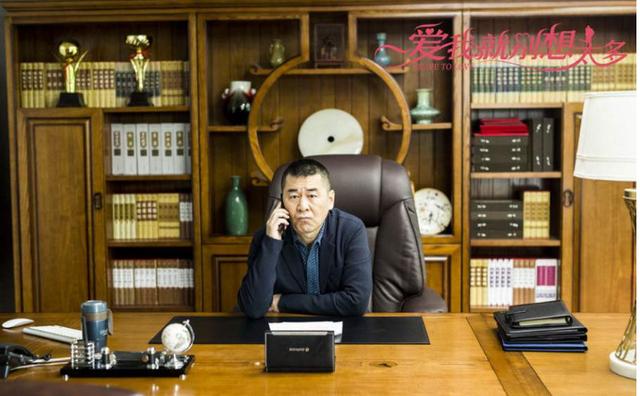当他转身要离开时(他离去成绝响)

那是一本被我翻得残破不堪、如今早已丢失的书——《多情剑客无情剑》,作者古龙。
书里有个人叫郭嵩阳,以一柄铁剑扬名。他与主角李寻欢决战,对方不忍伤害,三次相让,郭嵩阳最终收剑认输。
感念于李寻欢的人格魅力,他以点穴之法羁縻住李寻欢,代替他去和鬼魅一般的荆无命一战。自知不敌,他以身试剑,故意让荆无命刺中26剑之后,还用最后一点力气把残躯悬挂于瀑布之上,让水将血污冲刷干净,以便随后赶来的李寻欢得以从伤口观察出荆无命的剑法特点,做到知己知彼。

《小李飞刀》中的李寻欢
尔时年少,深感震撼: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现实中有这样的例子吗?
后来知道,有,而且不计其数——比如谭嗣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东渡日本,他明知一死仍决意留下,用生命来警醒国人。“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
也许是担心康梁对未能共死心怀愧疚,他还留下千古名句以表劝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作为火种离去的,作为牺牲留下的,各得其所,“咱们还是兄弟”。
郭嵩阳、谭嗣同,仅仅是虚构与现实的区别么?当然不止于此。
按弗洛姆先生的说法,这叫先知和祭司的区别。先知是价值信念本身,祭司是追随者或者宣称追随者。
郭嵩阳是一个好的祭司,他忠实于他的先知李寻欢;而谭嗣同本身就是一个先知,他用壮烈的方式告诉世人,即便社会一片荒寂,还是有一小群人,肩上承载着希望,就像亚伯拉罕要在所多玛城寻找的“十个义人”。
对此,有一句整体上来历不明的话,一语分出轩轾:“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中国社会的侠义精神,总在时光里波动,时隐时现。
今天是一个离去与退隐的时节,世无大侠,“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楚留香”。
被克制的激情我读《多情剑客无情剑》时,已是1990年代,那时中国社会的理想主义光辉已经暗淡。在理想主义澎湃的1980年代,金庸、古龙,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册。
当时的理想主义,是一种被集结起来的公共精神,想要以一己之身,去为国家、社会做点什么的自觉意识。1980年代,这种自觉意识确实席卷了整整一代人,我们连尾巴也没有赶上,在这条路上只拾到一点牙惠。
武侠小说的流行,正因为它契合了蓬勃的公共精神,激发了担当意识。故而从武侠小说的兴盛与式微,可以和不同时代的社会性格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
今天,金庸与古龙早已过时了,更遑论等而下之的那些二三流武侠小说家。不过今天也有今天的“武侠”,它以“玄幻、仙侠”等新题材的面目出现。较早的有影响力的新题材武侠作品,是新世纪初的《仙剑奇侠传》,这是一部游戏改编的电视剧。

《仙剑奇侠传》中的李逍遥
我们这群余晖之下的武侠迷,那时正上大学,在津津乐道金庸、古龙的同时,相当一部分人也坦然接受了这种新的混合题材。
这和这一代大学生对国事的议论仅止于议论可谓若合符节,我们更关心的,是未来的就业与收入。精神食粮本身已经不与现实挂钩,无论再让人心潮澎湃的作品,都只是一种娱乐。
“玄幻、仙侠”不断滋长、繁茂,到今天人们最熟悉的可能是《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了。这些作品的一个共性是没有任何时代背景,纯粹是消费主义驱使下的一种想象力驰骋。
抽离了时代背景,就抽离了现实感,因而无论故事怎样进展,都决不会带来思想负担。因为这是价值观建构了作品,而不是作品建构价值观——出于消费与娱乐目的而制造的故事,当然不会告诉受众应当警惕消费与娱乐,这和社会公共精神的萎缩完全对应。
此处无意借通俗流行文学的变化去褒扬或批判某一代人,而是首先挑明一个道理:社会气质会主导文艺偏好。
回顾1980年代,理想主义气质其实相当程度上起于一种集体的稚气。刚刚改革开放,一个大变革时代来临,一切价值都在重构,而中国社会并不具备应付这个大变革的心智——因为长时间的阵营壁垒隔阻,人们见过的世面太少。

年轻人充满希望,想要担当,但不知具体路径。武侠小说正因为符合这一气质,给知识青年的“为国寻路”热情提供了出口,也为普通人与时代如何建立联系提供了最通俗的解释。
金庸、古龙的作品,几乎都完成于在大陆流行之前。所以他们的流行和今天的新题材流行不一样,社会不是被动接受商业逻辑的娱乐喂食,而是主动选择身上缺乏的成分。
某种程度上说,这有点“开眼看世界”的意思,只不过看到的,是中国自己的东西——传统文化里一种被克制的激情。
这种激情就是侠义精神,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有浓重的乌托邦味道的价值流派。
武侠的祖宗侠义精神最重要的渊薮,是墨子。在墨子的主张里,这种精神叫“任侠”。
他先解释了“任侠”的意思:“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相当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然后阐明“任侠”的实践方式:“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不顾一切,扶危救困。
墨家不但有学院派的学术团体负责价值供给,而且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来践行认定的价值。
在电影《墨攻》里,赵国为了攻打燕国,而试图先攻灭夹在赵燕之间的梁国,这样梁国就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于是墨者革离被“组织”派往梁国,协助守城。
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确曾真实发生,《墨子·公输》就记载,墨子为了止楚攻宋,派出禽滑嫠等300人,持守圉之器入宋以待楚寇。

墨子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里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超越任何时代的终极道德实践家。正因其精神的纯粹,决定了其不可持续,不说世俗权力与其它秩序思想的攻击, 他建立的组织本身也会因为内部矛盾而瓦解——因为不可能人人都是墨子。
墨子一身正气的侠义精神富于乌托邦色彩。事实上,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中关于战争的描述,几乎就是墨家行动的翻版。乌托邦人不为利益而战,而是为信念而战,常常不惜代价援助被欺凌的邻邦。
权力是最大的现实主义,墨家在秦朝碰上了死敌法家,在汉朝又遇上了法家化的儒家,再加多种因素作用,于汉代逐渐式微。然而即便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也不完全否定墨家的价值。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见义不为,无勇”,隐约还是有侠义的影子。
“侠”的精神,墨子是最“正宗”的一家,但并非独此一家,甚至也不是最早的一家。中国人熟悉的“侠”,至少还有两支。
一是“游侠”。这些人有的踽踽独行,爱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的被收聚在贵族门下,成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主角,比如孟尝、春申、平原、信陵手下的一些宾客。
二是“绿林豪侠”。从王莽时期啸聚于湖北绿林山的王匡、王凤开始,一直延续下来,代代有之,基本特点就是反抗官府、劫掠财宝。
这两类“侠”,都是血勇有余,但价值信念广度不足。如果说墨子作为一个先知,是良知和仁慈统领智慧与勇气的一个整体,这些人在最好的状态下,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片面。

金庸和古龙所创造的武侠小说世界,是一个混合了各种“侠客”的江湖,但故事的主人公,一般还是有明显的墨者痕迹。郭靖是“侠之大者”,而李寻欢本身就是价值化身。
武侠小说为了赋予主人公“任侠”的能力,必须虚构给他一身高强的武功。而墨家的“侠”,武艺并不是必要条件,所以墨者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号召。
墨家的“任侠”精神,是一种遥远的绝响,但因为它是超越任何时代道德的正义诉求,它点燃的星火从未熄灭。乱世,它是一声内心号角,太平时代,它是一种美丽想象。
1980年代其实是思想的乱世,故而内心的“任侠”号角被吹响;而其后的经济机会夺走了号角,太平的气氛把它转变为虚幻的想象力。
对“任侠”的爱与怕中国有最灿烂的武侠文化,又有最不适宜武侠精神生长的社会土壤,这是一对矛盾。
历朝历代,人们在想象空间里都会对侠义精神着迷,但退回现实生活,他们又会非常自觉地防止侠义精神在初级社群里滋长。
儒法并用是历代国家治理的常态,儒与法,都与“侠”不兼容。
法,自然不用细述,这是一种严格否定的秩序,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私力的不受约束。所以韩非子说得非常明白:“儒以文触法,侠以武犯禁。”“带剑者”是“五蠹”之一,五蠹不除,亡国灭朝。
儒,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概括的广阔胸怀,但这是为知识分子专设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稀有阶级,故而这是“体制内”的专利。
并且这一专利还有公认的转化途径,简而言之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心服务于政治秩序。
这显然与“侠”的存在方式冲突。墨子会把门徒派到各国去争取政治地位,但政治身份只是他们积累资源、更好地实现独特的价值信念的一种手段,如果现实与正义相违背,他们就一定归附良知。

更重要的是,儒家对知识分子的成长有一个顺序安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直接到国,没有给社会留下空间,因而精英的社会化过程其实是一个“国家化”过程。而缺失社会视角,就会缺乏平常的公共精神,从而给普通人树立利人的榜样。
所以,成为一个对国家重要的人,在一般化的市井经验里,是以“光宗耀祖”的自私形式呈现的,而不是标榜一个人为公共利益做了哪些贡献与牺牲。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家”是最重要的精神信仰,这与“孝道”这一社会治理手段息息相关。
人们对历史可以含含糊糊,对国家大事多数一知半解,但每一族的族谱、每一户的家谱都非常完善、精确。今天人们指代脑海中最精确的事情,还会用“如数家珍”。

《刺客聂隐娘》剧照
每一个普通人家的男性,最重要的身份是家族漫长的传承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纵向序列中的一个符号。所以,中国男性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承担“序列责任”,这一责任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则是保全性命,延续链条。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父母在,不远游”,“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谆谆教诲,在平民百姓的直觉认知中最后都演化为一条——不要冒险,不要死。
所以我们看到,在宋代陈元靓的《事林广记卷九·警世格言》中,“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句子,堂而皇之成为一种“经验”遗之后世。鲁迅先生解释说,这是“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
这样的社会土壤,其实对“任侠”精神是敌视的。
除非出现了极端情况,那就是天下混乱,家本身已经难以保全,没有了退路。不论是墨子那种正气浩然的侠,还是报恩、复仇、劫富济贫的“侠”,大多出现于整体或局部的乱世。
如此看来,武侠精神的暗淡,其实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作者 | 南风窗新媒体主编 李少威
编辑 | 苏米
排版 | GINNY 菲菲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