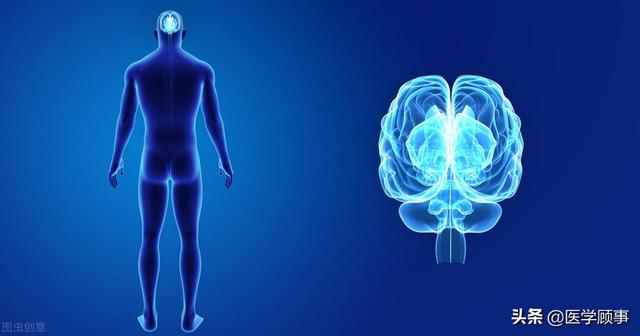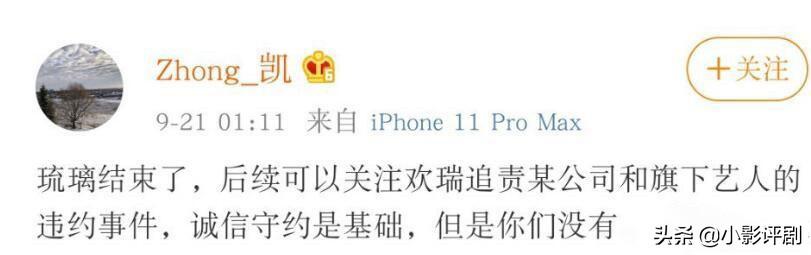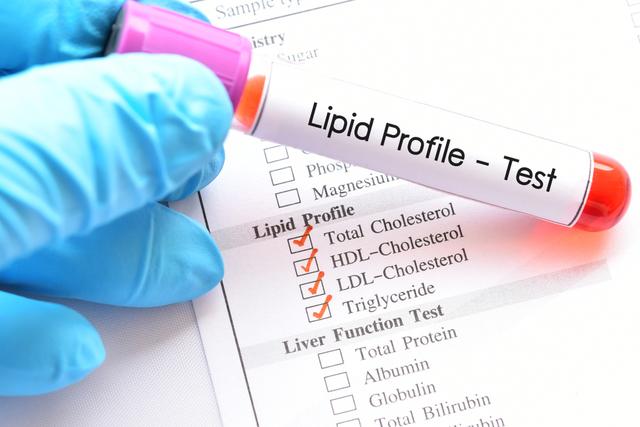妈妈生病了看图写话二年级(母亲生病了)
明导读:记得我第一次出远门求学归来的那个寒假,到家时正是一个天晚欲来雪的黄昏,寒风刺骨。进门没有看见母亲,问及乡邻才得知她还在屋背一个叫“欧布新”的自家地里劳作。听后我拔腿跑过去一看,远远地就望见了母亲正在一片绿油油的菜地里挥舞着锄把,北风在这山谷里肆无忌惮地猛刮着。
文|吴波
(一)
淡淡的阳光,透过窗户跌落在贵阳这家肿瘤医院的角落里。六楼的25号病床上,母亲伴随着轻微的呻吟静静地睡着了。我在拥挤不堪的床头择一小地沉重地坐下来,望着近处林立的高楼和远处飘移的白云,木然地发呆。
这是一个立秋过后不久的下午,我放下公务从几百里外的乡镇风尘仆仆地赶上来,一来是为了能尽些孝,二来也是为给之前也请了假来照顾的几个弟兄换个班。尽管当初父亲也跟随着上来了,但大字不识一个的他,要来为母亲办理入院的相关手续,带母亲上上下下去各科室间作名目繁多的检查,这对连电梯都不会用的一个农村老头子来说,很难,简直是举步维艰。
母亲入院已有两个星期,负责办理手续的我们已换了两拔人。只苦于当前入院的检查名目实在太多了,直到我进来的这个星期,才把常规检查作完。当时,听交接班的四弟说,明天医生就可以拿治疗方案了,心头释然了许多。
母亲的病情是由一个不起眼的小脓包引起的。
今年回家过春节时,看到她本已日渐苍老的脸部鼻梁上敷了些草药,问是怎么一回事,要不要去医院做个检查。她连连摇着头说无甚大碍,就长了个小包包,找些草药敷一段时间就好了。
对于长年与荆棘毒草、镰刀锄头以及牛虻蚊虫打交道的农村人来说,哪一个的身上不生些小脓包留一些小创伤呢?当时我们也确实这么认为,也就没有过多地放在心上。
直到后来草药医师换了几个,还是不见好,且有不断肿大的迹象,才送到县城医院里来,经医生切割一小块肉疮送省里化验,确诊为癌细胞后,全家老老少少才大吃一惊。慌慌张张送到地区的一家医院去治疗。放疗了一个多月,不但不见好转,面部越来越肿得厉害了,两眼间的鼻根部通了一个鸟蛋大小的窟窿,现出白森森的鼻梁骨,四周肿得红通通的。
无奈之下,又只好转入省里的这家医院。最为糟糕的是,通过核磁共振以及CT照片,发现那些可怕的病毒已扩散到大脑以及体内的肝脏去了,这不啻为一个晴天霹雳,眼前只有抓住化疗这根稻草,看看能否救母一命了。
(二)
西方人说:“我们都是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那一口被咬得深或者浅,那是命中注定。尽管我们都知道生老病死是人生不可逾越的规律,但一旦落到自己的头上来,却难以做到如庄子般“击盆而歌”的超脱了。就比如此时的我,眼睁睁地望着病床上的母亲,一个给予自己生命并付出了一生心血的人,目前神志尚还清醒,尚能下床步行的人,却被上帝“咬烂”了,是如何地心如刀绞!
当前母亲疼痛的部位还仅限于面部,她说恨不得把这一脓疮割掉。我知道真正的疼痛的还没有到来,当体内的细胞进一步扩散恶化过后,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而这些,作为文盲的母亲是不知晓的,仅凭她目前的一点有限的药理知识,只知道癌症这东西很难治好。因此也没有那么乐观,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把生的希望不停地寄托于护士前来替换的几瓶药水上。
医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第二天上午,左等右等,好不容易才盼来了主治医师查房,只见他们简单地询问了一些状况后,又回到办公室拿出母亲这十多天来查出的各项生理指标分析研究。
临近下班时,才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去告知会诊结果。主治医师是个叫金风的女医生,50来岁,带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温文尔雅。她严肃地告诉我:“你母亲的病理细胞已扩散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只有采取药物化疗。但她老人家的心脏不是很好,免疫能力很低,手术下来风险很大,你们家属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接下来简要地向我分析了一大通可能出现的意外。我内心被一种悲凉的情绪充斥着,别无选择地说:“回去也只能坐着数日子,就下一回赌注吧,至于要出现意外,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样风险那样风险,不治疗才是最大的风险。”
尽管家属已立下了生死契约。但院方还是出于谨慎,叫我们下午再去作一次心电图检查。排了大半天队,终于有了结果,诊断为间歇性房颤,药物作用后极有可能带来心肌梗塞等风险。第二天上午又叫我们去作心电图24小时监测。
如此一来,又要意味着再花1-2天的时间来检查。一向老实巴交的父亲也坐不住了,嗔怪医生说能否治疗干脆给个痛快说法,不能再这样折腾来折腾去。他还说在我们乡镇那些卫生院,一般检查仅半天的时间就搞定,到这里来光是这样检那样查已耗半个多月来了,一个好端端的人也要憋出病来。
我也理解父母的焦灼心理。但是还得由医院说了算,只好又劝慰他们好好配合。心理还暗暗担心母亲的化疗是不是会因其心脏问题而被迫叫停,那样还不知如何向她交待呢。因为疼痛中的母亲一直盼望着医生尽快上药来,哪怕再痛苦她也愿意接受。
不难看出,母亲求生的愿望多么强烈!
(三)
在等待检查的漫长过程中,母亲的面部一日一日地脬肿起来,身体却一天一天的消瘦下去,上下楼都显得很吃力了,我只好搀扶着她慢慢行走,就像当初她以极大的母爱扶着我蹒跚学步一样。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穿越时空的遂道,我觉得四十多年前的她牵着我,和现在我搀扶着她,虽说环境不同,心境竟是如此的一致。只是,作为我们父女母子一场,就像台湾作家龙应台在《目送》里所写的,我和她的缘分就是不断地目送:她欣慰地看着我渐渐长大,我忧伤地望着她慢慢变老。“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在这目送的过程中,我们都觉得时光过得太快了,仿佛尚有诸多事情还没做好,彼此竟已变大变老。
母亲姓张,是本镇张往村人。虽说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可是她的童年人生并没有因朝代的更迭而享受过多的阳光雨露。由于外公的早逝和外婆的改嫁,幼年时就饱偿了寄人篱下之苦。加之那是个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集体食堂时代,童年留给她们这一代人最为深刻的记忆,恐怕就是“饥饿”了。
打小时就听母亲经常提起,为了裹腹,路边的野菜早就被她吃了个遍,连白麻栗树上长出的果籽,也被摘下来捣烂了和成面团煮吃过。每当回忆起这些辛酸往事时,母亲总是说:“那味道真个苦啊,吞进去不容易,排出来更难。乡村茅厕里一蹲就是大半天。有些娃崽实在屙不出来了,只好由大人拿着木棒慢慢去抠……”。
或许是由于当初的营养不良,母亲长得很矮小。加之天生有瘸腿缺陷,人不算机灵聪慧,头脑也很简单,在邻居中常常被人取笑。平常找个伴来唠嗑的机会也很少,就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来证实自身的价值,与同是憨厚朴实的父亲一起撑起这个家,一箪一瓢地哺育子女,一砖一瓦的添置家园。
如果说要用一些凝炼的词汇来概括母亲的一生,我想贴在她幼小时代的标签就是“苦难”,成人后便是“辛劳”,直到晚景才从儿女身上得到些许微不足道的“幸福”。
由于没有什么文化,父母一生就信奉“天道酬勤”这个理。尤其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分田到户后,父母把乡下的农活干到了极致。起早贪黑地奔走于田野间,胼手胝足、含辛茹苦,披星戴月、风雨无阻,是我们那一带出了名的“劳模”。


正是有了他们的这份不惜气力的拼命精神,才把我们这五兄弟拉扯长大的同时,还能供我们上学读书,其中有四个还读到了中专,上了大学,幸运地成了国家干部。要知道,在那个没有任何国家免费和补贴的年代,我们在学校每用的一分一厘,都是父母在自家的几亩薄地里勤扒苦做换来的啊!
记得我第一次出远门求学归来的那个寒假,到家时正是一个天晚欲来雪的黄昏,寒风刺骨。进门没有看见母亲,问及乡邻才得知她还在屋背一个叫“欧布新”的自家地里劳作。听后我拔腿跑过去一看,远远地就望见了母亲正在一片绿油油的菜地里挥舞着锄把,北风在这山谷里肆无忌惮地猛刮着。
显然她是决心要在大雪封山之前把这块油菜地薅修好,以羸弱之躯立于风中与之搏斗。地头,一堆柴火在冒着一缕有气没力的青烟。我知道,那是她准备着实在冻得受不住了,才去取暖一下……
多少年后,当满文军的一首吟颂母爱的歌曲《懂你》唱响大江南北时,我也很受感动,脑海里时不时地浮出母亲在那个严寒的天空下劬劳功烈的场景。
(四)
这样一位把爱与世界全给了我的母亲,从我这里得到的是否就是骄傲与自豪呢?望着病床上静静地躺下的母亲,我在反省着,也在忏悔着。因着她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一些生活上的邋遢习性,经常遭我们子女的奚落,又因着一些母性固有的唠叨,遭到我不耐烦的呵斥也是常事。
最令我愧疚的一件事,是在我就读乡镇中学的一天下午,我所在的一楼班级的教室里,全班同学在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突然,窗外传来了母亲叫唤我小名的声音:“七—唉—,七—唉—”的叫着。声音很脆亮,是当年呼惯了我回家吃饭的那种声音,完全盖过了老师的授课。

课堂秩序顿时被这一呼声打住了,所有的目光都寻声望去,我的脸也“唰”地一下子通红起来,恨不得有地缝钻似的赶紧跑出去。原来是母亲从七八里外的乡下挑菜到集市上卖完后,找到我学校里来了,随后颤巍巍地从厚棉的布衣襟里掏了一卷被捏得皱巴巴的零用钱递过来。还没完没了地嘱咐着我要用心向学。我迅速地接过了她的钱,接得天经地义,接得理所当然,还未等她唠叨念完,赶紧把她支走了。她也没再说什么,担着那一对空篮子一跛一瘸的默默离开……
都说儿不嫌母丑。少不更事的我,正是虚荣心旺盛的时刻,为着母亲当时不知礼节的举止,以及衣着邋遢的形象,感觉真真地颜面扫地了一回,仿佛在同学眼里“矮”了半截。后来,我看了台湾的那部电影《搭错车》,以及影片里的主题曲《酒干倘卖无》时,才明白当时的举止,是何等地伤着自己母亲的自尊心啊。
对于这些,母亲似乎从没计较过,倒是还经常念及我尽的第一份孝心来。那是我刚上师范读书不久,在外务工的堂叔回家路过我所在的城市,和我留宿了一夜。第二天送他回去时,我因思母心切,特地托他给母亲捎带了一包学校里蒸煮的馒头,这种馒头是用上等面粉做成的,对于来自农村的我来说觉得非常香喷。
据说她收到后很是高兴,为着即将有出息的大儿子,她把馒头分成了若干瓣,散给隔壁的邻居们一起分享,至今还时常念起,并且脸上总是荡漾着幸福。至于后来我工作了,借着出差和学习的机会,也给她带来一些香港的月饼、上海的酥糖、西安的糕点什么的,味道应该不错,但却没听她再次提起了。
(五)
心电图24小时的动态监测结束后,医生把记录仪上的数据又导入电脑进行了一整天的分析比对,第三天才得出结论来。结果很糟糕!定性为室上性心律和室上心律均失常。这样的身体状况若硬上化疗,随时都有心肌梗塞或心脏骤停的危险,医生是不敢贸然用药的,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先把心脏治好后再化疗。
这怎么还能行呢?当前母亲的癌细胞已扩散到了这种地步,只怕心脏还没调节好,黄花菜早都凉了。尤其是近两天来也许是体脏内的癌细胞已开始恶化的缘故,母亲已经什么都没有胃口,而且连连呕吐,虚弱得连呼吸都困难了。找到了管床的龙医生,欲探个根底。她很无奈地告诉我:“作为医生,救人是第一天职。

当发觉这个人还有救时,无论家属怎么困难,我们都得想方设法去救;当发觉病人希望很渺茫时,无论家属下多大的血本也无能为力。”她还告诉我:“肿瘤科室的病人一般分为四个等级,你母亲的病情已达到了最严重的层次--四级。化疗也仅是一种手段,也许能了却你们作为家属的一腔心愿。但是,有时花再大的钱也并不一定能买来平安。我说的这些,你应该懂的!”
听到这些委婉的劝解,我顿时坠入彻底绝望的深渊,木然地望着窗外的天空长叹一阵。回到病房里叫父亲出来商量了一通,最后还是决定撤退,只有带回老家去死马当作活马医,胡抓些草药来试试了。
为了避免刺激母亲,我们对她的病情一直隐瞒着,当她听说要出院时,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种求生的本能促使她喃喃自语:“你们就叫医生来试试吧,不试怎么晓得呢?再大的痛苦我也能接受……。”
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好编一些善意的谎言来安慰她,说这里的西药不管用,我们已在老家联系好了草药医师,那个效果更好。没有文化的母亲最后也相信了,很积极地配合我们办理出院手术。
当护士前来将输液管拔掉时,我分明看到拔掉的不仅仅是一根管子,而是母亲的那根救命稻草。不由悲从中来,赶紧跑下楼去找个僻静之处,放声痛哭了一场。
下午5时,我与父亲背着沉重的行李,搀扶着步履同样沉重的母亲,赶往贵阳北站乘坐当天下午由昆明驶往长沙的高铁,沉重地--回家。
这是母亲第一次坐高铁,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