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超金瓶梅里的梦(王志超金瓶梅里的梦)
《金瓶梅》里写梦的地方,不算太多,仅16次;加上一些似梦的幻觉描写,对人物作潜意识开掘处总约不过20次。其中,第六十二回梦最多,有6起;其次是七十九回,写了4次梦。
字数最多篇幅最长的梦,见一百回,吴月娘在永福寺做的梦,有955个字。最短的梦在六十二回,李瓶儿说,“那厮但合上眼,只在我眼前缠”,只12个字。二十九回西门庆病中梦见花子虚、武大讨债,也只14个字。
《红楼梦》里的梦,有32次,正好是《金瓶梅》的双倍;最长的梦在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8300多个字,比吴月娘的最后一个梦长得多,那是理解书中人物(尤其是女性)命运之纲要。
吴月娘的长梦显示了西门家族气数的了结和人物的最后结局,也是全篇的一个虚幻的“句号”。
《红楼梦》中最短的梦是宝玉梦中听见秦可卿死讯,林黛玉梦中听见有人称薛宝钗为宝二奶奶,也都只十多个字,把个宝玉的怜香惜玉之情,黛玉的最重的心病写尽写绝。
可否从中看出这两部巨著间的关联?
《红楼梦》里的梦,量多,做梦的人广,内容也较泛,且有喜有悲;《金瓶梅》里的梦,量少,做梦的人较集中,内容也较狭窄,且有悲无喜。
《红》书里的梦精巧,细腻,充满了人情味;《金》书里的梦较为粗疏,人性的直露,尚未升华到“情境的工笔细描”,且多夹杂因果报应。
《红》书里的梦比《金》书里的梦重要得多,《石头记》“凡例”中脂砚斋根据书里宝玉做梦,梦中有曲名“红楼梦十二支”,认为“梦是其全部之名也。”
《金》书里的梦当然不是小说的“全部之名”;但也颇重要,与人物,与情节,与作者的主体意识都有关联。

《<金瓶梅><红楼梦>比较论稿》
不言而喻,写梦即写人。写梦,是一种展示人物命运的特殊手段。《金瓶梅》里梦的描写,与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联;很多梦都与主要人物之死有关,有的梦出现在人死之前,有的梦在人死之后出现。
这里,梦,是某种暗示,甚或是一种象征,且绝大多数是一种噩耗,一种衰败、陨落、消亡的“信息”,一声“丧钟”,一种人物命运的预示。譬如,六十二回西门庆和应伯爵同时梦见簪儿折了,“不想前边(李瓶儿)断了气”。
西门庆死之前,吴月娘也梦见“攧折碧玉簪”,“跌破菱花镜”……再如五十九回,李瓶儿梦见花子虚对她厉声斥骂之后,时三更三点;次日,官哥儿即断气身亡。
第一百回,吴月娘做完全书最长的梦之后,孝哥儿也出家了。在这里,梦几乎是一种“神谕”;带有原始部落对梦的理解的痕迹。
书中人物对梦的重视和虔诚,也是原始部落把梦视为神灵之谕的态度的某种延续。在这里,梦是可怕的,几乎是阴界神灵的召唤和灵魂的显现,生死攸关,直接成了人物运命中厄运到来的“先兆”。
亚里士多德认为“梦是一种延续到睡眠状态中的思想”。柏拉图也认为“梦是一种感情的产物”。梦,确是人物心态的曲折的、“非现实方式”的反映,写梦便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描写。
第九回,武松在武大灵前梦见武大,实际上是武松复仇心理的曲折表现;第十七回,李瓶儿梦幻中见西门庆到来,也是她爱慕、思念西门庆欲攀附西门庆的心理的写照;而李瓶儿常梦见花子虚,这是“做贼心虚”的心态的反映,一种违反了伦理道德规范而心有余悸,甚或胆颤心惊的情绪的再现。
书中的梦确是因人而异,各人的梦,都打上各个人物性格、思想、情感的烙印。真可以说是一人一梦,梦如其人。
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梦(托不同的梦);梦成了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方面和重要手段,甚至可以说是人物形象的重要部分,展示人物关系,构成作品人物形象体系的一种手段。
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史,是人物命运史,既然梦是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命运的手段;那梦自然与情节也不无关系,甚至是情节发展的契机。
譬如武松梦见武大后,立即采取复仇的行动,引出了后来的诸多情节。李瓶儿的梦“催化”了她的死,也引发了不少场面、事件和细节。
春梅梦见潘金莲后,清明去永福寺为金莲祭坟,巧遇吴月娘和孟玉楼,带出了一番今非昔比的感慨,展现出了与前大不相同的人物关系。
吴月娘的最长的梦,点出了带有象征性的“孝哥出家”的人物命运的结局,并为全书作“结”。
可见,不少梦的描写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它属于小说的“情节部分”;它使“现实”与作为现实的曲折反映的“虚幻”有机结合,使人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有机结合。
梦属于人的精神世界,是一种非规律化的混乱的思维方式;但它写在小说里,也就成了物质世界和人的精神生活、人物关系的反映。这在《金瓶梅》里也是十分明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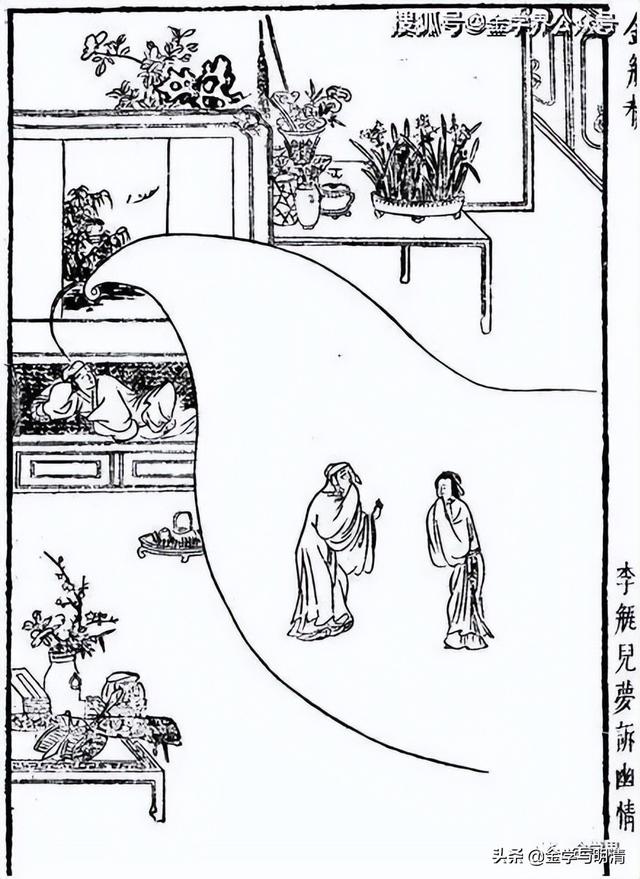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若就与梦有关联的几个主要人物作具体分析,就更明白梦的描写对塑造艺术形象的重要作用了——
李瓶儿。这是小说中与梦关联最多的一位女主人公。
有人说,李瓶儿的性格前后不统一,其依据是,前部分李瓶儿泼辣刁悍,好色纵欲,私通西门庆,气死花子虚,嫁蒋竹山,不久,就又斥骂、赶走了他,这一切都表明她似乎是个很不正经很凶狠的女人;后部分却是慷慨大度,审慎小心,温良恭俭让,连西门庆都说她“性子极忍耐得”,俨然一个善良的女性。
其实,这正是人物性格非单一、复杂化的体现。在进入西门家族之前,李瓶儿不满于花子虚和蒋竹山,而倾心于西门庆,一旦嫁到西门家,如愿以偿,人物的环境变了,性格上有所变化,这是正常的,符合生活真实的,也正显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及其必然性,人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有迥然不同的表现,这是普遍规律。
这可以用有关李瓶儿的两个梦加以形象化地注释:第十七回,李瓶儿在梦幻中见到西门庆到来,这是她爱慕、思念西门庆的心理的写照,甚至一连几次,任狐妖假名抵姓摄其精髓,若按正统伦理道德衡量,可谓荒淫之极。
可李瓶儿成了西门家族六娘之后,对西门庆却是百般温顺,体贴入微;死后她还托梦给西门庆说是花子虚在阴界告了一状,要西门庆防备。
梦中还说,“诚恐你早晚遭他毒手。”足见她对西门庆的深情厚义。她对官哥儿也充满了母爱。前者犹如“淫妇”“泼妇”,后者宛若贤妻良母,判若两样。
实质是不同环境所决定,针对不同人物所致,对西门庆有所好、有所爱,对花子虚、蒋竹山有所恶、有所恨。
相异中又有同一性,即对西门庆的爱恋、忠诚、温存。甚至,七十一回西门庆借住在何千户家,她还托梦给他,告诉他,她已寻了房儿,“咫尺不远,出此大街,迤东造釜巷中间便是”。足见她对西门庆的倾心,与过去,生前,在阳界并无二致。
李瓶儿的衣饰,生前世间和死后阴界也不同:第十五回,吴月娘等人到李瓶儿家观灯,“李瓶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盈堆,凤钗半卸,鬓后挑着许多各色笼儿”,犹如官宦人家的贵妇人;而李瓶儿托梦给西门庆时,梦中形象是“雾鬓云鬟,淡妆丽雅,素白旧衫罩雪体,淡黄软软,袜衬弓鞋,轻移莲步,立于月下”。
衣饰尽管不同,但对西门庆却十分专一,这些不同衣饰都是为西门庆而着而戴,所谓“女为悦己者容”,不可谓其性格前后不统一。
围绕李瓶儿,还有其他几个梦,如西门庆梦见东京翟亲家那里选了六根簪儿,内有一根 [石否]折了……这些梦都带有一定的预示性、象征性,暗示李瓶儿的命运和结局,也都显露了作者对她的一定的同情心。
六十二回,李瓶儿梦见花子虚拿刀弄杖,说他那里买了房子,叫李瓶儿去。李瓶儿又梦见花子虚领着两个人……“告准在阴司,决不容你”。
这些梦,一方面显示李瓶儿有愧于花子虚的心理和心有余悸、胆颤心惊的情绪;另方面也反映了一种冤怨相报、因果报应的意识。
六十二回里,还写了迎春丫头梦见李瓶儿“去也”,李瓶儿即断气身亡的情景。其中李瓶儿有句话:“嘱咐你们看家,我去也。”
这很容易使人想起《红楼梦》里秦可卿托给王熙风的那个梦,同样反映了一个善良温顺的女性,对自己投身并生活过的家族的关切,担忧和希望这个家族能保全实力、门第、荣耀的心愿。
只是贾家也罢,西门家也罢,显赫一时的家族都无可奈何地崩溃倒塌了。研究有关李瓶儿的梦,对认识、把握人物乃至整个人际关系、情节发展都很有意义。

《红楼梦》插图
潘金莲是另一位女主人公。可奇怪的是与梦幻最多的李瓶儿相反,生前,没做过一次梦,只在死后,托梦两次。
一次是托梦给刚从东京回山东清河县的陈经济,要他葬埋,免得日久暴露。可这个在她生前与她打得火热的小女婿,自身难保,未使金莲魂灵如愿。
另一次是托给守备府中的庞春梅,要春梅念母子之情,领埋其无人敢领埋的尸体。与李瓶儿死后的哀荣相比,潘金莲是够惨的了,死后竟一时无人安葬,应了她生前的话:“算的着命,算不着行……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
李瓶儿虽说是“可惜一个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场春梦”,但她病危时,死亡后,西门庆都不惜耗费重金,为之作佛事、道事,其丧事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在全书中为最。而潘金莲却死无葬身之地;靠灵魂儿苦苦哀求,才由昔日女婢埋葬。
这既反映了作者对她的谴责、鞭笞,也包含着作者对她的同情、怜惜。潘金莲确是个既淫又乱之妇,而且这种淫乱还不限于单独的性本能的放肆渲泄,还带有强烈的攻击性的嫉妒本能,以致她因色、因争宠争霸而贻害他人;但是,这一切都含有明显的社会性,由社会及其环境、风气所造成。
一方面,她淫荡,毒辣,自私,凶险;另方面却又聪明、伶俐,多才多艺,而遭受种种不幸。
作者对其恼怒与同情,诅咒与怜惜,都集中反映在她所托的两个梦中。
拿潘金莲与李瓶儿相比较,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尤其是李瓶儿进入西门府中之后。明显地表现了作者“褒李贬潘”(或作“扬瓶抑金”)的倾向。这怕也是潘金莲的“不幸”。
春梅也只做了一个梦,梦见潘金莲托她领埋,梦后担着风险为潘金莲领埋,安葬在永福寺内。她还对周守备假说做了个“梦”:“我梦见我娘向我哭泣说,养我一场,怎地不与他清明寒食烧纸儿,因此哭醒了。”以此为借口,清明去永福寺为潘金莲祭扫。
这一真一假的梦,都表示了春梅与金莲的缘份和情义。作者写春梅也并没有单一化,鞭挞之余仍有所同情,她毕竟是奴婢出身,西门大官人一倒,她便首当其冲被卖出门而前途渺茫。
作者还特别描绘了她与潘金莲的一番情义:蒙难时想着潘,得意时惦着潘;平日常以肺腑之言劝慰主娘;金莲落难,她又一直要设法搭救,以致金莲托梦后,她敢冒大不韪,领埋、祭奠潘金莲。
从一真一假的梦中,读者完全可以看得出,她是个知恩图报、珍重情义之人。南柯一梦,把一个复杂而有明显发展、变化过程的女主人公形象,勾划完整了。

《金瓶梅》连环画
西门庆的梦与“色”有关。最明显的是第七十一回,西门庆在何千户家梦见李瓶儿,且“梦中云雨”。李瓶儿原是托梦给西门庆,告诉他她已寻了房儿,不想西门庆却“供他(她)相偎相抱,上床云雨”,还“不胜美快之极。”
在西门庆身上,作者写尽了“戒淫”的意旨。除了“梦中云雨”而外,还写了西门庆因色而梦,因梦而病。
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从王六儿家中醉出,三更时分,阴云昏昏,打马过街之际,幻见一黑影子从桥底下钻了出来,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回家之后又去金莲房里过夜,然后得病。
这次梦幻受惊,正发生在他与王六儿和潘金莲两次性行为之间,正好说明他的“梦”与“色”的关联。同时,西门庆(连同李瓶儿)的梦与“财”也有关。西门庆娶李瓶儿,弄到一笔原属花子虚的财产。
李瓶儿常梦见花子虚来“缠”,而花子虚冤魂纠缠(梦)的具体内容是:花子虚在阴界告她,对她说:“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五十九回)。
尤其是西门庆得病之后(七十九回),在病中幻见花子虚、武大讨债。这里武大讨的是命债、风流债,花子虚讨的债还得加上“财物”债。
我们找遍全书也找不到武大索“财物”的梦,因武大本无财,西门庆奸娶潘金莲只是为了贪图享乐,羡慕她的美貌风流,为了“占有”这个尤物,他还倒贴了些银两。
这是西门庆与李瓶儿同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关系的很大差别。这种不同的人物关系也显现在梦中。
这种与“财”挂钩的梦,确是有独特性质的,或多或少反映了那个时期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特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的金钱关系的印记,正因为“逐末营利”,“逐丰游食”成风,“末富居多,本富居少”,西门庆才会这样巧取豪夺,以致夺友妻,占友“财物”,朋友(花子虚)死后还来讨“债”。
西门庆的占有确实是财与色双重的、是“好货”与“好色”的结合;在他的淫乱生活中,充满了“铜臭气”。
这里的“梦”,对塑造西门庆这个荒淫无度、对女性占有欲特强的色魔形象,非正常化野蛮掠夺、积累的商人形象,起了深化作用。
他在财与色的占有上确是独特的,对后世是有影响的;这其中,梦的深化作用也值得借鉴。
在西门庆死之前,吴月娘做了个“大厦将倾”的梦。这个梦暗示西门庆即将死亡。而西门庆的死,其本身就带有某种象征性;它象征着西门家族从发迹到衰亡,是发迹的终点,衰败的起点。
这个对金钱、女色、权势的占有欲极端膨胀的恶魔的死,这种官、商、霸结合、新型的商业关系与传统的宗法权势,宗法思想相杂交的家庭的崩溃、瓦解,无论就小说史而言乃至社会史、文化史而言,其意义都是独特的。
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黑暗、腐败、没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连宗法制度也受不住“好货”、“好欲”的冲击,直至崩溃。另一方面,其中也包括了这样一个内涵:新型暴发户商人的发迹,固然是对封建旧秩序及其人与人关系的冲击、挑战;
但同时,这种新型商业资本(萌芽)及其代表人物,在强大、顽固、僵化的封建势力面前,却是软弱无力的,它的发迹,也必须以一种“攀高枝”的手段,借助、依附、投靠封建势力(如韩道国送亲女给翟谦为妾),并为封建势力所强化,进一步转化为封建势力的代表(如西门庆也做了官);
在封建势力的笼牢中,限制下,它发迹到一定程度,到达饱和点,也必然会“大厦倾”式地解体、消亡。
当然,正如恩格斯所说:“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限制。”西门庆这个形象也未受市民阶层的局限。
小说在描写这个形象时,对于他的“好货”,他的雄心勃勃,他的商业活动及其财富积累的特种手段,他在商业活动中所给予其他人物的同情、资助、支持,都作了如实的肯定性的描写。
五十六回作者直接说:“人生在世,荣华不能常守,有朝无常到来,凭你堆金积玉,出落空手归阴”。因此,西门庆仗义疏财,救人贫难。人人都是赞叹他的。如他对常时节的周济,对吴典恩的恩典。满足李智、黄四的要求。

《金瓶梅》连环画
西门庆说:“兀那东西(金钱),是好动不好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积下财宝,极有罪的”(五十六回)。
这种富贵无常是典型的商人心理,商人价值观。但同时,作品又无情地揭示了以西门庆为代表的这一阶层人物的自私,贪婪,荒淫,邪恶;“超前”地揭露和批判了金钱关系的丑恶罪行和其所造成的种种悲剧;尤其是其本身在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面前,无法超越,无法摆脱的悲剧。而这一切,都在对西门庆的死以及他死前的种种恶梦的描写中得到深化。
罗丹说:“丑的也须创造”(《文艺论丛》第10辑第404页)。拿陈经济这个丑的形象的塑造及其梦来说,就显得比较“单一”了。
第九十三回,陈经济腊月打更,已经落难,但他仍然梦见当初在西门庆家的荣华富贵,如何与潘金莲勾搭,顽耍戏谑;一副荒淫无耻、轻薄浮滑的嘴脸。
西门庆死后,我们可以把陈经济看作是西门庆色情生涯的延续;但两厢对照却有许多不同处:西门庆的好色是他“财产”和“女性”占有欲的表现,目的是为了满足占有欲;陈经济却是一味好色,以本身享乐为目的。
西门庆在玩弄女性时表现出一种施虐的本能;而陈经济却带有一些“高就”的意味。西门庆对待被他勾引、蹂躏的女性是一种“俯视”的角度,而陈经济却是“仰视”角度。西门庆的性行为,在他看来是符合封建伦理纲常和商品经济萌芽时期的人与人的“交易”的;而陈经济却是违反封建宗法规范的。
西门庆对女性常常是恩赐式的玩弄;而陈经济却往往是偷香窃玉式的。正因为陈经济是一个痞子式的花花公子,所以才会在落难并无从摆脱困境时做了那么一个浮幻、荒唐的梦。
这个梦,既是他与潘金莲乱伦关系的终结,也为他后来与庞春梅的通奸淫乐,埋了伏笔。潘金莲生前与他打得那么火热,死后托梦于他,他却无从为小丈母娘情妇埋葬。这完全是个“小人”。
作者让他死于张胜刀下,又让他做了那么个梦,表明了作者对他的鄙视、厌恶和鞭笞。
这个形象连同其污秽之梦,概括了那个时代的肮脏、淫糜、畸形、变态的面貌,风气和把人变成魔的丑恶环境。
吴月娘的梦很符合她的主妇的身份;也与她的信仰、意识、情感相吻合。
七十九回吴月娘在家做了一个梦……月娘与金莲争夺一大红绒袍。这既反映了作品中矛盾冲突的重要方面——妻妾不和,也反映了作为家庭主妇吴月娘对西门庆偏爱潘金莲,恩宠李瓶儿的不满。潘金莲有美貌风流缠住西门庆,李瓶儿得子受尊;这两者的挑战,压力,迫使吴月娘也希望早生贵子,笼络住西门庆,保住主妇地位。但她的方式是焚香祈祷以及求仙药仙方(得胎)。
这与她笃信佛、道两教有关。正因为她是佛道两家的忠实信徒,她的有关梦的意识自然带有迷信因果色彩。
同一回,即西门庆病后死前,她请吴神仙圆梦:大厦将倾,红衣罩体,攧折碧玉簪,跌破菱花镜。在她看来,这是不祥之兆;果然不久西门庆病故。

《金瓶梅》插图
大树一倒,吴月娘无法支撑这个家族,于是,死的死,散的散,改嫁的改嫁,被卖的被卖,逐出家门的逐出家门,连她自身也无法立足——在永福寺又得一梦,即书中最长的一个梦,一灵真性同吴二舅等男女带珠宝前往济南投奔亲家云离守,在梦中险些受辱,经历了一场惊吓,于是“适间梦中都已省悟了”。
而所谓“省悟”,又引出了带有象征性的“孝哥出家”的人物命运的结局,为全书作“结”。在吴月娘的深层意识里,梦简直是因果报应,是神灵的谕示。
这种梦的观念带有某种正统性质,有一定的代表性,与作者的主体意识有相通之处。
笑笑生当然不可能预测,他的后世人们对梦会有那么多的理解和认识:譬如有人把梦看成是一种“病变”,一种“肉体内在障碍的表现”(印度盛行);也有人视梦为“一种内在的对美与善的追求”(如歌德);更有人视梦为一种“灵感的、创造力的启示”,甚至直接把梦看成是又一种思维方式,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思考,有时能解决人在非梦状态下无法解决的难题。
也有人相信“梦是生活的预演”(如阿德勒),用来“断定生命的欲望”(如赫尔尼)。
弗洛伊德则坚持说梦为“愿望的达成”,哈特曼认为人可借“梦”而追溯出自我的另一领域——潜意识……笑笑生只能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和选择来反映梦,以其当时不可能没有的佛(道)教的观念来写梦。
人类对梦的认识和看法一直是相互矛盾的;其中唯物的也好,唯心的也好,也都有它各自相通之处。
纵观《金瓶梅》全书所有关于梦的描写,不难体会出笑笑生对梦的认识也有双重性:作者书中所写之梦,一方面带有迷信、神谕,因果轮回的色彩,另一方面作者又把梦写成人物思念已极所致。这两种梦的描写体现了作者的两种梦的意识和观念。
一方面承认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七十九回里,作者明白地写道:“自古梦是心头想”。
另方面,书中的梦,也是作者人生如梦的消极心态和因果报应观念的体现。作者在七十四回里写吴月娘听黄氏卷时,说“功名盖世,无非大梦一场,富贵惊人,难免无常二字。”
吴月娘最后一梦之结果是有所“明悟”,“明悟”结果是孝哥儿出家。从全书看,正如有关“色”“性”的观念(有关描写所体现)是矛盾的一样,小说中有关梦的描写所体现的梦的观念也是相矛盾的:
一方面透露出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另方面又强调梦即“空”,最后终究皈依佛门。这也是书中的梦的最后的归宿。就梦与色而言,或色中有梦,梦中有色;或因色而梦;或色就是梦。
书中色梦相浸的种种描写,也是一种戒淫警世思想的表现。尤其是六十一回“四梦八空”的描写:“思多也是个空,情多也是个空,都做了南柯梦;思量他也是空,埋怨他也是空,都做了巫山梦;亏心也是空,痴心也是空,都做了蝴蝶梦;得便宜也是空,失便宜也是空,都做了阳台梦。”
在这里,色是空,色如梦,空即梦,梦即空;色、空、梦三意一体,道出了有关梦的深层意识,也暗示出全书一重要立意:色如梦,梦即空。
这代表着许多“艳文学”的同一的思维模式:色—梦—空。主人公贪色纵欲,后均有所“明悟”乃至“大彻大悟”,最后堕入空门。这正好又回应了佛家以色戒色的彻底的辩证法。
作者的有关梦的观念(及描写)上的矛盾,实质上也是“天地之间,以好生为本”、生而有性,与人生“无非大梦一场”归于佛道的矛盾,以及“人欲横流”与“四大皆空”的矛盾,在“梦”上的反映。
这种矛盾明显地反映了作者主体意识、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局限与不统一。然而,无论从作者主体意识还是小说的客观效果,从情节特别是结局来看,在这两种有关梦的观念中,“人生如梦”和因果报应观念(及其表现)还是占了上风。

影松轩本

文章作者单位:无锡市文化局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三辑,1992,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