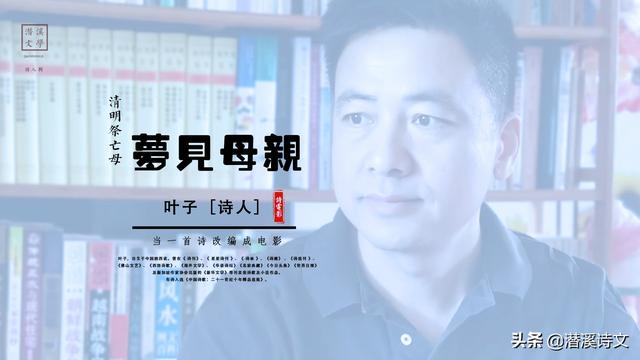沈阳盛京的故事(沈阳故地寻访记)
叶琳昌
作者小传:
叶琳昌,1936年11月生,上海嘉定人。1953年毕业于同济高工土木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一机部沈阳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建工部东北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渤海工程局、第二工程局,四川省第九建筑工程公司(现为重庆第九建筑工程公司)见习技术员、技术员、工程师、技术科副科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等职。目前兼任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防水分会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上海市建设系统专业技术学科带头人等职。历年来共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专著18本(含与别人合作)。并有多项科研项目,获得国家奖励。上述专著、论文等有关文献已被上海嘉定图书館珍藏。
东北沈阳,是我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地方。1953—1955年期间,我曾在那里落下眼泪,洒下汗水,为共和国建设捐献青春而自豪。那时的沈阳,像初升的太阳,到处充满着希望和活力。青年时代的记忆是无法抹掉的,特别在退休后的清闲日子里,怀旧的情结更加炽烈。趁去北京参加屋面工程技术规范审定会的机会,我终于在2001年的4月中旬,转道回到了阔别已有半个世纪的沈阳。
铁西区兴华街新9号,我曾在这里生活过近2年。这幢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兴建不久的三层单身住宅楼,在当时空旷的场地上十分显眼。该处交通方便,出门不远是铁西广场,有轨电车(当时沈阳人称之为“磨电”)从南北方向由沈阳南站通向铁西区各主要街道。在单身住宅楼内,每个房间的面积约有15 m2,一般住上4—5人,配有小桌子,冬天有蒸气采暖,住宿条件在当时算是不错的。在这幢住宅楼内,住着上百人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学生。白天一早,大家都匆匆忙忙到各自的工地去上班,整幢楼内寂静无声。一到晚上,楼内开始热闹起来。操着不同口音的学生诉说着今天工地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偶尔也听到一些歌声和琴声,而更多的人则坐在床上看书学习,汲取新的知识。只有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大家才会相聚在一起奕棋打扑克。记得同室的统计员、上海籍的马家驹,对棋谱颇有研究,下棋时又能灵活多变,很多人都败在他的手下而心有不甘。而王牧西(贵州人)等人打桥牌时也工有心计,当每副牌结束时都要对着记分表反复切磋,有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让人感到在欢乐中追求一种新的升华,这是何等平静而又幸福的日子。
现在回忆起的一些室友,在很早的时候就没有联系了。如今我踏上原来熟悉的地方,旧的单身住宅楼早已不见踪影,代之而起的是一幢一幢错落有序的高层建筑。但有一点是没有改变的,对面的铁西百货大楼还在(图1),仅仅是在原址旁边扩建一新。我信步走到那里,抚摸着原来的墙面,心中疑惑地问:这就是我几十年前常来的地方吗?记得在“铁百”的一条小街内,过去是专门卖小吃的地方,煎饼、吊炉饼、豆腐脑、鸡蛋羹、猪下水汤,都是我们常吃的早点,现在这里却看到的是小百货摊位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我还在努力寻找当年的食店,还想品尝一下老板娘做的吊炉饼、猪下水汤……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4年春节年初三的那天,在北京工作的陈鼎表兄(小时候我们称他为昆荣哥哥)专程来沈阳看望我,带来了家乡亲人的问候与鼓励。陈鼎表兄长我十多岁,他家住在离嘉定娄塘镇不远的北井亭村,小时候常有走动。他们全家上下精于农作,勤劳节俭,且热情好客。他与弟弟陈奕(我们称他为阿华哥哥)俩人又擅长木匠手艺,在乡里颇有名气。1949年之后,他们都响应祖国号召,先后外出参加工程建设。陈鼎表兄参加工作不久,即在北京铁路建筑单位担任施工员等领导职务。他的到来,是我参加工作后遠在他乡看望我的第一位亲人,在倍受鼓舞的同时使我感动得留下了热泪。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好好工作,吃苦耐劳,感恩父母,报效祖国。于此,我对新的生活更充满了期待(图2)。
随后我来到了和平区的太原街,这是一条著名的商业街。恍然间,好像我又找回了当时的感觉。当我走进原来的新华书店,踏上已显陈旧的楼梯,在“建筑工程”的书柜前,我写的《防水工程》《建筑防水工程渗漏实例分析》《防水工手册》等书赫然在目。一时间,惆怅如入梦间,此时我又想起每当星期天休息的日子里,我都要与潘家怡(同济高工同班同学)一起,来此寻找新书的情景。正是这个地方,正是这些总结人类智慧的书籍,使我能够在事业上不断取得进步,抚慰着我忙来忙去并不安宁的心魂。
在太原街背后,有一条狭长的小弄堂,在一个装饰一新的建筑物上,我熟悉的“东北电影院”几个大字使我怦怦心动(图3)。那时候,我们都愿意在这设备一流的电影院里,欣赏一些新上映的中外著名电影,在驱散一周来疲劳身心的同时,也使精神上得到一些美的享受。现在,我伫立在售票处的广告板前,许久许久地不愿离去,还遐想那再也追不回的梦……
走了一上午,感觉到有些累,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我跟陪我来的刘启太(1972年在四川相识并在重庆479厂一起共事过的东北设计院的老朋友)说,最好到南站附近的一家“勺园”去吃。这家饭店是上海人开的,那时候我们常到那里去吃炸对虾、滑溜鱼片、炒猪肝、糖醋排骨、木须肉等。但是我们走了几圈,仍不见勺园在那里?在多次询问之下才知道这家名店还在,但不知搬到哪里去了?这样,我唯一的希望,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落空了。
在往回赶公共汽车的时候,我特意在铁路沈阳南站周围兜了一圈。这个上世纪40年代由日本人修建的火车站,在当时堪称一流,如今还在服役(图4)。而在“文革”时被毁的苏军解放纪念碑,又重新修复供人瞻仰。原来那清洁宽阔的广场,现今被川流不息的人群和商贩的叫卖声所淹没。1953年9月7日那天,我与几位同学就从沈阳南站走出来,前往位于肇工街104号的一机部沈阳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报到。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又回到了你的身旁,想从这里再次走进那时的生活,而一路的不顺利,使我的希望逐渐暗淡。但从这里开始工作和点燃的火种,在我的心中却仍有甜蜜的回忆。我行于此地而不知此身何在,让寻梦的希望留到最后。
我匆匆地走来,又匆匆地回去。忽然间,眼前的一切锁住了我青年时曾经拥有的欢乐时光。(写于2001年五一节,2022年6月补充定稿)

图1(a) 沈阳铁西百货商店在原址上扩建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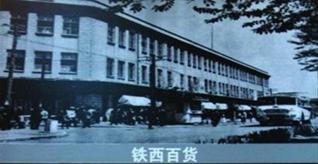
图1(b) 沈阳铁西百货商店在原址上扩建前的老照片

图2 陈鼎表兄1954年2月5日专程来沈阳看望我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胸前口袋上还别着在当时引为骄傲的
“一机部沈阳建筑安装公司”的徽章和钢笔

图3 沈阳“东北电影院”几个大字,使我怦怦心动。

图4 20世纪40年代修建的沈阳站至今仍在服役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