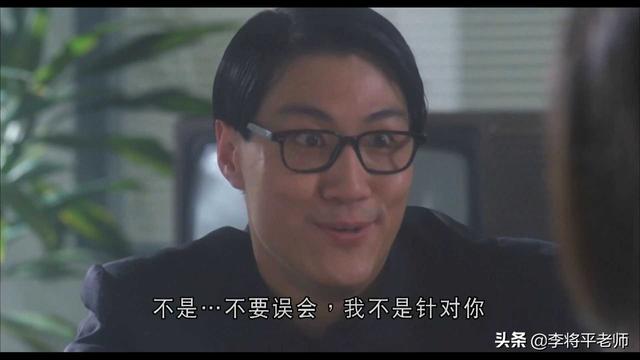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性格特点(红楼梦人物林黛玉的解析)

林黛玉无疑是《红楼梦》里最受读者喜爱的角色,也是书里重点描写的文学形象之一。她天生丽质,千娇百媚,与贾宝玉算得上天生地设的一对儿人生知己与灵魂伴侣。
但从书的开始,便交代了,黛玉的美带着几分“病态”。这样的病美人在《红楼梦》里不少,除了黛玉,还有宝钗、妙玉、巧姐儿......虽然一部小说里出现有关病的情节毫不奇怪,但在这部书里,病并不是配套的生活琐事,而是作者着力为之的。表面上看,“病”的情节只分配给了有限的几个人物,仿佛只他们几个是带病而生的,但实际上,这仅被用来起到提醒读者的作用。在作者的笔下,我们能感觉到,“病”在这部书里,是所有人物的共有特点,是带有隐喻性的。
那么,“病”究竟隐喻着什么呢?
仅以黛玉为例,黛玉究竟得了什么病,在书里表述得很模糊,有的只是“不能见外姓人”这种出自癞和尚口中的疯话。这处理方式难免使人心生疑窦,怀疑作者之所以在此语焉不详,不愿讲出来,是因为黛玉所患的并非什么器质性的疾病,比如肺病、胃病,而是“心病”或是笼罩在这个人物身上的“病态”气质。
对此人们历来有种种猜测,比如,有说“病”代表了黛玉与贾宝玉的肉体之情,这在当时的社会,是被压抑而无法表达的。也有说这是曹雪芹高明的描写技巧之一。总之,这些猜测总还是局限在文学的范畴内。我倒觉得,红学研究,常爱说“草蛇灰线,伏笔千里”,而这世上,能以这两句标榜自己,并把这作为安生立命之本的,就是心理学了。所以,我想在此,以心理学来做一番捕风捉影。我从黛玉这个人物身上捕捉到的第一个“影子”那就是,黛玉这样的女子一辈子只能由一个人来哄。她刻薄的语言、刁钻的本性,似乎就在向周围宣告着:“我”就是这么难哄,怎么样?在这世上,除了那个被我认可的特定对象外,就再没有能够把我哄好的人了。在书里,这个人当仁不让是贾宝玉。除了宝玉外,所有人,在黛玉眼里都是视而不见的。书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宝玉受到北静王的厚爱,从他那儿得了一串麝香串儿,便送去给黛玉玩。没想到,她丝毫没有体会宝玉的心意,一听说串子是北静王送的,就说了一句“什么臭男人戴过的。”然后一把扔在地上。除了作为叙述的伏笔外(这在后面会提及)这个任性的举动无异在做这样的心理宣告:不管世上有什么样出色的男人,我也只能由你哄好。黛玉的小性儿有一部分就是如此。宝玉的出场,会令黛玉得到安慰,变得兴奋、活泼、伶牙俐齿。偶尔犯回小脾气,也有宝玉急得什么似的,来想方设法地把她哄好。所有这些情节,我想已经像屏风上的画,一幅幅镌刻在熟悉本书的读者的心里。但一离开宝玉,这画风就立刻转变了,在“潇湘馆”,不管身边是谁,黛玉的情绪会陷入低谷,无理由地伤心落泪。这动不动就流泪的样子,肯定使她受人取笑,还被起了个“潇湘妃子”的绰号。至于“还泪”一说,应该也是起源于生活里的玩笑话。从这个画面,假如动用我们的联想能力,将黛玉从山重水复的大观园,放回苏州林家的小园林里。那时,黛玉只是一个几岁的小女孩,你觉得那时,她是不是与成年后一样,一样害怕独处呢?此时她还不知道世上有宝玉这样一个人在,但她是不是也如依赖宝玉那样,成天在思念着一个能哄她的人呢?泪眼婆娑地祈求那个人再一次出现。当有人试图靠近她时,虽然那时她还不会说话,但为了表示那个人绝不可替代,她会用尽力气哭喊,并歇斯底里地拒绝他人的接近呢?从此,我们能否得出一条推论,黛玉成年后的性格是她幼儿期性格的延续,所谓“还泪”不仅指向宝玉,也一定指向一位早期的依恋对象。当我们将林黛玉从家喻户晓的小说人物,还原到一个普通的家庭里,就有了空间做进一步设想,她成年期表现出的情绪失控问题,其根源可能来自婴儿期,来自她与依恋对象的创伤关系。正因为早期依恋关系的挫折与创伤没有得到及时修复,才使得她成年后,当面对成人式的爱情时,会出现情绪失控等一系列表现,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或许,当初曹雪芹在设计林黛玉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没打算将她塑造为集天下之美于一身的古典仙女(虽然黛玉真的是仙女)。在构思时,他也许已经意识到,他所要写出的黛玉,有着许多世俗人看来不尽完美之处。也许,他就生出这样的创意,以“病”这个词来命名林黛玉,以及这部小说里所有人物的共同缺陷。可以这么说,黛玉口中的“不足之症”,不是什么身体的“不足”,而是其人格结构中的创伤或缺陷。
记得本书最著名的批注者脂砚斋曾经在批语里透露,原著书末应有一张情榜,上有“黛玉情情”这样的判语。虽然对这个细节还存在不小的争议,但我认为以“情情”两字代表黛玉在书中的性格,倒是恰如其分,因为这活脱道出了一个心中有情,或者说为情而生的女子的形象。而不幸,黛玉“情情”的性格中,带有童年的依恋创伤。这近似于心理学中的边缘型人格。在此处,边缘代表极致、极端,意即具有边缘人格特点的人,他们的思维、情绪常常处于问题的边缘处。我们知道,女性与男性建立依恋关系时是不尽相同的。女性对依恋对象更专一,她倾向于以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主要是母亲)作为主要的依恋对象。对这种儿童心理有过研究的人都会发现,中途醒来的儿童会强烈渴望母亲的抚慰,这时候,如果父亲自告奋勇代替母亲来哄他的话,反而会惹恼儿童,甚至受到儿童的攻击。而男性大部分倾向于将父母双方都当做自己的依恋对象。假如说,具有自恋人格特点的人有一个“别人不好”的内心设定的话,那么,具有边缘人格特点的人内心中就有一个“我不好”的内心设定。当她遭遇困难时,总会认定是自己的原因,是自己不配得到好的结果,因而陷入重重自责之中。对依恋对象的渴望,会促使她采取极致的表现,就像个孩子,哭喊、踢打,仿佛不如此就无法换来依恋对象的关注和回馈一般。假如说自恋人格是放大了自己的形象,进而微缩了周围世界的话,那么边缘人格就正相反,他们总是放大周围世界,进而微缩自己。不论外在的举止有多么骄傲,对边缘人格的人来说,那只被用来掩饰他们无法逃避的“我不好”的内心感受。因此,具有边缘人格特质的人,不时会冒出些不好的预感来,而他们的聪明才干,要么被用于证明自己的预感是正确的,要么被用于与之对抗,总之,围绕这预感打转,就像猫咪围着自己的尾巴打转,而无法从其中脱离出去。黛玉就是具有类似的特点的人物:
a、比如,黛玉伤春、葬花的举动,带有被遗弃的伤感。春天过去,春神就此离去了,抛下了花与我们。黛玉感叹落花不仅是感叹美的流逝,也是对自身命运的感叹。古代诗人屈原曾在自己的名作《橘颂》里歌颂南方的橘树。通过橘树,他感受到了不离不弃、“一志”的母爱,而这母爱从此一直陪伴着诗人。相比之下,黛玉诗里描写的春天就没有这般温暖,反而有落在泥淖中的危险,“风刀霜剑”的寒冷、“质本洁来还洁去”的不公、怨恨,以及“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中凄凉的被遗弃感。
b、在书里,黛玉常会做出一些极端的、带有攻击性的举动,比如一些我们熟悉的情节——剪香袋,烧诗稿,这些略显莽撞的毁坏举动,都源于“我不好”的内心设定。香袋、荷包,这些物件,被她当做自己的一部分,毁坏这些物件的举动,其实都是自毁行为的延续与象征。就像一个孩子,为了获得父母的抚慰,踢掉被子,毁坏玩具,如果找不到替代品,他就做出拧自己的脸,哭的喘不上气,不好好写作业等等极端举动。这些充满孩子气的、带有威胁性的举动在书里看似因贾宝玉而起,但正如之前分析的,这种行为本身含有着对原始依恋对象的渴望,与她幼年时的行为是一致的。
c、黛玉狭隘的个性、刁钻的语言风格,显示出其幼年家庭关系其实很紧张,语言里如此多的比喻、试探、抱怨、反话,表明在这个家庭里她无法直截了当地真实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才在成年后形成如此的语言风格。而宝玉与她在一起时,也需要不断地猜测她的心事,猜测她的话背后的心理意图是什么。读者在看宝玉与黛玉的对话时,总为宝玉捏着一把汗,觉得宝玉与她在一起时,事事要陪着小心,字斟句酌。即使这样,稍有不慎,就会切中她内心中不好的预感,引发情绪的失控,甚至于更激烈的举动。
d、黛玉的小性,总是因误会而起。由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一旦失控,首先丧失掉的是思考能力,由此,进入到过度思考、自动思考的模式里去。在读者看来,她闹误会的本事,也是国宝级的。《红楼梦》里有一章节,黛玉去看望宝玉,本来是出于好意。但听了丫头们在院子里吵闲架的一言半语,立刻就以为是宝玉挑唆她们在讽刺她。饶是她在书里以聪明著称,但在这时,却没有办法像其他人(比如宝钗、凤姐)一样,运用头脑去思考事件的其他可能。原因在于,这看似偶然的事件,启动了她内心极深处一个糟糕的心理预期,使她瞬间落入了情绪失控的陷阱之中。这也意味着她瞬间失去了共情他人与共情自己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她唯有依赖他人,提供共情。而且,只有宝玉这样爱的对象,才能同时提供准确的共情与宽厚的抚慰,这二者缺一不可。这可能也是具有边缘人格特点的人的共性,如果从依恋对象那里无法得到共情与抚慰,他们的情绪就会面临失控,走向极端。
只要宝玉一现身,诸如此类的小误会,就消散了,黛玉总能在宝玉的抚慰下转涕为笑。但独自面对时,她的表现就像笼中惊恐的小鸟,毫无章法。这是黛玉这个人物的重要特点。据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再一次出现类似的误会,而宝玉若不能相救,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比如假设宝玉随北静王与贾政外出慰边去了,如果恰在此时,贾府上下,出现了一条流言,流传黛玉的母亲贾敏体弱,不能生育,而她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贾敏、林如海抱养来一解膝下无儿之苦。这样的流言肯定先在丫头、老妈子间流传起来,假如被黛玉无意听到,这条无凭无据的流言会对黛玉的情绪造成怎样的打击呢?要知道,黛玉在贾府的生活完全依靠贾母接济,与宝玉成亲的心愿也只能仰仗她老人家的支持。假如贾母听到这流言的话,哪怕这仅仅引起一点点质疑,那么贾母态度的转变,肯定会被散布出去,造成那些本无怜香惜玉之心的下人们,不仅在背地里,就是当着黛玉的面也敢于和她拌嘴,给她气受。如果这一切有人暗中推波助澜,而宝玉不在身边,贾母又有所冷落、回避的话,这一切,无疑会给黛玉造成严重的精神压力,有可能大病一场,甚至生出“质本洁来还洁去”这样极端悲观的想法来。
也许,有人会疑问,在那个时代,当曹雪芹构思《红楼梦》时,会否像我们所说的,具有与现代人类似的眼光与心理知识呢?我们将他的构思拉上人格的高度,这么做是否过于现代了呢?我觉得,一点也不。不仅如此,我觉得远远不够,这位大作家原本的设想一定比我们高明得多。心理学,即使在今天,也还处在阐释、理解人性的阶段,而文学中对人性的阐释比心理学早得多,也更丰富、更精彩。对这部书做心理分析就是这样,虽然不应机械地把小说的每一部分都绝对地看作是自传性的,但对于这部小说,我赞同胡适的基本观点,它无疑是一部关于人生的巨著。也因此,在这部作品里,总有些真实的,而非虚构的人生故事。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发现小说中这些真实的东西。这需要一个前提,即我们分析的人物是一个真实存在过、有过真实心理活动的人。所以这一切的基础在于,黛玉不应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我想,这是可以确定的。因为这个人物身上有丰富的、多层次的意义,极其生动,比如“潇湘妃子”这个绰号,品味起来,就格外精彩,这一定是来自于生活中的,其背后应该有着非常生动的生活故事,其趣味性,甚至超过了小说中的某些情节。
这篇心理小传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林黛玉是有原型作为依据的。我认为,她曾经就生活在曹雪芹身边,或就是他的家人,也未可知。以她的音容笑貌为背景,曹雪芹构思出了林黛玉这个人物,可能并没有将她全部的真实经历照搬到林黛玉这个人物身上,但这一切还是溶进了以黛玉所代表的那一类人的情节之中。《红楼梦》开篇,有个人物名叫甄士隐,他名字的意思,不就是隐藏了某些真事吗?甄士隐的女儿唤做英莲,从小就被拐走了,后来进了大观园,改名香菱,曾向黛玉学写诗。我们现在基本能够确认一点,在《红楼梦》之前,曹雪芹的确写过另一部近似的书,没有写完,又转而去写作《红楼梦》,这使得两部书的人物、情节混合在了一处。而在上一部书里,黛玉也是主要人物。那部书的风格更加写实,很有可能是按照黛玉原型的真实经历写出的,至少相去不远。后来曹雪芹通过天才的自省,完全放弃了之前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发展出更艺术化、更有设计感的个人风格。我觉得,在重写时,为了避免过多真实的情节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小说里,使小说成了传记,曹雪芹可能对英莲的故事做了修改。在原先那部书里,英莲应该幼年被拐后,很快被另一家人买去,从此在那一家生活了很多年。而在《红楼梦》里,这一情节被改成英莲被拐后,没有马上被卖掉,而是跟着拐子生活,养到了十几岁后,又将她卖给薛家。这个情节有点出人意料。要知道,拐子得手后,应该赶紧把孩子出手才对,而守着拐来的孩子将其养大,让人不禁怀疑这拐子的职业究竟是什么。从道理上讲,将拐来的孩子养大后再卖,也许能多卖几十两银子,但存在风险。如果不把孩子尽快变现,万一孩子生了病,还要花钱看病,要是病死了,那更前功尽弃了。多卖些银子这个愿望,能使这拐子守在英莲身边,一过就是十年吗?而且这个拐子,这些年在靠什么生活呢?总之,拐卖英莲的这个拐子是有些名堂的。
宝玉的丫鬟晴雯,像是黛玉内心中莽撞、侠义性格的化身。她俩都具有边缘人格的某些特点。比如,与黛玉一样,晴雯不太爱惜东西,开玩笑时,会和宝玉一起将名贵的扇子撕来玩,这是留给其他人诟病的地方。你可以把晴雯不爱惜东西看作是天真烂漫的表现,但不要忘了,作为具备边缘人格特点的人物,她不仅不爱惜东西,也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因此,她才能做出伤害自己的身体,自病中为宝玉补孔雀裘的事,这是宝钗、探春一干人所做不出来的。这种勇于自伤、不爱惜自己的性格,正是边缘人格的特点。
尤二姐和尤三姐,也属于书里描写出的具有边缘人格特质的人。虽然一个懦弱,一个刚烈,看似差别很大,但作为具备边缘人格特质的人物,她们身上却体现了边缘人格的另一特点,善良。不管怎样刻薄、尖刻,怎么对人讽刺、挖苦,看似攻击性十足,但这两个具备边缘人格特质的人物似乎从没打算将他们的攻击性诉诸实现。他们表现出的攻击性看似指向外界,但兜兜转转,最终还将落在自己身上。我觉得,这也正是曹雪芹在本书里,对黛玉这一类人的认识,并对此抱有最深切同情与喜爱之处。
还有一个小说人物,虽然她的戏份不多,但与黛玉也有丝丝缕缕的联系,这个人就是秦可卿。她对小说的贡献不在于情节,而在于设计感。她的来历、名字、卧室的装饰、生病时的药方,所有与她有关的东西,都是值得研究的,这个人物就完全是由隐语、象征、含义、线索组成的(红学中甚至有秦学一支),虽然仅仅出场了几页,却因集中体现了曹式写作风格,成为曹雪芹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她才貌双全,而曹雪芹给她起的表字很有意思,叫“兼美”,说她兼有黛玉、宝钗之美。黛玉、宝钗是《红楼梦》里最漂亮的两位,而秦可卿一身兼有二人的美丽,可见曹公对这个人物的喜爱。但就是这样一位艳压群芳的荣国府长孙媳妇,曹雪芹写她的出身时,却没有把她写成四大家族中任一族的小姐,而且说起来跟他们一点瓜葛都没有,她竟是从专门收养弃婴的“养生堂”中抱来的。
我们提到了与黛玉同类型的几个人物,有的遭拐卖,有的是抱养来的,曹雪芹似乎看透了这一类边缘人格的主要特点——无法摆脱的无归属和被遗弃感。在这部充满设计风格的小说里,是否就暗示了林黛玉的原型,也是一位自小抱养来的,有小性的女子?那么,在这篇心理小传的最后,不揣鄙薄地假设我们的分析,符合著者的原意。他在构思这一人物时,已看到黛玉身上具有早期人格的创伤与缺陷,并且,最后也是伤于此。所以,不妨沿着这个假设,设想这样一个脆弱的,容易误会别人,并容易为流言所伤的黛玉,当她遇到一条关于自己身世的流言时,那一直困扰她的情绪问题,会如何爆发呢?现行的续书过多强调了这样一点——外部环境改变之后,会对人物命运产生巨大影响。而没有充分重视这方面的线索,即原书中围绕“病”这一人格缺陷所伏笔的人物内在的性格因素。而伟大的悲剧莫不致力于极力发现人性自身的弱点,绝不会简单地诿过于世事的无常。黛玉的结局在本质上与晴雯、尤氏姐妹这一类人的结局是一样的,这一类人的悲剧,都是伤于内心对自己的敌意与攻击性(自我攻击、自责不是性格缺陷,必须看到,人物表面缺陷的背后必然是爱的表达。因爱才会自责,在成人是这样,对所有人是这样,幼儿也不能免于此。幼年期的爱与自责隐藏得更深,因为它已经无法付诸语言,就无法被长大后依赖语言的成年人所理解。对这类人来说,她们的人生从开始就注定了,是一篇爱的故事,不管表象是什么,是荒漠,还是丰饶的绿色,从始至终,她们的人生都是爱的故事,是童年故事在成年的翻版)。
黛玉有句诗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按照曹雪芹的写作风格,这句诗中可能蕴藏了黛玉之后对自己的处境的认识。
让我们回到之前的假设,分析一下这条流言背后的人。我记得在书里,第一个讲出“金玉良缘”的其实是薛蟠,虽然遭宝钗否认,又被薛姨妈斥责,但在这一家人之间,颇有些心照不宣。尤其是举止粗鄙还自视挺高的薛蟠,被斥责一顿之后,一定不觉得自己闯了祸,反而会自以为猜中了妹妹的心事。因此,这个流言,可能是由“金玉良缘”的创始者薛蟠发起的。事情的起因,也许是在某次宴饮之时,薛蟠喝醉后,想起此事,依旧愤愤不平,便央求出席宴饮的某德高望重之人给他出谋划策,帮他促成其妹与宝玉的婚事。也许,那位高人人不好当着众人明说,便推辞了,借口小解,离席而去。薛蟠看出眼色,尾随着他离开了酒席。眼看到了无人之处,或许那人想结交薛蟠,或许纯粹为了犯坏,又蒙薛蟠许了不少好处,在指点薛蟠一番之后,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几句话教唆得薛蟠精神一振,冲动之下,买通些下人,就这么把这个流言散布开了。这一节的回目也许可以叫“醉霸王花荫获毒计”。也许做完之后,薛恶霸谁也没说,把这件事丢在脑后,也没放在心上。那么,是谁将这个流言吹到黛玉耳朵里的呢?因为传递这个流言的人很多,能把这个流言传递给黛玉的,其实很多。也许是某个在水边洗衣服的女仆,也许是行事大大咧咧的史湘云。因为生性警惕,敏感的黛玉随时能感到自己被流言包围了。但最有可能做出此事的,是书里极有心计的薛宝钗。她可能假借关心,不经意间,就把这个流言说给黛玉听了。而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贾母。将流言传进贾母耳朵里不难,但是怎样能使她对自己的外孙女产生怀疑呢?也许是这样,贾母听到流言后,便找王熙凤,让她偷偷找人查证此事。贾府上下,除了紫娟熟悉黛玉,了解黛玉的家庭之外,还有一个人与黛玉相识,那就是贾雨村。人人都知道紫娟是黛玉最接近的人,找她问容易惊动黛玉,当然,派人回苏州查最可靠,但王熙凤爱图省事,不愿因这事闹得沸沸扬扬,因此很有可能找贾雨村来闲聊,借机打听。因为贾雨村既是贾府的亲戚,又做过黛玉的老师。贾雨村也许是被薛蟠的银子买通了,只言片语间,已知道王熙凤的目的,暗暗做了不利的证言,激起了贾母对黛玉身世的怀疑。或许,那个在酒席宴间给薛蟠出主意的人也是他。一定有很多人出于各自的动机,参与到散布流言的行列里,才会造成这飞短流长的局面。但每个散布流言的人他们自己又没有主观愿望用这一套来致黛玉于死地。最终的悲剧结果,一定需要黛玉的参与,经过了黛玉的放大之后,才会将这局面与“风刀霜剑”联系起来,构成一幅人言可畏,步履维艰的险状。之前,我们曾分析过,当流言传出时,在这个节骨眼上,贾宝玉不一定在大观园,而是跟北静王出去了,所以当初林黛玉听到北静王的名字,才会生出那么大的反应。面对流言,黛玉会重演之前怡红院误会时的一幕,情绪失控加无休止的过度思考。失去了哄她的人,几乎可以肯定,这会让她一病不起。作为具备边缘人格特点的人物,她几乎不会去谴责散布流言的人,查清来源,光明正大地与他们战斗,而只会自伤身世,流着泪,责怪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世界上。假如她是抱养来的,那么就很有可能无法与宝玉成婚。而且贾母的怀疑,会让贾母收回将她许配给宝玉的承诺。这不是最可怕的打击,最可怕的是,这个结果,暗合了她内心对自己的不好的预感。即使这时宝玉得到消息,不惜与父亲决裂,兼程赶回来,赌咒发誓地保证娶她,甚至以出家来抗争。但宝玉的表白,不会让她振作,因为她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我不好”的自我怀疑之中。而这时,可能贾母已经起了疑心,下令禁止宝玉不经通报,随意进入大观园了。并且封锁消息,不许下人将有关黛玉的消息传递准确给他。也许他俩真会像并头读过的《西厢记》的情节一样,通过紫娟、茗烟的帮助,才能见上一面。私会时,黛玉也许会说起自己的病情,开玩笑地说自己就是来还泪的云云,最终把书里开始的传说落实在生活化的情节里。之后,黛玉的心病,已难以逆转,忽然有一天她早起时,发现与平时不同的情况,枕上一滴泪痕皆无,似乎自己的泪已还尽了。想起之前与宝玉开的这个玩笑,心知自己命不久矣。在续书里,黛玉死于宝钗婚礼之后,临死焚稿,呕血,心中是怨恨宝玉的。而在这个版本里,她没有任何怨恨,真的是泪尽而亡。不过若是曹雪芹来构思,肯定比这高明一万倍,好在一切无关紧要,只当聊备一说。
黛玉死后,她所代表的边缘人格特质的那一类人物就宣告谢幕了。大观园里,宝钗、探春、熙凤这一类自恋人格特质的人物独占鳌头了。但很快,他们的末日也要来临了。曹雪芹似乎也很能抓住了这一类人的特点,那就是开场《金陵十二钗》戏词里所唱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具备自恋人格的人就像是舞台上的戏子,演的热闹,可惜扮演的都是别人。人生如戏,总是轮回的演出,你脱下的戏服,下一场,不知又会被谁穿上。假如林黛玉代表着纯粹的悲剧的话,那么自恋人格特质的人,既是悲剧,也是闹剧。
入选主题
- 梦回红楼
- 懂点心理学
- 文艺评论
分享至
你的喜欢和关注,会让我开心好几天
喜欢

等1人喜欢

睡睡兔
博主很神秘,点进去看看吧~
116篇文章4人关注
全部评论

- tribune公主作者
- 0
- 今天看到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作的一首诗《柳絮》抄在这里
- 我是一朵柳絮,
- 长大在美丽的春天里,
- 因为父母过早地把我遗弃,
- 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己。
- 我是一朵柳絮,
- 不要问我的家在哪里,
- 愿春风把我吹送到天涯海角,
- 我是一朵柳絮,
- 生来无忧又无虑,
- 我的爸爸是广阔的天空,
- 我的妈妈是无垠的大地。
- 展开
- 2018-02-13 19:20:22回复TA 删除
加载中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