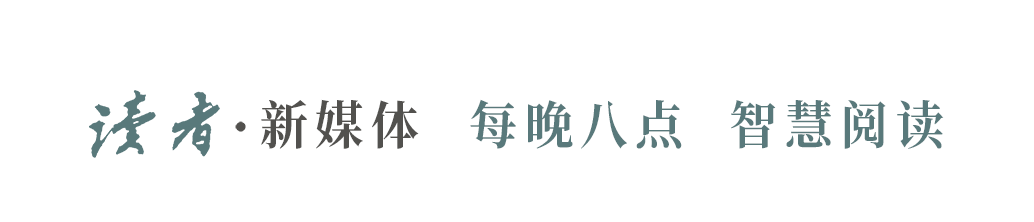折腰知荣辱回首见浮沉(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诗曰: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此孟浩然之《与诸子登岘山》也。何为乎此诗?所为见“羊公碑”之故也。羊公者谁?羊祜(221年-278年),字叔子,泰山南城人。晋著名战略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时人感其德行,故尊之为公也。
羊公曾登湖北襄阳之岘山而叹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 ,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年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山也。”时人感羊公此事而树之以碑,为其接任者杜预命为“堕泪碑”也。
唐人有孟子者亦登此山,见碑而喟然有此诗也。吾人知此事而读此诗则清清然而易识也。然而“羊公碑”知之者少,而孟浩然此诗知之者多也。故人因事而兴,事因人而名,岂有异乎。
岘山在湖北的襄阳,当年西晋的羊祜常登此山,曾经发出过前贤胜士“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的感叹。后来孟浩然也登上此山,看到了“堕泪碑”,联想到羊祜的感慨,也同样感受到了人事的代谢,也发了一番感慨,写成了以上的诗句。如果联系到羊祜的典故来理解这首诗,则很容易理解孟浩然诗所表达的情怀,也很容易受到它的感染。人事是代代相传不会停止的,古人已经永远成为古人了,而我们也不过是即将成为古人的当下人而已。想到这里不免会对自己现在所作的“登临”产生一种虚幻之感,因为此登虽然是可以感知的事实,但想到自己成为古人以后,这个“登临”就是一个虚无的东西了。所以孟浩然说“复”登临,表达得极其勉强。在这种情绪之下,江山的胜迹也会觉得是勉强地“留”的;同样的情绪之下,孟浩然看“鱼梁”之水是“落”的,看“云梦”之泽是“寒”的了;理解了孟浩然这样的心事后,再看“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这样直白的句子,就有了感人的力量了。
这首诗因“羊公碑”联想到人事代谢而起兴,孟浩然将它写成了千古名诗,说明了艺术创作之需要有切实的缘起。这个道理于书法亦然,书法如果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要有感人的力量,一旦有了实际生活的“缘起”,那么即使技术的表现略显平常一些,也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就像这首孟浩然的诗,其诗句可谓是明白晓畅,直抒己见,却反而更加动人,以至于我们对于此诗的了解更甚于对“羊公碑”这个事件本身的了解了。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